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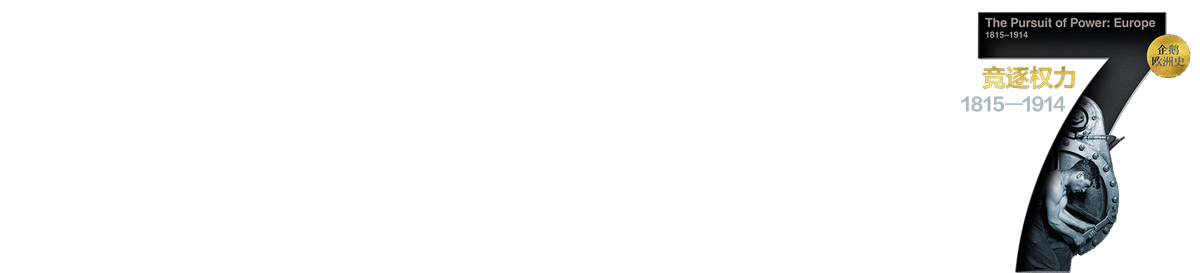
欧洲各国政府普遍渴望建立安全的集体防御体系,防止之前几十年的惨烈战争死灰复燃。这不仅体现在神圣同盟中,也体现在旨在促进战胜大国之间合作的其他各样措施中,尤其是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力促成立的“四国同盟”。在该同盟下,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以及后来加入的法国外交代表将定期举行正式会议,维护国际合作。这些大国的代表在开会期间安排并实施了一系列交易。例如在1818年的亚琛会议上,代表们拒绝了巴伐利亚对巴登大公国部分领土的诉求,削减了法国为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造成的破坏向盟国支付的赔偿的数额。代表们还决定结束盟国对法国的占领,非正式地接纳法国加入“欧洲协调”体系。会议规定,君主制将成为秩序的基石,原则上实行绝对君主制,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容纳传统立法机构,比如三级会议或应召显贵会议,或是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的议会。英国人并不完全赞同以上方针,其本国政体就含有一个选举产生的强大立法机构。在整个19世纪20年代,因对以上安排有不同的理解,英国人与奥地利人往往很难步调一致。
自由立宪主义是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和人民主权理想的产物。人民主权的思想在法国称霸欧洲末期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法起义中有所体现。自由立宪主义显然没有亡。欧洲各地自由宪政的支持者对王朝复辟时期的专制政策日益不满。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Fernando VII, 1784—1833)是在法国于半岛战争中战败后被拿破仑扶上王位的。他摒弃了1812年通过的开明宪法,恢复了昔日的绝对主义体制,重新接纳了之前被取缔的耶稣会,实行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退还拿破仑占领西班牙期间没收的贵族和教会土地。大臣个人必须直接听命于国王,彼此之间不得商议国事。费尔南多七世随心所欲任免大臣。1814—1820年期间,朝廷大臣平均任期不超过6个月。为了保住官职,众大臣不得不以最露骨的方式显示自己效忠于反革命原则。陆军大臣弗朗西斯科·德·埃吉亚(Francisco de Eguia, 1750—1827)头戴18世纪的假发,借此表明自己对旧制度的忠心。费尔南多七世在倒行逆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取缔了共济会,重新恢复宗教法庭。恢复后的宗教法庭马上开始迫害被视为异端的人。
在此背景下,西班牙政府难以有效应对美洲殖民地的起义。不但如此,费尔南多七世政府还立场强硬,拒绝对起义者做出任何让步。西班牙被法国占领,战后又经济衰退,陷入了财政困境。为了镇压美洲的独立运动,恢复对殖民地的统治,西班牙徒劳派遣远征军横跨大西洋。结果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到了1820年,西班牙实际上已经破产,甚至无力负担另一支拉美远征军的费用。1820年1月,一批少壮派军官公开“宣布”(pronounced)支持1812年宪法,开了“兵谏”(pronunciamiento)的先河,兵谏传统一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参加过对拿破仑作战的众多官兵和游击队首领受到费尔南多七世的冷落,因而愈加倾向自由主义。心怀不满的政治家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中的不少人曾遭逮捕或流放,有的也因国王压制人民参政议政而心灰意冷。西班牙警方效率低下,以上各派趁机以共济会分会为依托(警方严禁共济会开展活动,但他们依旧秘密集会),策划了一系列阴谋。所有的密谋计划都失败了,包括趁国王去妓院寻花问柳之机行刺。但是在1820年时,密谋者得到了军队中下级官兵的支持,这些官兵一想到有可能再被派去远征美洲,不禁不寒而栗。起义队伍在各省日益壮大。民众在王宫外的街头举行了游行示威,表达了对政府为挽救摇摇欲坠的财政而横征暴敛的愤恨。费尔南多七世被迫接受1812年宪法,召开议会,把执政权力移交给任期三年的自由派政府。但他不断否决议会通过的一切决议,竭力阻挠立宪主义者。局面越发动荡,城镇和乡村发生的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费尔南多七世呼吁外国干预。1823年,议会宣布废黜顽固不化的国王。激进分子开始扬言要重演巴黎革命期间发生的九月大屠杀一幕,雅各宾派的胡安·阿尔普恩特(Juan Romero Alpuente, 1762—1835)就是其中一个,一个批评者鄙视地称他“相貌丑陋、蓬头垢面、衣冠不整”。阿尔普恩特提起九月大屠杀,还杀气腾腾地提醒听众,“一夜之间,就有1.4万人被处决”。
在神圣同盟眼中,日益混乱的西班牙局势和爆发革命的危险不可容忍。意大利爆发的类似事件使西班牙危机雪上加霜。1814年,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一世(Vittorio Emanuele I, 1759—1824)结束流亡生活回国,统治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回国时,他也头戴18世纪的假发——复辟的根本象征。埃马努埃莱一世恢复了拿破仑之前的法律制度,但没有在已正式独立的热那亚实行,因为当地反对声浪过于强大。他还恢复了贵族的种种特权(包括只有贵族有权使用歌剧院包厢,在意大利,这个问题在文化上很重要),允许撒丁岛保留封建制度。犹太人和新教徒丧失了在法国统治时期获得的权利。埃马努埃莱把书报检查和操控教育的大权交给了耶稣会会士。摩德纳公国废除了拿破仑的各项改革措施,意大利中部教皇庇护七世(Pius VII, 1742—1823)统治下的几个国家也是一样。教皇拆除了街头的路灯,禁止使用天花疫苗,理由是这都是招人讨厌的现代发明。在意大利半岛的一些地区,比如波旁王朝统治下的两西西里王国,拿破仑推行的司法和行政改革措施有不少都保留了下来。自由色彩最强的是北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大公国,当地政府长期受到启蒙价值观的浸润。奥地利在教皇国驻扎了军队,防止自由主义复活。
当地的知识阶层开始对现实心怀不满。拿破仑时代他们占据的职位现在给了返回的贵族。知识阶层被一脚踢开了。两西西里王国的不少知识分子虽然保住了工作,但政府内的工作机会很少。王国的中央集权政策引起地方显贵的怨恨,他们感到自己的自主权受了限制。征兵制引起下层阶级的反抗。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保留了拿破仑的大部分改革措施,产生了一个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下的中央集权政府。高级教士由国家任命,没收的土地不予退还。拿破仑时代任命的绝大多数文官留任。然而,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行政中心在维也纳,这些文官感到难有作为。例如,只有哈布斯堡君主国首都会说德语的人才有晋升机会。服兵役的年限从4年延长到8年,征兵范围扩大。新入伍的意大利人更有可能被派到君主国的偏远地区服役,比如阿尔卑斯山以北和以东。王国的几任总督告诫梅特涅,不要重蹈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推行改革的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 1741—1790)的覆辙,约瑟夫二世试图在帝国全境实行中央集权,用单一模式统治各地。一位总督说:“伦巴第人一向无法接受以德意志人的方式治理他们的国家,也永远不会接受。”
地方显贵对国家集权的做法感到不满,曾经抵抗过拿破仑的人同样有怨气。在意大利南部,这些人从1806年起自发结成共济会式的秘密团体,名曰“烧炭党”。1815年后,法国人也仿效意大利人结成烧炭党。英国人一直鼓励这些团体密谋反对拿破仑的统治。反对专制主义是这一运动的核心内容。拿破仑倒台后,烧炭党人又找到了新的斗争目标:意大利半岛很多地区卷土重来的复辟政府施行的暴政。烧炭党人以西班牙自由主义者为榜样,发动了起义。对现实不满的士兵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起义者横穿那不勒斯,迫使两西西里国王斐迪南一世(Ferdinando I, 1751—1825,俗称“大鼻子国王”,因为他的鼻子比普通人的大)接受1812年的西班牙宪法。动乱开始向意大利半岛北部蔓延。皮埃蒙特的自由主义者开始策划推翻反动君主的起义。1821年3月,一批心怀不满的军官在皮埃蒙特的几个军营升起了三色旗。埃马努埃莱惊恐万状,逊位给他的弟弟——反动透顶的卡洛·费利切(Carlo Felice, 1765—1831)。躲在摩德纳的费利切威胁说,他决不容忍削弱“君主权力”的任何行为。与此同时,据说倾向自由主义的年轻摄政王卡洛·阿尔贝托(Carlo Alberto, 1798—1849)任命皮埃蒙特起义领导人圣托雷·迪·圣罗萨(Santorre di Santarosa, 1783—1825)伯爵为战争部部长,着手筹划进军奥地利控制的伦巴第地区。
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国的局势对维也纳会议上通过的保守纲领构成了重大威胁。俄国沙皇力主干预,但奥地利人和英国人最初觉得西班牙的形势没那么严峻。自由运动波及意大利后,奥地利人感觉受到威胁。1820年末,神圣同盟在奥地利统治的西里西亚地区的特罗保(奥帕瓦)举行会议,不顾英国反对,决定采取行动。1821年初,神圣同盟在莱巴赫再次开会,进一步确认了干涉决定。费尔南多七世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此前他被囚禁在那不勒斯,在许诺尊重宪法后被释放。刚脱离危险,费尔南多七世就收回了做出的承诺。奥地利派遣一支军队进入教皇国,随后南下那不勒斯。3月23日,这支军队抵达那不勒斯,沿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革命党人分裂为两派,一派是民主烧炭党人,另一派是追随拿破仑时代统治者若阿尚·缪拉(Joachim Murat, 1767—1815)的温和自由派,其中很多人在缪拉政府内任过职。内部分裂的革命党人无力抵抗奥地利人。那不勒斯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西里岛后,当地民众马上发动了起义。街头爆发了骚乱,大批群众攻打巴勒莫市内的监狱,一群手工业者砍下了两名立宪自由派领导人的头。工匠行会拒绝支持自由派。以上事件反映了战后这一地区陷入的经济衰退之深。当地显贵对人民起义怕得要死。起义者在巴勒莫以外地区孤立无援,无力打败岛上的那不勒斯军队。奥地利军队抵达后,起义就被扑灭了。
与此同时,奥地利人还出兵北意大利,轻而易举打败了起义者。千余人被迫流亡海外,其中就有圣罗萨。他在巴黎化名居住了一段时间,后被警方发现,再次被驱逐出境,最后在诺丁汉落脚,靠教法语和意大利语谋生。流亡者的悲惨境遇深深触动了热那亚学生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1821年4月,年仅15岁的马志尼在热那亚码头上看到流亡者寻找去西班牙的船只,并为“意大利流亡者”募捐。后来马志尼回忆道:“那天,我脑海里第一次产生了一个模糊的念头……我们意大利人 有能力 也 应该 为实现祖国自由而奋斗。”奥地利人扑灭起义后,97名烧炭党成员及其他起义者被判处死刑(不过除7人外,其余的人都逃走了,受到缺席审判)。没有逃走的几个人后来改判无期徒刑。在两西西里王国,复位的斐迪南一世就没有这么仁慈了。他手下的警察总监卡诺萨亲王安东尼奥·米努托洛(Antonio Minutolo, 1768—1838)大肆抓捕、审判起义者。几名烧炭党人被公开处决,更多的人被判处长期监禁。甚至连梅特涅都觉得太过火了。在梅特涅的压力下,疯狂报复的斐迪南一世被迫把自己的警察总监解职。在教皇国,新教皇利奥十二世(Leo XII, 1760—1829)禁止犹太人拥有财产,还强化了耶稣会士对教育的控制。在意大利各地,大批政府工作人员因涉嫌参与或同情起义而丢掉工作。皮埃蒙特新国王卡洛·费利切表示,在广大平民百姓中,“坏人都受过教育,好人都愚昧无知”,只有军队和教会可以信赖。
维也纳会议列强在如何应对西班牙局势上越发踌躇。1823年4月,法国终于出兵把费尔南多七世重新扶上王位。梅特涅对法国人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虽然西班牙革命党人试图唤起人民对抗击拿破仑和“在1808年震惊世界的能量和决断”的回忆,但这一次,法国的十万大军小心翼翼避免劫掠,并为所需粮草付钱。他们没有遇到西班牙人民或军队的顽强抵抗。西班牙军队的高级将领很快与国王握手言和。法军逼近,费尔南多被关在塞维利亚的最后几天是在从房顶上投纸飞镖中度过的。费尔南多复位后,罢免了自由派大臣,恢复了君主专制制度,清洗军队官兵,全面压制思想自由。军官人人有一份关于自己政治倾向的档案,这些档案成了军队改组的基础。法国占领军对费尔南多以上做法很不赞成,敦促他寻求和解。一些保王派军官也认为费尔南多搞的清洗过头了,加泰罗尼亚的司令官在派保王派“清洗者”去大学前,会先允许自由派教授把大学图书馆里的可疑图书带回家。但总的来说,镇压的目的达到了。自由派后来又发动了几次起义,但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
西班牙自由分子的起义不仅激励了意大利人,也激励了葡萄牙人。戈麦斯·弗莱雷·安德拉德(Gomes Freire de Andrade, 1757—1817)是葡萄牙军队内一位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军官。他短暂的职业生涯反映了这一时代各种思想流派交织的复杂情形。安德拉德曾在拿破仑的葡萄牙军团中服役,后出任帝国德累斯顿总督。他是里斯本共济会的大头领,因被控参与推翻以贝雷斯福德子爵(Viscount Beresford, 1768—1854)为首的英国军事当局密谋而遭到逮捕。贝雷斯福德本是英国将领,被任命为享有元帅军衔的葡萄牙军队总司令。安德拉德和贝雷斯福德这种为外国效力的做法,在拿破仑失败后的那些年里颇为常见。两人都没能善终。1817年,安德拉德被判犯有叛国罪,处以死刑。1820年8月,在西班牙一月起义的影响下,由一批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军官组成的混合体“宣布”反英。去巴西找国王要权的贝雷斯福德闻讯赶回葡萄牙,但被禁止下船。他不得已回到英国,于1812年出任泽西岛总督,这个职位的政治风险较小。经过长时间的谈判,葡萄牙革命党人于1822年颁布了一部激进宪法,选出一届议会,恢复了君主制,但只赋予君主有限权力。宪法扩大了公民权利,废除了葡萄牙境内对自由企业的种种封建限制,同时试图再次限制与巴西的贸易,结果巴西脱离了葡萄牙。法国对西班牙的干预在1823年引发了一起军事政变。一位年轻的军官若昂·萨尔达尼亚(João Saldanha, 1790—1876)招募了一小支部队,进军里斯本解散议会,颁布了一部新宪法,扩大了国王若昂六世(1767—1826)的权力。但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国王召回贝雷斯福德担任自己私人顾问的举动遭到广大自由派人士的憎恶,萨尔达尼亚试图搞折中,但保守派分子依旧心怀不满,他们怀疑萨尔达尼亚是共济会的首领。萨尔达尼亚发动的政变使法国人失去了出兵葡萄牙的理由,但对葡萄牙国内冲突而言是火上浇油。几年后,葡萄牙爆发了一场内战,看上去是一场王位争夺战,其实有更深层的背景。
俄国青年一代军官在战争期间和1815年占领法国的日子里,深受法国大革命思想的濡染。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共济会在俄国也颇有影响。它强调人性,重视开展慈善事业,宣扬可以私下讨论问题。俄国精英分子对欧洲的一些自由主义者相当熟悉,一批俄国军官还与瑞士烧炭党人建立了联系。1816年2月,一群人组成了“救国协会”,出身贵族的年轻近卫军军官在一起热议各种观点,比如废除农奴制,用法庭公开审讯取代俄国传统的秘密审判体制。1817年2月,“救国协会”易名为“幸福协会”,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协会部分成员参照美国宪法起草了一部俄国新宪法草案。少数人还进一步主张取消贵族头衔和特权,以土地国有化的方式消除贫困,其中就有一位年轻上校,叫帕维尔·佩斯捷利(Pavel Pestel, 1793—1826)。拿破仑入侵俄国时,佩斯捷利在1812年的博罗季诺战役中负了伤。佩斯捷利主张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性质的俄罗斯共和国,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为一院制议会。但他的自由主义理念把沙皇统治版图上的非俄罗斯人地区排除在外,包括芬兰、波罗的海诸国、格鲁吉亚、高加索地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佩斯捷利认为,除了有权享受有限独立的波兰人外,其他一切臣属民族都应该融入俄罗斯民族。(实际上,俄属波兰王国的自治和立宪地位对这一团体的成员不无影响。如果波兰可以有一部宪法,那为什么俄国不能有呢?)
1823年时,又出现了一个激进秘密组织,名叫“斯拉夫人联合会”,一共有25名成员,几乎清一色是出身贵族或上层阶级的军官。他们制订了逮捕乃至刺杀沙皇的计划,期待以此揭开革命序幕。1825年11月19日(俄历),亚历山大一世去世,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出乎革命党人意料,皇位第一顺位继承人、亚历山大一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Konstantin Pavlovich, 1779—1831)大公没有继承皇位。帕夫洛维奇大公素有思想开明的名声,至于这名声有多大根据,就不清楚了。康斯坦丁娶了一位波兰女伯爵,选择留在波兰,放弃了俄国皇位继承权。皇位于是传给了尼古拉,他是三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尼古拉有一个儿子,这样罗曼诺夫王朝就后继有人了。尼古拉一世(1796—1855)以极端保守著称,密谋者坚定了动手的决心。尼古拉从一名告密者那里得知消息后,于1823年12月14日(俄历)匆忙宣布自己是沙皇,挫败了革命党人发动政变阻止他继位的计划。革命党人在莫斯科参政院广场调集了3 000余名士兵,开枪打死了沙皇派来的调停者。沙皇旋即下令自己调集的9 000名士兵开枪镇压,革命军队逃离了现场。1826年1月3日(俄历),俄国南部地区的一次规模较小的起义也失败了。所谓“起义”就此结束。尼古拉一世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传讯了600余人,将其中121人送上法庭审判。包括佩斯捷利在内的5人被判处死刑,31人被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85人被判短期徒刑。
起义者史称“十二月党人”。和19世纪20年代欧洲其他国家类似团体的情况一样,这些人都是出身上层阶级的年轻军官。他们策划发动军事政变,但同时又是知识分子。他们亲身经历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深受民主和平等思想的濡染。像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源自共济会或受其影响的秘密社团往往是展开讨论或策划起义的场所。欧洲各国政府首脑对这些社团非常警惕。梅特涅称这些人是“一支真正强大的力量,他们在暗中活动,危害尤大,他们给社会肌体的各部分造成损害,处处留下道德败坏的种子,这些种子随后迅速生根发芽”。1820年12月,梅特涅告诉亚历山大一世,欧洲大国只有密切合作,方能化险为夷。观点保守的作家认为,烧炭党等秘密团体是1789年大革命的罪魁祸首。1815年,一位保守派作家写道:“只有在不正常的人当中才会产生阴谋。”哈布斯堡君主国政府要求所有政府公务员宣誓,表明自己不属于任何秘密社团。社会上到处弥漫着杯弓蛇影的气氛。1814年,哈布斯堡皇帝弗朗茨一世访问威尼斯时,看到有人佩戴领带别针,担心这可能是共济会使用的某种秘密符号,于是马上要求提交一份相关的调查报告。他的手下在欧洲各地奔走收集情报,描绘出一幅存在一张巨大的颠覆分子国际网的可怕图景。由于一些社团使用了“共济会”“烧炭党”等具有跨国性质的名字,因此弗朗茨的怀疑似乎得到了验证。19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政治家兼小说家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仍然认为,秘密社团“犹如一张大网罩住欧洲”。他以惯常的夸张口吻告诫道:“这些秘密社团和民众运动结合在一起,有可能摧毁社会,如同上个世纪末发生的那样。”
以上观点极大夸大了现实情况。19世纪的国家更需要害怕的是害怕本身,而不是革命党人的密谋。这种焦虑反映了梅特涅希望为国际社会协调镇压措施找到依据的愿望,以及迪斯累里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倾向。的确,一些国家秘密社团中的一些人彼此之间有联系,但他们并没有形成任何目标一致、相互协调的组织。1823年时,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革命浪潮已经消退,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可以说是浪潮的尾声。不过从某些方面看,秘密社团可以说是国际革命运动的早期胚胎:秘密社团受类似观点的影响,采取类似的手段,均源自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统治,就像是梅特涅和神圣同盟宣扬的国际保守主义的镜像,只是力量小得多。由于此前几十年的大动荡,1815年时,政治已经国际化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被外国军队入侵或占领过,也都入侵或占领过他国。在19世纪的进程中,这一现象将以越来越激烈和连贯的方式反复出现。
当然,各国各有自己的特色。在英国,密谋推翻政府的不是下级军官,而是一批自称斯宾斯博爱主义者(Spencean Philanthropists)的激进人士。这一派得名于托马斯·斯宾斯(Thomas Spence, 1750—1814),他反对圈占公地,主张实现男子普选权、废除土地贵族阶层。在阿瑟·西斯尔伍德(Arthur Thistlewood, 1774—1820)的领导下,他们企图借乔治三世(George III, 1738—1820)去世之机起事,就像几年后十二月党人想趁沙皇去世之机发动起义一样。西斯尔伍德参加过1816年的斯帕广场骚乱(Spa Fields riots),当时,斯宾斯派策划利用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进攻伦敦塔。这一次,斯宾斯派策划突袭内阁晚宴,杀死在场的所有人。一个密谋者扬言要把所有人枭首,把其中两人的头颅放在威斯敏斯特桥上示众。密谋者想象,他们的举动会引发一次反政府大起义,之后他们就可以仿效18世纪90年代法国革命者的做法,成立一个公安委员会。大规模暗杀计划其实出自小组里一个名叫乔治·爱德华兹(George Edwards, 1788—1843)的人之手,此人后来被警方收买,专门扮演密探的角色。爱德华兹向英国内政部告发了暗杀计划,警察突袭了位于卡托街的密谋者据点。在随后的打斗中,西斯尔伍德捅死了一位警官。少数几人跑掉了,多数人被逮捕,其中10人以叛国罪名被送上法庭,5人被判终身流放。1820年5月1日,包括西斯尔伍德在内的其余5人被当众处以绞刑。他们的尸体从绞刑架放到地上后,又被砍去了头颅。(大批围观群众见状,发出震耳的嘘声。)
卡托街密谋者的不寻常之处在于,他们是平民而不是军人。但在其他方面,他们与19世纪20年代初的革命团体并无二致。俄国十二月党人虽然抱有平等理想,但比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革命党人更脱离社会上的其他阶层。他们出身贵族,却具有民主精神,追求扩大政治基础,然而,他们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由于俄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因此十二月党人只能用老办法,靠军事政变实现自己的理想。在欧洲其他地方,军事政变同样是推翻王朝复辟时期政权的常用手段。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有公民社会的地方,更多受过教育的平民——律师、医生、教师、商人——加入了革命活动,而在俄国,这种人比较少。受过教育的平民如果感到大众起义的威胁,就会马上从激进活动中退出来,在西西里就是这样。1789—1794年,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党人与平民力量无套裤汉结盟,最终令法国陷入恐怖统治。鉴于这一教训,1815年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团体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争取平民百姓的支持的。王朝复辟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动乱是1819年的反犹骚乱。这次动乱除了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阶级成员参加外,确实也有知识分子参与,但很多自由主义者对骚乱的反犹特征十分反感。加入骚乱的人四处毁坏财产,梅特涅为此坐卧不安,他认为这些人对公共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1819年,梅特涅表示,爆发骚乱之地“毫无安全可言,因为在任何问题上,同样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生”。中产阶级自由派大多有同感。19世纪后期,他们对不受控制的民众怀有的恐惧感将再次浮现,给革命者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