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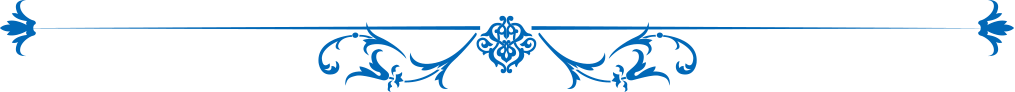
对约翰·卡文迪什谋杀继母的审判将于两个月后举行。
关于这几个星期我没什么可说的,但我对玛丽·卡文迪什充满了真挚的钦佩和同情。她斗志昂扬地站在丈夫这一阵线,蔑视所有认为他有罪的想法,并全力以赴地与之斗争。
我跟波洛说了我的钦佩,他沉思着点点头。
“是的,她是那种在艰难的环境中显示出最佳状态的女人,这更加衬托出了她们身上可爱和真诚的一面。她的骄傲和妒忌已经——”
“妒忌?”我问道。
“是的。你没注意到她是个非常善妒的女人吗?在我这么说的时候,她的骄傲和妒忌已经被放在一边了,她只想着她的丈夫,还有降临在他身上的可怕的命运。”
他说得很有感触,我认真地看着他,想起了最后那个下午,他正在考虑说不说的问题。带着那种“为了一个女人的幸福”的柔情,我很高兴他亲自做了这个决定。
“到现在,”我说,“我都无法相信。你瞧,直到最后一分钟,我都以为是劳伦斯!”
波洛龇牙咧嘴地笑了起来。
“我就知道你是这么想的!”
“但是是约翰!我的老朋友约翰!”
“每个凶手都有可能是某人的老朋友,”波洛富有哲理性地说道,“你不能把情感和理智混在一起。”
“我得承认我本以为你会给我个暗示的。”
“可能吧,我的朋友,我没这么做,就因为他是你的老朋友!”
我被他的话弄得很窘迫。我想到自己那么轻率地就把自以为是波洛对包斯坦的看法告诉了约翰。附带说一句,关于对包斯坦的指控——他已经无罪释放了。然而,虽然这一次他比他们更加聪明,而且关于间谍活动的指控没能把他遣送回国,但是今后他的各种权利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活动范围也缩小很多。
我问波洛是不是认为约翰会被定罪,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回答说,相反,他极有可能被宣判无罪。
“但是,波洛——”我反对道。
“哦,我的朋友,我不是一直跟你说我没有证据吗。知道一个人有罪是一回事,证明他有罪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是这样,证据就太少了。这就是麻烦的地方。我,赫尔克里·波洛,知道,可是在我的链条上缺少最后一个环节。而且除非我找到缺少的那一环——”他严肃地摇摇头。
“你开始怀疑约翰·卡文迪什是在什么时候?”过了一会儿,我问道。
“你就一点儿也不怀疑他吗?”
“不,从没有过。”
“你曾无意中听到卡文迪什太太和她婆婆的对话片段,可后来她在审讯中却没有坦诚相告,你都没有怀疑过?”
“没有。”
“如果把两件事放在一起,你要想一想,如果和英格尔索普太太吵架的不是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你记得吧,审讯时他竭力否认——那一定是劳伦斯或约翰。那么,如果是劳伦斯,玛丽·卡文迪什的行为就无法理解了。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是约翰,整件事情就能很自然地解释通了。”
“所以,”我恍然大悟地大声说道,“是约翰那天下午在跟他母亲吵架!”
“完全正确。”
“你一直都知道?”
“当然。这样卡文迪什太太的行为才解释得通。”
“可是你却说他会被无罪释放?”
波洛耸耸肩。
“是的。在警方的法庭审理中,我们将听到关于案件的起诉,但是他的律师十之八九会建议他保留答辩权。这样在审判时,我们就会感到很吃惊。而且——啊,还有,我要提醒你一句,我的朋友,在这个案子中我不能露面。”
“什么?”
“是的。严格地说,我跟这起案子没有关系。即使我找到链条上缺少的最后一环,我也必须留在幕后。让卡文迪什太太觉得我是在帮她丈夫,而不是跟他作对。”
“要我说,这是在玩手段。”我抗议道。
“当然不是。我们对付的是一个绝顶聪明、不择手段的人,所以我们必须采用能力所及的一切方法——否则他会从我们的指缝中逃走。这就是我要小心地留在幕后的原因。所有这些都是杰普发现的,所有的功劳都是杰普的。如果我去作证——”他咧嘴笑笑,“很有可能是被告的证人。”
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按部就班地做事。”波洛接着说,“太奇怪了,我能提供证据推翻控方提出的一个论点。”
“什么论点?”
“关于烧毁遗嘱的论点。约翰·卡文迪什没有烧毁那份遗嘱。”
波洛是个名副其实的预言家。警察法律诉讼中的细节我就不详加说明了,因为里面有很多无聊的重复。我直接说一点:约翰·卡文迪什保留了答辩权,并直接受审。
九月,我们都去了伦敦。玛丽在肯辛顿租了一幢房子,波洛也属于这个家庭聚会中的一员。
我在陆军部找到了一份工作,所以能经常看到他们。
几个星期过去了,波洛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他说的那个“最后一环”仍然没有找到。私下里我倒是希望维持现状,因为要是约翰被判有罪,玛丽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九月十五日,约翰·卡文迪什出现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被告席上,被指控“蓄意谋杀艾米丽·阿格尼丝·英格尔索普”,但他表示“不认罪”。
欧内斯特·海维韦萨爵士,著名的皇家法律顾问,将为他辩护。
菲利普先生,皇家法律顾问,代表王室对此案展开审理。
这件谋杀案,他说,经过了充分的谋划,并且极其冷酷无情。确确实实证明了一个溺爱孩子的、轻易相信别人的母亲被继子蓄意谋杀,然而她对他比亲生母亲还要好。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开始抚养他。他和他的妻子在斯泰尔斯庄园里过着奢华的生活,受到她事无巨细的关心和照顾。她是他们善良而慷慨的恩人。
他建议传召证人证明被告是一个挥霍浪费的人,经济上已处于穷途末路,但仍然跟邻近的农场主的妻子雷克斯太太有染。此事传到了他继母的耳朵里,在她去世前的那个下午,她就这件事指责他,随后两人争吵了起来,一部分说话的内容被人无意中听到了。就在前一天,被告在村子里的药店里买了士的宁,他化了装,目的是把罪行嫁祸给另一个人,即英格尔索普太太的丈夫,一个他极度妒忌的人。幸好英格尔索普先生提供了一个无懈可击的不在场证明。
公诉律师继续说道,七月十七日下午,和儿子争吵之后没多久,英格尔索普太太就立了一份新遗嘱。第二天早上,在她卧室的壁炉里发现了这份烧毁的遗嘱,但是有证据显示,这份遗嘱的条款有利于她的丈夫。其实在结婚之前,死者已经拟定了一份有利于英格尔索普先生的遗嘱,但是——菲利普先生摇着富有表现力的食指——被告不知道这件事。旧遗嘱还在,是什么导致死者重新立一份新遗嘱,他说不出来。她是个老太太了,很有可能已经忘记了之前那份,或者——这对他而言似乎可能性更大——她可能以为一旦结婚,这份遗嘱就作废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一些说法。女人都不怎么精通法律知识。大约一年前,她完成了一份对被告有利的遗嘱。他会拿出证据证明在那个悲惨的晚上,是被告最后把咖啡端给他继母的。晚上的时候,他得到允许进入她的房间,就在那时,毫无疑问,他找到了烧毁遗嘱的机会,因为就他所知,这份遗嘱会让英格尔索普先生的利益变得合法有效。
被告被逮捕是因为一位非常优秀的警官,也就是杰普探长,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一个装有士的宁的药瓶,此药瓶跟谋杀发生前一天村里药店卖给假英格尔索普先生的那个是同一个。这些可怕的事实是否可以构成判定被告有罪的充分证据,陪审团将予以裁决。
菲利普先生还巧妙地暗示道,如果陪审团不这么裁决,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说完,他坐了下来,擦擦额头。
第一批原告证人大多数都是那些已经在聆讯时传召过的人,并且第一次出示了医学证明。
欧内斯特·海维韦萨爵士——因对证人采取无道德原则而闻名于全英国——只提了两个问题。
“我认为,包斯坦医生,士的宁作为一种药品,起效很快吧?”
“是的。”
“而且你无法说明何以在本案中药效延缓?”
“是的。”
“谢谢。”
梅斯先生指认出公诉律师递给他的药瓶就是他卖给“英格尔索普先生”的那一个。
经过追问,他承认他和英格尔索普先生只是面熟,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这位证人并没有被盘问。
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被传召上来,他否认买过毒药,以及跟妻子吵过架。有好几个证人都证明他所说的属实。
花匠的证词是关于见证遗嘱签署的。之后多卡丝被传召。
多卡丝,对她的“少爷”忠心耿耿,竭力否认她听到的是约翰的声音,不顾一切地坚决声称,在内室里和她女主人在一起的是英格尔索普先生。被告席上的约翰脸上浮起了一丝苦笑。他太清楚她的英勇反抗是多么没用了,因为否认这一点并不是辩护的目标。当然,卡文迪什太太不可能被传上来出示对她丈夫不利的证据。
提了几个有关其他情况的问题之后,菲利普先生问道:
“今年六月下旬,你记不记得百盛寄来一个给劳伦斯·卡文迪什先生的包裹?”
多卡丝摇摇头。
“我不记得,先生。也许寄来了,不过劳伦斯先生六月份离开家了一阵子。”
“万一他不在家的时候有包裹寄来,怎么办?”
“放在他房间里,或者再寄给他。”
“是你做这些事吗?”
“不,先生,我会放在门厅的桌子上。这种事情都是霍华德小姐打理。”
伊芙琳·霍华德上了法庭,盘问了她几个别的问题之后,又问到了包裹这件事。
“不记得了。寄来的包裹太多了。不可能每个都特别留意。”
“你记不记得,劳伦斯先生去威尔士之后,你是把包裹寄给他了,还是放在他房间了?”
“不记得寄给他了。如果寄了会想起来的。”
“假定有个寄给劳伦斯先生的包裹后来不见了,你应该注意得到吧?”
“不,我不会这么想。我会认为有人替他保管起来了。”
“我想,霍华德小姐,是你发现这张牛皮纸的吧?”他举起一张布满灰尘的纸,正是波洛和我在斯泰尔斯庄园的起居室里检查过的那张。
“没错,是我发现的。”
“你为什么要找这张纸?”
“请来负责这个案子的那个比利时侦探让我找的。”
“你最后在哪儿找到的?”
“在衣橱的……顶上。”
“在被告衣橱的顶上吗?”
“我……我认为是这样的。”
“不是你自己找到的?”
“是。”
“那你一定知道在哪儿找到的了?”
“是,在被告的衣橱顶上。”
“这就对了。”
来自戏剧服装供应商百盛的一名店员证实,六月二十九日,他们按照要求向劳伦斯先生提供了一把黑胡子。是写信预定的,信封里装了一张邮政汇票。不,他们没有保留此信件。所有的交易事项都做了登记。他们按照指定的姓名和地址——斯泰尔斯庄园,L.卡文迪什先生——寄出了胡子。
欧内斯特·海维韦萨爵士笨拙地站起身子。
“这封信是从哪里写来的?”
“从斯泰尔斯庄园。”
“你们寄包裹也是这个地址?”
“是的。”
“信件是从那里寄来的?”
“是的。”
海维韦萨像个猛兽一样冲他扑了过去。
“你怎么知道的?”
“我……我不明白。”
“你怎么知道信是从斯泰尔斯寄来的?你注意到邮戳了吗?”
“没……但是……”
“啊,你没注意到邮戳!可你却信誓旦旦地宣称信是从斯泰尔斯寄来的!实际上,可能是其他地方的邮戳?”
“是……吧。”
“虽然这封信写在印了地址的信纸上,可也许是从其他地方寄来的呢?比如,威尔士?”
店员承认这有可能是事实,欧内斯特爵士这才表示满意。
伊丽莎白·威尔斯,斯泰尔斯庄园的二等女佣,说她上床休息之后想起来,没按英格尔索普先生的吩咐那样只是关上门,而是把前门给闩上了。于是她再次下楼去纠正自己的错误。她听见右侧传来一声轻微的动静,于是她偷偷朝过道看了看,看到约翰·卡文迪什先生正在敲英格尔索普太太的门。
欧内斯特·海维韦萨很快就驳回了她的证词。因为招架不住他那无情的逼问,她绝望地自相矛盾起来,于是欧内斯特爵士带着满意的表情又坐了下来。
安妮的证词说的是地板上的蜡烛油,并且看到被告把咖啡端进内室。
审讯结束,第二天继续。
我们一到家,玛丽就强烈地谴责起控方律师来。
“那个可恶的人!他给我可怜的约翰布了一张多大的网啊!他把每件小事都扭曲得面目全非!”
“嗯,”我安慰她,“明天就不一样了。”
“没错,”她陷入了深思,忽然又抬高了声音,“黑斯廷斯先生,你不会认为——当然不可能是劳伦斯了——哦,不,不可能!”
但是我也很迷惑,所以单独和波洛在一起时,我问他觉得欧内斯特爵士的目的是什么。
“啊,”波洛一副欣赏的口气,“他是个聪明人,那个欧内斯特爵士。”
“你觉得他认为劳伦斯有罪吗?”
“我认为他不关心任何事!不,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搅浑陪审团的脑子,让他们对哥哥还是弟弟做的产生意见分歧。他努力证明,针对劳伦斯的不利证据,和针对约翰的一样多。而且我绝对相信他会成功的。”
审讯重新开始时,探长杰普是第一个被传召的证人,其证词简明扼要。讲述完早期的一些事件之后,他接着说道:
“根据所获得的情报,萨默海警长和我本人在被告暂离房屋期间,搜查了他的房间,在他五斗橱里的一些内衣下面,我们发现了:第一,一副金丝夹鼻眼镜,和英格尔索普先生戴的那副很相似——”这个已经提交给法庭,“第二,这个药瓶。”
这就是那个已经被药店伙计辨认过的药瓶,一个蓝色的玻璃小瓶,里面有一些白色结晶,标签上写着:“盐酸士的宁。剧毒。”
警察法庭诉讼以来,侦探发现的最新一条证据是一张长长的、几乎全新的吸墨纸。是在英格尔索普太太的支票簿里发现的,用镜子反照,就会清晰地出现这几个字:“我死后,全部财产都留给我深爱的丈夫阿尔弗雷德·英格……”这说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那份被烧毁的遗嘱有利于死者的丈夫。接着,杰普出示了修复后的、从壁炉取出的烧焦纸片,连同在阁楼上发现的胡子,共同构成了他全部的证据。
但是欧内斯特爵士的盘问还在后头。
“你搜查被告房间的时候是哪一天?”
“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正是惨剧之后的一周?”
“是的。”
“你说你在五斗橱里发现了这两样东西,抽屉没上锁吧?”
“是的。”
“你觉不觉得,一个犯了罪的人把罪证放在一个随便谁都能找到的没上锁的抽屉里,这几乎不太可能?”
“可能他是匆忙间塞进去的。”
“可你刚才说过离案发整整一个星期了。他有充足的时间移走并销毁它们。”
“可能吧。”
“关于这点,不存在可能。他有还是没有充足的时间移走并销毁它们?”
“有。”
“下面藏着这些东西的那堆内衣是厚还是薄?”
“厚的。”
“换句话说,这是冬天时穿的内衣。显然,被告不应该去开那个抽屉,对吗?”
“也许吧。”
“可否回答我的问题?被告有没有可能在盛夏最炎热的那一周,去开一个装有冬天内衣的抽屉?有还是没有?”
“没有。”
“既然如此,有没有可能现在说的这两样东西是第三个人放在那儿的,而被告对此一无所知?”
“我认为不太可能。”
“但还是有可能?”
“是的。”
“可以了。”
接下来是更多的证据。关于七月底被告发现自己陷入经济危机的证据,关于他和雷克斯太太有染的证据——可怜的玛丽,对一个有自尊心的女人而言,听到这些,该多么苦涩啊。伊芙琳·霍华德说的是对的,虽然她对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的憎恨让她一口咬定他就是那个与本案有关的人。
之后,劳伦斯·卡文迪什被带入证人席,低声回答着菲利普先生的问题。他否认六月份在百盛订过任何东西。实际上,在六月二十九日,他就远离庄园到达威尔士了。
欧内斯特爵士的下巴立刻挑衅似的翘了起来。
“你否认于六月二十九日向百盛订购过黑胡子吗?”
“没错。”
“啊,万一你哥哥发生什么事,谁将继承斯泰尔斯庄园?”
这个残忍的问题让劳伦斯苍白的脸立刻一片通红。法官不满地咕哝着,被告席上的约翰则愤怒地向前探着身子。
海维韦萨根本不在乎他当事人的愤怒。
“回答我的问题。”
“我想,”劳伦斯平静地说,“会是我。”
“你说‘想’是什么意思?你哥哥没有孩子,你会继承它,是吗?”
“是。”
“啊,很好。”海维韦萨那和蔼的语气中有一种残忍,“而且你还会继承一大笔钱,对吗?”
“实际上,欧内斯特爵士,”法官抗议道,“这些问题跟本案无关。”
欧内斯特爵士鞠了一躬,继续发射利箭。
“在七月十七日星期二,你和另一位客人去参观了塔明斯特红十字医院的药房,是吗?”
“是。”
“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你正好是一个人待着,你是否打开了毒药橱柜,检查了一些瓶子?”
“我……我……可能吧。”
“我认为你确实这么干了吧?”
“是。”
欧内斯特爵士又向他发射了第二个问题。
“你是否特别检查过一个瓶子?”
“没有,我不这么认为。”
“小心点儿,卡文迪什先生。我指的是装有盐酸士的宁的一个小瓶子。”
劳伦斯的脸色一下子变青了。
“不……我真的没有。”
“那你怎么解释瓶子上面留下了你清晰无误的指纹?”
这种恐吓的手段对紧张的情绪来说非常有效。
“我……我想我可能拿过瓶子。”
“我也这么想!你从瓶子里拿出过什么东西没有?”
“当然没有。”
“那你干吗拿瓶子?”
“我曾经学过医学,对这种东西自然感兴趣。”
“啊!所以你对毒药‘自然感兴趣’,对吗?然而,你是等到只有一个人时,才满足你的‘兴趣’的吧?”
“那纯粹是巧合。就算其他人在那儿,我也会这么做的。”
“可是,这事发生的时候,其他人不在那儿吧?”
“不在,但是——”
“实际上,整个下午,你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是独自一人,然而你对盐酸士的宁的‘自然的兴趣’就发生在——我说,发生在——几分钟之内,是吗?”
劳伦斯结结巴巴地说得很可怜。
“我……我……”
欧内斯特爵士满意地说:
“我没什么要问你的了,卡文迪什先生。”
这几个盘问在法庭上引起了强烈的骚动。在座许多打扮时髦的女人都忙着交头接耳,她们窃窃私语的声音越来越响,法官不得不生气地威胁说如果不马上安静下来,就要把她们从法庭请走了。
还有一个证据。几个笔迹专家就药店毒药登记册上的“阿尔弗雷德·英格尔索普”这一签名发表了看法。他们一致认为这不是他的笔迹,并认为也许是被告伪装的。盘问之后,他们承认也有可能是其他人巧妙伪造的。
欧内斯特·海维韦萨爵士的发言并不长,然而却使案情有利于被告,并且态度强硬有力。他说,在他多年的经验中,从来——从来都不知道单凭一点微弱的证据就可以指控谋杀。这些证据不仅仅完全是间接的,而且绝大部分都没有得到证实。让他们来看看这些他们听过和公正地筛选过的证据。士的宁是在被告房间的一个抽屉里发现的。正如他所指出的,这个抽屉没有上锁,并且他认为没有证据能证明把士的宁放在那儿的人是被告。实际上,这是某个第三者把罪行嫁祸给被告的邪恶目的的一部分。控方无法提供哪怕一点证据支持他们的论点,即从百盛订购黑胡子的人是被告。被告已经坦白承认他和继母之间发生过争吵,但这件事还有被告的财政困难都被严重地夸大了。
他那博学的朋友,欧内斯特漫不经心地向菲利普斯点了点头,然后说道,如果被告是清白的,在聆讯时就应该站出来解释吵架的人是他,而不是英格尔索普先生。关于这一点,爵士认为事实被扭曲了。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星期二晚上,被告回到家里,有人确定地告诉他英格尔索普夫妇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被告丝毫没有怀疑有人可能把他的声音错听成了英格尔索普先生的。因此他想当然地认为继母吵了两次架。
控方断言,七月十六日星期一那天,被告装扮成英格尔索普先生去了村子里的药店。恰恰相反,那个时间被告正在一个叫做“马斯顿的小树林”的偏僻之地,是一张匿名字条让他去那儿的,字条上是一些勒索敲诈的话,威胁他如果不照做就会向他妻子透露某些事情。因此,被告到达了指定的地点,白白地等了半个小时才回家。不幸的是,来回的路上他没有遇见一个人能证明这件事的真实性。幸亏他保留了这张字条,可以作为证据。
至于有关烧毁遗嘱的陈述,被告以前当过律师,一年前所立的那份有利于他的遗嘱,已经因为继母的再婚而作废了。他会出示证据证明是谁烧了这份遗嘱,而且有可能为本案打开一个全新的视角。
最后,他向陪审团指出,除了约翰·卡文迪什,还有不利于其他人的证据。他引导他们注意一个事实,对劳伦斯·卡文迪什的不利证据就算不如对其兄长的有力,至少也是不相上下的。
此时,他传召了被告。
被告在证人席上表现得很好。经过欧内斯特爵士的巧妙处理,他把故事讲得既精彩又让人信服。他出示了收到的匿名字条,并交给陪审团检查。他愿意承认自己出现了经济困难,以及跟继母的分歧,这对他否认谋杀很有助益。
结束陈述之后,他顿了顿,又说:
“我必须澄清一件事。我完全拒绝和否认欧内斯特·海维韦萨爵士针对我弟弟的暗示。我深信,我弟弟在此案件中所做的绝对不会比我多。”
欧内斯特爵士只是笑了笑,他敏锐地注意到,约翰的抗议已经在陪审团中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
接着,盘问开始了。
“我认为,你所说的你没有料到证人可能把你的声音错听成了英格尔索普先生的。这不是很奇怪吗?”
“不,我不这么认为。有人告诉我说我母亲和英格尔索普先生吵了一架,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不是真的。”
“女佣多卡丝重复了谈话片段——你一定记得这些片段——之后,你也没有想到吗?”
“我没听出来。”
“你的记忆肯定非常短暂!”
“不是的,但当时我们都很生气,而且我觉得说了很多多余的话。我没怎么留意我母亲实际都说了什么。”
菲利普先生表示怀疑的冷哼是法庭辩论技巧的一个成就。他转向了字条的话题。
“你恰到好处地提交了这份字条。告诉我,上面的笔迹感觉熟悉吗?”
“不熟悉。”
“你不认为这和你那经过伪装的笔迹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吗?”
“不,我不认为。”
“我告诉你,这是你自己的笔迹!”
“不是。”
“我告诉你,你急于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所以想出了这么个虚假而不可思议的约会的主意,并且自己写了这张字条以证明你的陈述!”
“不是。”
“就在你所宣称的自己在一个偏僻、人迹罕至的地方等待的时候,其实你是去了斯泰尔斯村的药店,以英格尔索普先生的名义买了士的宁,是这样吗?”
“不,这是个谎言!”
“我告诉你,你穿着英格尔索普先生的一套衣服,贴着跟他相似的修剪过的黑胡子,到了药店——还在登记册上签了他的名字!”
“绝对没有这种事。”
“那么我把字条、登记册上的字迹,还有你自己的笔迹,这三者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交给陪审团审议。”说完,菲利普斯先生坐了下来,一脸已经尽到职责、但仍对这种蓄意的伪证感到十分震惊的表情。
此后,由于时间已晚,案子下星期一继续开庭。
我注意到波洛的样子十分气馁。我太了解他纠结的眉头了。
“怎么了,波洛?”我问。
“啊,我的朋友,事情不顺啊,不顺。”
我心头禁不住安慰地一动。显然,约翰·卡文迪什可能会被宣判无罪。
到家以后,我的小个子朋友挥手拒绝了玛丽发出的喝咖啡的邀请。
“不了,谢谢你,太太,我想上楼去自己的房间。”
我跟着他。他走到书桌旁边,仍然皱着眉头,拿出一小盒纸牌,然后拖了一把椅子到桌边,而且让我诧异万分的是,他开始一本正经地搭纸牌房子了!
我不自觉地拉长了脸,他马上说道:
“不,我的朋友,我不是老糊涂了!我在稳定自己的神经,仅此而已。这工作需要手指精密。手指精密才能让大脑精密。我从未像现在这样这么强烈地需要它!”
“出了什么事了?”我问。
波洛朝桌上使劲捶了一拳,推翻了他仔细建造的大厦。
“是它,我的朋友!我能造一座七层高的大厦,可我不能——”捶了一拳,“找到,”又是一拳头,“我跟你说过的最后一环。”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只好保持沉默。接着,他又开始慢慢地搭建纸牌了,同时还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
“完成了——就这样!放上——一张牌——另一张——用数学的——精密度!”
我看着纸牌房子在他手中不断增高,一层接一层。他从来没有犹豫或动摇过。简直就像是在变戏法。
“你的手真稳,”我说,“我相信我只看到你的手抖过一次。”
“毫无疑问是在我生气的时候。”波洛十分平静地说。
“确实!你怒气冲天。你还记得吗?在你发现英格尔索普太太卧室里那个文件箱被撬开的时候。你站在壁炉台旁边,习惯性地摆弄着上面的东西,手抖得就像一片树叶!我得说——”
但是我突然打住了。因为波洛嘶哑而含混地大叫一声,再次推翻了自己的杰作,双手按在眼睛上不停地揉着,显然非常痛苦。
“天哪,波洛!”我大叫,“你怎么了?病了吗?”
“不,不,”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是……是……我有了一个想法!”
“啊!”我长舒一口气,大声说道,“是你的那个‘小想法’吗?”
“哦,实际上,不是!”波洛坦白地说,“这一次是个非常巨大的想法,了不起的!这是你——你,我的朋友,给我的!”
忽然,他紧紧地抱住了我,热情地亲吻我的双颊。还没等我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他已经跑出了房间。
这时,玛丽·卡文迪什走了进来。
“波洛先生怎么啦?他从我身边冲过去,大喊着:‘汽车库!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告诉我汽车库怎么走,太太!’可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已经冲到大街上了。”
我急忙来到窗口。没错,他在那里,正在街上猛冲,没戴帽子,边跑边做手势。我转向玛丽,对她做了个表示绝望的手势。
“他被一个警察拦了一下,接着又跑了,现在拐过街角了!”
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无能为力地对视着。
“出了什么事?”
我摇摇头。
“我不知道。他正在搭纸牌房子,忽然说有了个想法,于是,就像你看到的那样,他跑了出去。”
“好吧,”玛丽说,“希望他晚饭前能回来。”
可是,夜幕降临了,波洛还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