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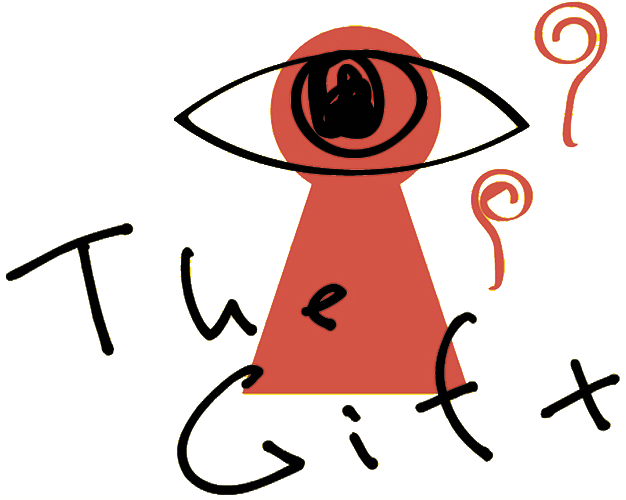
《天赋》的大部分章节,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在柏林完成的;它的最后一章一九三七年完稿于法国的里维埃拉。《当代纪事》——一组前社会革命党成员在巴黎创办的一家重要的流亡者杂志——分期(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第六十三至六十七期)刊登了该小说,但却删除了其中第四章。该章被拒载,与书中第三章(二〇四页)瓦西列夫拒绝出版那部传记,都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这是生活发现它不得不模仿它所谴责的艺术的绝好事例。只是在一九五二年,该小说开始创作近二十年之后,它的完整版本才最终问世,由好心的纽约契诃夫出版社出版。想象一下人们在俄罗斯现政权统治下居然有可能读到《天赋》,该是何等有趣的事。
我从一九二二年起一直客居柏林,与书中的男青年循了相同的时间轨迹;但无论这一事实,还是我与他共有的一些爱好,诸如文学和鳞翅目昆虫学,都不应该让读者说声“啊哈”,并且将构思者混同于他构思的人物。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从来不是费奥多尔·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我父亲不是中亚地区的探险家,虽说我仍然有望将来哪天成为这样一位探险家;我从未向济娜·梅茨求爱,也不曾为诗人孔切耶夫或其他哪位作家担心。实际上,正是从孔切耶夫以及另一个次要人物,即小说家弗拉基米罗夫身上,我看出了一九二五年左右我本人的些许印迹。
在写作此书的年月里,我在重现柏林及其侨民聚集区时,不能像我在后来的英文小说里描写某些环境时那样果断,那样无所顾忌。书中多处借助艺术技巧反映了历史。费奥多尔对德国人的态度,或许特别典型地反映了俄国流亡者对(柏林、巴黎或布拉格的)“本地人”那种粗鲁而荒谬的蔑视。再者,我笔下的男青年受到一个崛起的独裁政权的影响,该政权所处的时期与小说创作同时,而不是小说部分反映的那段历史时期。
知识分子的大量外流,形成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最初几年普遍移居国外的侨民中如此显著的一个群体,这在今天有如某个神秘部落的多次迁徙,它的那些鸟形符号和月形符号,现在正被我从大漠烟尘中逐渐发现。我们始终不为美国的知识分子所知(他们受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认为我们只不过是些凶恶的将军、石油巨头、拿着长柄眼镜的瘦削的贵妇人)。那个世界如今已经消失了,布宁
 、阿尔达诺夫
、阿尔达诺夫
 和列米佐夫
和列米佐夫
 消失了。弗拉季斯拉夫·霍达谢维奇
消失了。弗拉季斯拉夫·霍达谢维奇
 消失了,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俄国诗人。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们正在相继离世。他们在最近二十年的所谓“失去家园者”中尚未找到继承者,这些“失去家园者”已将自己苏维埃祖国的地域观念和平庸习气带到了国外。
消失了,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俄国诗人。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们正在相继离世。他们在最近二十年的所谓“失去家园者”中尚未找到继承者,这些“失去家园者”已将自己苏维埃祖国的地域观念和平庸习气带到了国外。
《天赋》的世界目前是一个幻境,如同我的大多数作品,有鉴于此,我能以一定程度的超然的口吻谈论此书。这是我过去或今后的最后一部俄语小说,它的女主人公不是济娜,而是俄罗斯文学。第一章的线索围绕费奥多尔的诗歌展开。第二章是费奥多尔文学进程中一次朝向普希金的突进,包括他尝试着描述父亲的几次动物学野外考察。第三章转向果戈理,但它真正的中心却是献给济娜的爱情诗。费奥多尔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传》,一首十四行诗内的一个螺旋式结构,是第四章的重点所在。最后一章糅合了先前所有的主题,并隐约暗示了费奥多尔梦想将来哪天写出的书:《天赋》。我不知道书中那对年轻恋人被打发走以后,读者的思路还能跟随多远。
众多俄罗斯天才作家加入了书中庞大而有序的阵容,致使本书的翻译殊为不易。我的儿子德米特里·纳博科夫完成了第一章的英译,但由于自身事务的急迫,无法继续翻译下去。其余四章由迈克尔·斯卡梅尔翻译。一九六一年冬天,我在瑞士的蒙特勒认真修订了五章的所有译稿。我对每首诗歌的译文及散见于书中的若干诗行的译文负责。卷首的那段引语并非虚构。书中的最后一首诗则模仿了《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一节。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于蒙特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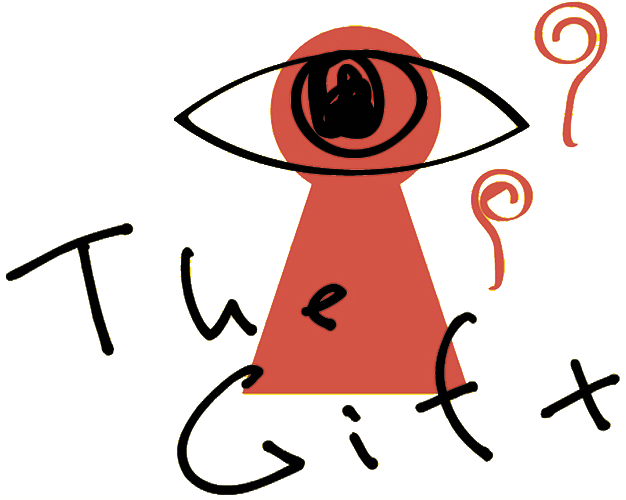
橡木是树。玫瑰是花。鹿是动物。麻雀是鸟。俄罗斯是我们的祖国。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P.斯米尔诺夫斯基
《俄语语法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