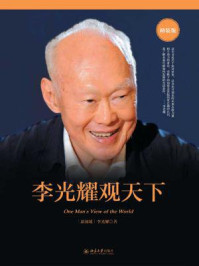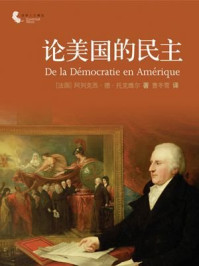雅典民主往往被叫作“直接民主”,这当然是有道理的,毕竟所有公民都有权利与义务参加经常举办的公民大会。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在雅典政治生活中,更活跃的成分不是公民大会,而是法庭、500人议事会、行政机构。这三类机构的运作方式似乎不能被称为“直接民主”,因为其主角只有一部分公民,而不是全体公民。在只有部分公民参与的情况下,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政治过程持续被同一批人把持,形成一批固化的政治精英,而将其他公民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
但雅典并非如此,尽管没有在政治的方方面面做到“直接民主”,它的制度安排却展现出尽可能让人民当家做主的特征。第一,三类机构的规模都很大,可以让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每年,法庭有6000位候选审判员,议事会有500位成员,行政官有700位,加在一起,担任各类公职的人达7000多位,占全体公民人口四分之一左右,占30岁以上公民的比重可能高达50%。第二,三类机构的任期都很短,可以让尽可能多的公民有机会参与政治生活。三类职务任期都只有短短一年,且议事会成员与行政机构人员只限一个任期,任期一满,必须离去,换上另一批人,任何人都无法长久独霸这些位置。第三,三类机构的人选都是以抽签的方式产生,可以让所有够资格人士都具有完全平等的机会当选,不允许任何人占据先机。
把雅典的法庭叫作“法庭”有点牵强,它其实是个三合一的机构,“可以看作公民大会的一部分”,
 除了审理各类司法案件外,还担负着立法与行政职能。之所以还是将它称为“法庭”,仅仅是因为实在找不到与之对应的现代词汇。
除了审理各类司法案件外,还担负着立法与行政职能。之所以还是将它称为“法庭”,仅仅是因为实在找不到与之对应的现代词汇。
前面提到,在雅典政制中,法庭的地位与公民大会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然而,在如此重要机构唱主角的,却是人民审判员(dikastai),即担任审判员的普通老百姓。他们不是“法官”,因为雅典的法庭压根就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专业资质的法官(当然也没有律师);他们也不是“陪审员”,因为既然不存在其他主审官,何来“陪审”之说?这些普通老百姓就是主审官,他们的地位如此之高,以至于古希腊著名的演说家、政治家德摩斯梯尼(前384—前322)对他们说:“我转求于你们,雅典的公民们!在我看来,法庭的权威不仅大于我所在那个德谟区的选民,而且大于议事会与公民大会。这合情合理,因为你们的决定在方方面面都是最公正的。”

法庭是雅典政制中最早民主化的机构,梭伦改革后,审判权就交到了由普通人组成的法庭手中,普通公民可以就行政官的决定提出申诉。克里斯提尼改革前后,开始实行年度候选审判员制:每年选取6000位30岁以上、不欠国家债务的公民为候选审判员。参与法庭工作的年龄要求之所以比公民大会高10岁,很可能是因为雅典人相信,年长的人更明智、更理智。
 今天看来,这种大10岁的年龄要求似乎无关紧要,但在雅典却非同小可。当时的人均预期寿命不会超过25岁。
今天看来,这种大10岁的年龄要求似乎无关紧要,但在雅典却非同小可。当时的人均预期寿命不会超过25岁。
 如果有3万成年公民可以参加公民大会的话,那么符合法庭年龄要求的公民不会超过2万人。换句话说,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符合年龄要求的公民需担任候选审判员,报名的人当然需更多。这么说来,雅典每位30岁以上的公民都可能在一生中不止一次出任审判员。
如果有3万成年公民可以参加公民大会的话,那么符合法庭年龄要求的公民不会超过2万人。换句话说,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符合年龄要求的公民需担任候选审判员,报名的人当然需更多。这么说来,雅典每位30岁以上的公民都可能在一生中不止一次出任审判员。
候选的6000名审判员也许来自10个部落,每个部落600人。这些人都是从自愿报名的人中以抽签的方式选取的。每年名单确定之后,榜上有名的人会聚集起来参加一个仪式,诵读“人民法庭誓言”(Heliastic Oath):宣誓依法依规,或依据自己的最佳判断,无偏无妄地审案。
也许有人会推断,大多数报名的人都来自雅典市区;但现有证据表明,很多人其实来自内陆与沿海。他们一般属于中老年,因为青壮年需以劳力养家糊口,恐怕难以有时间经常参加法庭活动;他们中大多数似乎出身于中下阶层,尤其是公元前451年决定为参与审判工作提供津贴以后。
 这正说明,发放津贴有利于下层阶级参与国家事务。
这正说明,发放津贴有利于下层阶级参与国家事务。
在此后一年中,各种法庭开庭时,都从这6000人中挑选审判员。公元前5世纪时,所有审判员被分为10组,每组600人;这600人分别来自10个部落,每个部落60人。这样,每个组都会有各个部落的代表,避免偏听偏信。10组审判员被分派到10个法庭,任职一年。每个法庭专职负责受理某些类案件。每次开庭前,会事先公布需要多少位审判员。到了开庭日,属于该法庭的审判员如果愿意,可以排队,先到先入。晚到的候选审判员只能等以后的机会。这种安排使贿赂审判员成为可能,因为人们可以事先知道哪些人会审理哪些类案件。受贿的审判员只需早起一点,就可能参与审理相关案件。
为了避免司法腐败,大约从公元前403年起,雅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试图调整为法庭分派审判员的办法。在新制度安排下,审判员不再被分派给某个固定的法庭。新年伊始,所有审判员被分为规模相等的若干个组,每组以一个字母为标记。一共也许有10个组,分别以10个字母代表。每到开庭日,所有审判员(除因病因事请假者外)集合到法庭所在地。然后用两个箱子进行抽签,一个用来抽选审判员组,另一个用来抽选法庭。第一组被抽中的审判员组被分到第一个被抽中的法庭,以此类推。如果当天开庭的法庭不到10个,没被抽中的那些审判员组的成员只得回家,当然也拿不到当天的津贴。
 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事先知道,哪个审判员组将审理哪个案件。不过,这种抽选审判员组的方式恐怕也有被人钻空子的漏洞。因此,不久以后,抽选的方式又变了。
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事先知道,哪个审判员组将审理哪个案件。不过,这种抽选审判员组的方式恐怕也有被人钻空子的漏洞。因此,不久以后,抽选的方式又变了。
大约从公元前370年起,雅典开始使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程序,用抽签机为开庭随机挑选审判员。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描述,这时法庭所在地的布局是:它有10个入口,每部落一个;20个雅典独创的抽签机(kleroterion),每个部落两个;100个小箱子,每个部落十个;此外,每个部落还有两只瓮。在这个区域内,各个法庭用楣石或其他建筑材料隔开。以抽签选取审判员的方式可以说是繁复无比,被亚里士多德详细地记录在《雅典政制》的63—65节中。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描述,这时法庭所在地的布局是:它有10个入口,每部落一个;20个雅典独创的抽签机(kleroterion),每个部落两个;100个小箱子,每个部落十个;此外,每个部落还有两只瓮。在这个区域内,各个法庭用楣石或其他建筑材料隔开。以抽签选取审判员的方式可以说是繁复无比,被亚里士多德详细地记录在《雅典政制》的63—65节中。
 简单说来,抽取方式如下。
简单说来,抽取方式如下。
每位年度后备审判员会配发一块铜质或木制的名牌(pinakion),上面刻有其名字与字母系统前十个字母中的一个。在10个部落中,每个部落里使用每个字母的审判员数目相等。

图1.7 后备审判员的名牌
图片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inakion_Archilochos.jpg。
每到开庭日的早上,每个部落的审判员分别在属于本部落的入口处集合,等待十位执政官抽签,每位执政官负责一个部落。到达后,每位审判员将自己的名牌放入标有他那个字母的箱子里。负责的那位执政官随机从箱子里抽取一个名字,抽中的审判员就是共有该字母的审判员当天值日的“插票者”。他从箱子里把其他人的名牌一一抽出,然后插入抽签机的某一列孔隙。每个部落的两架抽签机分别有五列插名牌的孔隙,共有十列孔隙。每一列包括带有某个字母的所有名牌。但横着看,每一行上的名牌都带有不同的字母。

图1.8 抽签机残片
图片来源:By Marsyas-Own work,CC BY-SA 2.5,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475523。

图1.9 抽签机复制品

图片来源:http://www.agathe.gr/democracy/the_jury.html。
名牌插完后,负责的执政官(或助手)开始在抽签机上放入混在一起的黑白两色骰子(或小球)。在抽签机的一边有一条空铜管,顶部是个漏斗,底部是个曲柄。骰子就混杂地放在漏斗处,让它们随机滑进管道。应放入骰子的数目取决于当天到场了多少审判员,需要多少审判员。一个白骰子意味着选中五位审判员,一个黑骰子意味着排除五位审判员。假如该部落当天应出300位审判员,但有400人到场,执政官应为两个抽签机的每一个准备30个白骰子,10个黑骰子。骰子放好后,摇一下曲柄,出来一个骰子。如果骰子是白色的,插入抽签机第一行孔隙的五位审判员当选。如果再摇一下,出来一个黑色骰子,第二行那五个人就得打道回府。这样不断地摇出骰子,直至抽出当天需要的所有审判员。
这种方法只决定了哪些审判员当日上岗。下一步还需决定的是,他们分别去哪个法庭?为此,在两只瓮中放入一些标有不同字母的小球,每个字母代表不同的法庭。当天早上的另一次抽签已决定哪个字母代表哪个法庭。抽选出来的每位审判员依次从瓮中随机捞出一个小球,并依据小球上的字母被分派至某个法庭。捞出小球后,他会得到一支授权他进入特定法庭的、加色的小棍(不同的法庭使用不同的颜色),并立即进入该法庭,以免任何人对他进行贿赂。

到了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法庭运作机制的另一环节也加入了抽签的成分。在此之前,负责将某类案件提交法庭的行政官总是使用同一法庭。但就在亚里士多德写作《雅典政制》(大约前328—前325)之前,这种做法被每天用抽签方式分派法庭取代。
上面描述的过程实际上设置了4次叠加随机抽选。第一次是把名牌插入抽签机时;第二次是摇骰子时;第三次是从瓮中抽球为审判员分派法庭时;第四次是为案件分派法庭时。有了这四重保障,大概没有人可以预测哪位审判员当天会上岗,到哪个法庭去上岗,案件由那个法庭审理。司法腐败的可能性因而被大大降低。这样的法庭赢得了雅典人民的信赖,在他们看来,与由少数专职官员断案相比,由大批与自己相似的审判员审案,出错的可能性小得多。

除了审理司法案件外,6000位候选审判员还可能担负立法重任。前面提到,公元前402年以后,制定或修订法律的权力落到了立法委员会肩上。而立法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以抽签的方式从6000名年度候选审判员中选取的,它们没有固定的成员,都是委员会开会当天早上抽选的。抽选的方法与为开庭随机挑选审判员的方式一模一样,也需使用审判员的名牌。
 有学者认为,立法委员会的成员不一定必须是候选审判员,任何报名的雅典公民都有机会。但无论如何,甄选的方式依然是随机抽签。
有学者认为,立法委员会的成员不一定必须是候选审判员,任何报名的雅典公民都有机会。但无论如何,甄选的方式依然是随机抽签。
 立法委员会的规模不小,恐怕最少500人,往往是1001人以上。
立法委员会的规模不小,恐怕最少500人,往往是1001人以上。
 一年以内,为了制定或修订法律,也许有必要频繁组建立法委员会,大概每月一次。
一年以内,为了制定或修订法律,也许有必要频繁组建立法委员会,大概每月一次。
 这样,也许几乎每位候选审判员都有机会参加立法工作。
这样,也许几乎每位候选审判员都有机会参加立法工作。
雅典之所以会让如此多的普通人以如此繁复的方式参与法庭的司法与立法工作,想必是为了凸显6000位候选审判员代表的就是全体雅典公民。正因为他们代表了人民,审判员的判决就是最终判决,不可以再提起上诉。

拥有庞大规模审判员队伍的法庭是雅典政制的一个显著特点。与法庭相比,议事会规模小得多,只有500人;但与其他议事会相比,雅典民主制下的议事会就不算小了。
议事会这种组织形式在古代和现代都很常见,它既可以存在于民主制下,也可以存在于寡头制下。在雅典演化为民主制之前与之后的地中海地区,在中世纪德语地区,在意大利城邦,议事会随处可见,其中绝大多数是寡头制的产物,它们的成员一般很少,聚集其中的人非贵即富。只要规模不大,不管其成员是由世袭、提名(cooptation)、票选产生,还是抽选产生,议事会都不大可能具有民主功能。世袭、提名自不待言,票选的小型议事会也会让野心家趋之若鹜,尤其是在存在巨大经济社会差别的情况下。要钱有钱、要关系有关系、要口才有口才、要长相有长相、要能耐有能耐的他们打起选战来,别人岂是对手。
 哪怕是抽选,一个人数太少的议事会也难以代表全体公民。因此,无论这类小型议事会起初是什么性质,最终它们都或迟或早会被社会精英阶层捕获,被这些人把持。
哪怕是抽选,一个人数太少的议事会也难以代表全体公民。因此,无论这类小型议事会起初是什么性质,最终它们都或迟或早会被社会精英阶层捕获,被这些人把持。
与寡头制下的议事会相比,民主制下的议事会往往规模大得多。梭伦建立的400人议事会就远大于雅典此前的任何议事会。克里斯提尼的民主改革又将其规模扩大到500人。
 但规模大只是议事会具有民主性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对雅典这么一个城邦而言,议事会规模达到500人已确实不小,但它毕竟不是全体公民都可以参加的公民大会。它只能协助公民大会治理城邦,而不能取代公民大会,或者篡夺公民大会的权力。如此一来,雅典民主制的设计者(也许不是个别聪明人,而是群策群力)就面临一个两难课题:一方面,为了更有效地运作,履行它所承担的各项职能,议事会规模不宜再进一步扩大了;另一方面,为了维护体制的民主性,要从制度上防范议事会蜕化为少数精英的俱乐部,变成公民大会的对立面。抽选再一次成为雅典解决难题的方法。
但规模大只是议事会具有民主性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对雅典这么一个城邦而言,议事会规模达到500人已确实不小,但它毕竟不是全体公民都可以参加的公民大会。它只能协助公民大会治理城邦,而不能取代公民大会,或者篡夺公民大会的权力。如此一来,雅典民主制的设计者(也许不是个别聪明人,而是群策群力)就面临一个两难课题:一方面,为了更有效地运作,履行它所承担的各项职能,议事会规模不宜再进一步扩大了;另一方面,为了维护体制的民主性,要从制度上防范议事会蜕化为少数精英的俱乐部,变成公民大会的对立面。抽选再一次成为雅典解决难题的方法。

议事会的500位成员分别来自10个部落,每个部落有50个名额。这50人在每个部落内的3个三一区之间并不是平均分配的,因为议事会成员的名额分配单位是那139个“德谟”。各个德谟分到的名额与其人口规模成比例。德谟人口越多,议事会成员名额越多;反之,德谟人口越少,名额越少。大约有40个德谟人口不多,它们各自只分到了1个议事会名额。但也有些德谟人口众多。这样的德谟有8个,它们每个分到10个或更多议事会席位。最大的一个德谟自成一个三一区,它独享22个议事会席位。但到了部落层面,来自3个三一区的议事会成员加在一起只能是50名。
 下面是潘狄俄尼斯部落(Pandionis)50位议事会成员名额在11个德谟中的分布图(见图1.10)。
下面是潘狄俄尼斯部落(Pandionis)50位议事会成员名额在11个德谟中的分布图(见图1.10)。

图1.10 潘狄俄尼斯部落50位议事会成员名额在某年的分布图
图片来源:Josiah Ober, “Epistemic Democracy in Classical Athens: Sophistication, Diversity, and Innovation,” in Hélène Landemore, Jon Elster, eds. , Collective Wisdom: Principles and Mechanism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32。
与雅典其他所有公职一样,议事会成员的任期只有一年。但与雅典其他一些公职不同,每位公民一生中最多可以担任两次,而不是一次议事会成员;不过不得连续两届连任。现实中,担任过两次议事会成员的人并不多。

在每个德谟里,设定的抽选范围有这么几个条件。
第一,年龄限制。只有30岁以上的成年公民才有机会进入议事会,与审判员相同。实际上,议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是约40岁。

第二,等级限制。无论是梭伦的400人议事会,还是克里斯提尼的500人议事会,只有出身于头三个公民等级,也就是具备一定财产资格的公民才有机会进入议事会。这样规定的理由也许是因为,制度设计者认为,只有这些拥有财产、为重装步兵提供装备的公民才有兴趣维护城邦的良治。当然,头三个等级未必都是贵族或富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普通人,由他们出任议事会,代表的不仅仅是上层精英。但不管怎么说,处于最低等级的公民则被排斥在外。这类人很多,也许占到雅典全体公民的一半以上,他们无缘成为议事会成员。假设有3万成年公民,头三个等级的公民约1万至1.5万人,其中30岁以上只有5000—7500人。简单计算告诉我们,如果只允许公民一生中担任一次议事会成员,即使所有人都愿意担任这种公职,10—15年后,就没有人可以出任议事会了。这大概是为什么允许公民一生中担任两次议事会成员的原因。即便如此,每位合资格公民每隔10至15年就得出任一次议事会成员,围绕议事会席位的竞争不可能非常激烈。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之前,这种制度安排还有足够的人力支撑。

不过,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其间的瘟疫造成了人口大量减少。有人估计成年男性公民从战前的40 000人降至战后的14 000—16 250人;
 也有人估计其间成年男性公民的数量是从60 000人降至25 000人。
也有人估计其间成年男性公民的数量是从60 000人降至25 000人。
 虽然估算的具体数目各异,但有一点很清楚,雅典公民人数下降了60%左右。我们知道,到公元前4世纪,关于议事会成员的等级限制不再适用:所有公民都有机会成为议事会成员,包括处于底层的第四等级公民。但我们不知道,这个变化是何时开始的。有人模糊地提到变化发生在阿里斯提德(前530—前468)时代以后,
虽然估算的具体数目各异,但有一点很清楚,雅典公民人数下降了60%左右。我们知道,到公元前4世纪,关于议事会成员的等级限制不再适用:所有公民都有机会成为议事会成员,包括处于底层的第四等级公民。但我们不知道,这个变化是何时开始的。有人模糊地提到变化发生在阿里斯提德(前530—前468)时代以后,
 但一般认为,变化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
但一般认为,变化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
 不清楚人口在公元前5世纪末大幅减少是不是也是产生这个变化的一个原因。
不清楚人口在公元前5世纪末大幅减少是不是也是产生这个变化的一个原因。

第三,自愿报名。关于这一点仍存在争议。有些研究认为,抽签并不是在所有符合年龄与等级条件的公民中进行;合资格公民还需报名,才会进入抽签名单。
 但也有研究相信,自愿报名并不是必要条件。
但也有研究相信,自愿报名并不是必要条件。

可以想象,每个德谟也许都希望挑选出比较成熟、比较有政治经验的人代表自己出任议事会;它们也许会鼓动这类人报名。如果有意愿担任议事会成员的人数与德谟分到的名额相等,则皆大欢喜,但这种可能性也许不大。如果有意愿担任议事会成员的人数比该德谟分到的名额多,就得进行甄选。雅典的做法不是通过竞选、票选的方式从中做出挑选,而是会进行随机抽选。我们并不清楚知道抽选到底如何进行:是从自愿报名的合资格人士中进行抽选,还是从德谟内所有合资格人士中进行抽选?是各个德谟分别进行抽选,还是所有德谟集中到一处(忒修斯神庙),然后各自抽选?
 是用不同色彩的豆粒进行抽选,
是用不同色彩的豆粒进行抽选,
 还是使用名牌进行抽选?
还是使用名牌进行抽选?
 这也许意味着,就抽签技术而言,其方式与挑选审判员的方式不大一样。
这也许意味着,就抽签技术而言,其方式与挑选审判员的方式不大一样。
其实,当各个德谟进行抽选时,抽出的人数并不是它们应选的人数,而是应选人数的两倍,其中一半是当选者,另一半是候补者;每位当选者搭配一位候补者。如果当选者身亡或疾病缠身,候补者可以顶替。
 还有一种可能性,当选者未必能通得过官方的资格审查。议事会新任成员的资格审查由上一任议事会负责,会查验当选者是否雅典公民、是否30岁以上、是否曾经担任过议事会成员、担任过几届等。除了满足法律要求之外,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同样重要:是否虐待过父母、是否逃避过兵役、是否遗弃过自己的盾牌、是否挥霍过自己继承的遗产、是否有私生子等等,都可能是考察议事会成员资格的标准。进入议事会的应是一群好公民。如果当选者未能通过资格审查,候补者就要替补上场了。
还有一种可能性,当选者未必能通得过官方的资格审查。议事会新任成员的资格审查由上一任议事会负责,会查验当选者是否雅典公民、是否30岁以上、是否曾经担任过议事会成员、担任过几届等。除了满足法律要求之外,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同样重要:是否虐待过父母、是否逃避过兵役、是否遗弃过自己的盾牌、是否挥霍过自己继承的遗产、是否有私生子等等,都可能是考察议事会成员资格的标准。进入议事会的应是一群好公民。如果当选者未能通过资格审查,候补者就要替补上场了。

抽选出来的议事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雅典人民呢?就各德谟而言,代表性应该不错,因为每个德谟都在议事会有其代表;而且代表的数量与其人口成正比。就各地区而言,城区、沿海与内陆也都有代表,分配比例似乎也不算离谱。
 如果只看这两方面,议事会可以说是“城邦的缩样”(polis inminiature)。
如果只看这两方面,议事会可以说是“城邦的缩样”(polis inminiature)。

但就各阶级而言,情况则较为复杂。毫无疑问,富裕阶层占有优势,理由很简单:虽然议事会成员可以按天领取活动津贴,但津贴的数额比非熟练劳动力一天的工钱还少。对需养家糊口的大多数男人来说,频繁参加议事会活动必然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尤其是对于囊中羞涩的穷人来说,放弃正常职业,担任一年议事会成员实在是牺牲太大。因此,穷人自愿报名参与议事会成员抽选的积极性很可能比富人小得多。有证据表明,议事会成员中,拥有财产的人确实比例较高。但与此同时,名单中也有一些人纯属无名之辈。
 这说明,议事会不可能完全被最富有的一小撮人控制,不同阶层在其中都有自己的代表。
这说明,议事会不可能完全被最富有的一小撮人控制,不同阶层在其中都有自己的代表。
 有学者认为,即使在成员的阶级构成上,也可以说议事会是“城邦的缩样”。
有学者认为,即使在成员的阶级构成上,也可以说议事会是“城邦的缩样”。

议事会成员在阶级之间的分布之所以不如在德谟与地区之间的分布均匀,其主要原因与主动报名的要求有关。这一要求偏向富有阶层,使得候选人群体中拥有财富的人比重较大,而抽签本身不会偏向任何阶层。不过,自愿报名也许并不总是参与抽选的条件;在有些情况下,德谟可能会施加有形或无形的压力,迫使不自愿的人也参与抽选。厌烦参与议事会活动的苏格拉底曾担任过议事会成员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
 还有一种可能,在某些时段,抽选也许不是在自愿报名的人中进行,而是在德谟内所有合资格人士中进行。
还有一种可能,在某些时段,抽选也许不是在自愿报名的人中进行,而是在德谟内所有合资格人士中进行。
 当抽选是在所有合资格人士中进行时,所产生议事会成员的阶级构成应会更加平衡一些。
当抽选是在所有合资格人士中进行时,所产生议事会成员的阶级构成应会更加平衡一些。
一届议事会形成后,内部会组建一些小组委员会,处理对雅典整体利益至关重要的行政事务,如负责对官员在职行为进行审查的审计委员会,负责查验所有官员账目的会计委员会,负责确保公职人员对雅典人民尽责的专门委员会,负责雅典海上力量维护与训练的专门委员会,负责主持重要宗教仪式的专门委员会等。所有这些小组委员会都是从全体议事会成员中抽签选取的。
 议事会还需每隔35—36天产生一个主席团,主持议事会与公民大会工作;主席团形成后,还需每天产生一位执行主席,主持当天的各项活动。主席团与执行主席也是经由抽签选出的。后来出现的九人委员会也同样经过抽签选出。与法庭一样,议事会从组成到运作几乎样样事情都与抽签分不开。
议事会还需每隔35—36天产生一个主席团,主持议事会与公民大会工作;主席团形成后,还需每天产生一位执行主席,主持当天的各项活动。主席团与执行主席也是经由抽签选出的。后来出现的九人委员会也同样经过抽签选出。与法庭一样,议事会从组成到运作几乎样样事情都与抽签分不开。
议事会在雅典政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抽选、定期轮换、限定任期等措施确保其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鲜有职业政治家。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雅典成年男性公民一生中都有机会成为议事会成员;在他们担任议事会成员期间,来自每个部落的人都有机会参与主席团工作;在来自某个部落的人担任主席团成员期间,绝大多数人(50人中的35人以上)都有机会在某日成为执行主席,主持议事会活动、主持公民大会(如果凑巧那天公民大会开会的话)、在国事活动中占据首席、会见外国来宾、执掌国库钥匙。这是一个相当于现代国家元首的职位。换句话说,绝大多数雅典成年男性公民一生中都有机会担任国家元首,哪怕只有一天。这在所谓现代“民主”社会中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种抽选加轮替的制度安排完全消除了任何部落、任何地区、任何一群人垄断议事会的可能性。如果说公民大会有全体公民参与的话,议事会同样也有全体公民的参与,只不过是以轮流参与的方式实现而已。批评雅典民主的人也许会说,这种制度安排使得任何人都无法积累丰富的统治经验与才干。但反过来,支持雅典民主的人会说,这种制度安排使得所有公民都有机会学习如何治国理政,都有机会建立跨越本德谟、本部落的社会网络。即使担任执行主席、主席团成员、议事会成员的时间不长,卸职之后,这些普通老百姓依然可以用其他方式把学到的经验、建好的人际网络运用到参政议政、当家做主中去。

所谓“公职人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指那些“在一定范围以内具有审议、裁决和指导责任”的人,其主要标志是具有“指挥权力”。
 严格地说,议事会成员也属公职人员,不管是在《雅典政制》中还是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都把议事会放在公职人员部分加以讨论,并多次指出,民主制下的议事会是公职人员的关键组成部分。
严格地说,议事会成员也属公职人员,不管是在《雅典政制》中还是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都把议事会放在公职人员部分加以讨论,并多次指出,民主制下的议事会是公职人员的关键组成部分。
 这里所谓“其他公职人员”,指议事会成员之外的那些公职人员,他们的使命是执行公民大会或法庭制定的法律与法令,仅仅可以做一些初步的裁决,但不享有裁决权。
这里所谓“其他公职人员”,指议事会成员之外的那些公职人员,他们的使命是执行公民大会或法庭制定的法律与法令,仅仅可以做一些初步的裁决,但不享有裁决权。

担任公职人员的最低年龄与议事会成员相同,都是30岁。
 与现代的政府职位不同,雅典的公职不一定是全职工作。在公元前4世纪,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公职人员是全职,其余是兼职。在公职是否受薪问题上存在争议,但有理由相信,履行公职可以获取相应报酬。
与现代的政府职位不同,雅典的公职不一定是全职工作。在公元前4世纪,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公职人员是全职,其余是兼职。在公职是否受薪问题上存在争议,但有理由相信,履行公职可以获取相应报酬。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取得津贴,穷人才有闲暇参政。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取得津贴,穷人才有闲暇参政。
 否则,担任公职只是有钱人的奢侈品。而像雅典这样的民主政体的一个特征便是,“最好是一切机构(如公民大会、法庭、行政机构)全都给予津贴;若实在不行,那么行政官员、法庭、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主持者或者至少是那些必须要在一起用餐的官员应该得到津贴。”
否则,担任公职只是有钱人的奢侈品。而像雅典这样的民主政体的一个特征便是,“最好是一切机构(如公民大会、法庭、行政机构)全都给予津贴;若实在不行,那么行政官员、法庭、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主持者或者至少是那些必须要在一起用餐的官员应该得到津贴。”

关于这些公职人员的规模、类别、产生办法,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一书中有大篇幅的讨论。
就规模而言,按《雅典政制》的说法,“邦内官员达700人,邦外官员亦达700人”。
 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一一点算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提供的各种职位数目,然后加总,得出雅典只有大约50类公职、350位相关人员的结论(见表1.1)。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雅典政制》几乎涵盖了所有公职,很少遗漏。
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一一点算亚里士多德在书中提供的各种职位数目,然后加总,得出雅典只有大约50类公职、350位相关人员的结论(见表1.1)。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雅典政制》几乎涵盖了所有公职,很少遗漏。
 但汉森认为,这个假设并不成立。他从文献与考古碑文材料中梳理出另外20多类公职,大约100多个职位。再加上其他可能的遗漏,汉森认为,说雅典有600—700位公职人员并不离谱。
但汉森认为,这个假设并不成立。他从文献与考古碑文材料中梳理出另外20多类公职,大约100多个职位。再加上其他可能的遗漏,汉森认为,说雅典有600—700位公职人员并不离谱。

尽管《雅典政制》对公职的涵盖未必全面,但从表1.1可以清晰看到,公职人员的产生办法大致有三类。
表1.1 《雅典政制》列举的公职


一是抽选,如表1.1中的26类职务,涉及256人,约占表列公职人员总人数的四分之三。有人估计,在雅典700位公职人员中,至少有500人以上是抽选产生的;
 还有人估计,大约有600位是抽选产生的。
还有人估计,大约有600位是抽选产生的。

二是票选,如表1.1中的16类职务,涉及74人,约占表列公职人员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三是委任,如3位主要执政官“按其意愿每人挑选两名助理”;又如执政官“为悲剧委任3名合唱队领班”。前者是辅助性职务,后者是历史遗产,因为《雅典政制》同时指出,以前执政官“还要为喜剧委任5名领班,但如今由各部族来提供这些人”。
 由于委任在雅典民主制下十分少见,涉及的公职与人员不多,且指挥权力有限,以下不再讨论。
由于委任在雅典民主制下十分少见,涉及的公职与人员不多,且指挥权力有限,以下不再讨论。
关于抽选与票选,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抽签分派官职被看作是民主的,选举则带有寡头政体的性质。”
 他如此判断的理据很简单:民主政体的宗旨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即只有人民才是自己的统治者。如果无法实现人民直接当家做主的理想,就应该实现轮流统治与被统治。基于这个逻辑,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民主政体下,“所有官职或者所有不要求具有经验和技术的官职,都应该通过抽签来选取;官职完全不应在财产方面有要求,或者只有最低限度的要求;一个人不能两次担任同一官职,只能在少数时候或在少数官职上连任,军职除外;所有官职或所有可能做到这点的官职的任期应该短暂……”
他如此判断的理据很简单:民主政体的宗旨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即只有人民才是自己的统治者。如果无法实现人民直接当家做主的理想,就应该实现轮流统治与被统治。基于这个逻辑,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民主政体下,“所有官职或者所有不要求具有经验和技术的官职,都应该通过抽签来选取;官职完全不应在财产方面有要求,或者只有最低限度的要求;一个人不能两次担任同一官职,只能在少数时候或在少数官职上连任,军职除外;所有官职或所有可能做到这点的官职的任期应该短暂……”
 雅典民主制似乎就是如此运作的。
雅典民主制似乎就是如此运作的。
在雅典民主制下,绝大多数公职人员确实是以抽签的方式产生的。其中最好的例子是10位执政官。
执政官是雅典最古老的官职之一,其数目随时代不断变化。当执政官由一人担当时,他是国王,其职位是世袭的。贵族废黜君主制后,执政官的数目增至3人(即王者执政官、军事执政官和名年官),由贵族选举产生,其入选的门槛是门第高贵及富有;起初他们任职终身,后来任期缩短为10年,继而缩短为1年。
 公元前7世纪末,执政官数目增至9人(新增6位司法执政官),由战神山会议确定各个职位的人选。
公元前7世纪末,执政官数目增至9人(新增6位司法执政官),由战神山会议确定各个职位的人选。

梭伦改革引入了两方面的变化。首先,它放宽了担任执政官的资格。以前只有出身贵族才能担任执政官,梭伦以灵活的财产资格代替了僵硬的贵族资格:在四个财产等级中,头两个等级的人都可以担任执政官,这使得执政官的大门同时向贵族与其他有产者敞开。其次,仅仅放宽当选资格并不够。假如沿用此前的选人办法,战神山会议依然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把非贵族人士排除在外。这样,梭伦改革的配套方案也同样重要:“他规定各类官职从各部族预先选出的候选人中经抽签而定。每一部族预先选出10位候选人以角逐9名执政官的职位,再从这些候选人中抽签而定。”
 当时雅典有四个部落,各部落票选出来的候选人加在一起达40人之多,是应当选人数的4倍多,当选概率是22.5%。只要票选出来的候选人包括非贵族出身的人士,谁也无法操控其后的抽选结果。可见引入抽选成为抑制战神山会议权势的利器。
当时雅典有四个部落,各部落票选出来的候选人加在一起达40人之多,是应当选人数的4倍多,当选概率是22.5%。只要票选出来的候选人包括非贵族出身的人士,谁也无法操控其后的抽选结果。可见引入抽选成为抑制战神山会议权势的利器。
后来,僭主政治时期,票选曾一度回潮,取代了抽选。显然,僭主们很清楚,他们可以玩票选于股掌之间;但抽选却可能让他们鞭长莫及。
据《雅典政制》记录,在公元前487年,挑选执政官的方式又改回为抽签。此时,雅典已由4个部落重划为10个部落。为了实现部落平等,执政官的总数也增至10人,即9人组成的执政官委员会外加一位司法执政官秘书。抽选分两阶段:先由每一部族预选出50位候选人,角逐执政官的职位;然后从这500名候选人中抽签决定由谁担任10位执政官。

这个新制度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每个部落的50位候选人实际上是进一步下放到德谟一级选出的。
 500人分散到139个德谟,这意味着每个德谟需推选的人并不多,其分布也许与议事会成员在各德谟的分布相近,从1人到22人不等。
500人分散到139个德谟,这意味着每个德谟需推选的人并不多,其分布也许与议事会成员在各德谟的分布相近,从1人到22人不等。
 由于当时担任执政官的财产资格仍停留在头两个等级,再加上不排除有人无意担任执政官,合资格的候选人在每个德谟更少,这使得在这个层级上进行推选比较容易操作。第二,不管各个德谟分配到多少候选人,每个部落最终只能推选出50名候选人。第三,应选人数与候选人数之比从梭伦时代的22.5%大幅降至2%,使操控结果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第四,抽选必须做出特殊安排,使得每个部落只能产生一名执政官,以实现部落之间的平等。第五,除了数目平等外,还需实现职位分配的平等:每年各种执政官职位在10位当选者之间的分配也由抽签决定,以确保所有部落都有机会推出担任权力比较大的执政官。在执政官中,权位最重的恐怕是名年官,其次是王者执政官,最后一名是司法执政官秘书。
由于当时担任执政官的财产资格仍停留在头两个等级,再加上不排除有人无意担任执政官,合资格的候选人在每个德谟更少,这使得在这个层级上进行推选比较容易操作。第二,不管各个德谟分配到多少候选人,每个部落最终只能推选出50名候选人。第三,应选人数与候选人数之比从梭伦时代的22.5%大幅降至2%,使操控结果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第四,抽选必须做出特殊安排,使得每个部落只能产生一名执政官,以实现部落之间的平等。第五,除了数目平等外,还需实现职位分配的平等:每年各种执政官职位在10位当选者之间的分配也由抽签决定,以确保所有部落都有机会推出担任权力比较大的执政官。在执政官中,权位最重的恐怕是名年官,其次是王者执政官,最后一名是司法执政官秘书。
 第六,由于是采取初选票选、终选抽签搭配,这种挑选执政官的方式仍具有民主与寡头混合的性质。
第六,由于是采取初选票选、终选抽签搭配,这种挑选执政官的方式仍具有民主与寡头混合的性质。

后来,初选从德谟一级提升至部落一级;再往后,初选的方式也从票选改为抽选。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执政官的产生方式已采取双重抽选:先在10个部落各自分别抽选出10位候选人;然后再从100位候选人中抽选出10位执政官,每个部落1位。这种双重抽选实际上是一种双保险,有助于确保无论是在部落一级,还是在城邦一级,都没人可以通过耍花招的方式篡取执政官的职位。

从表1.1还可以看出,不仅执政官是由10人组成的,雅典很多其他类别的公职人员也是由10人或5人组成,前者是每个部落每年出1人,后者是每个部落每隔一年出1人。在26类由抽选产生的职务中,18类属于这两种类型,涉及256人中的165人(64.5%)。所有抽选产生的职务任期都只有一年,唯一的例外是主管泛雅典娜节游行、音乐比赛、体育比赛及赛马的主赛人可以任职4年。不论哪种职务,每个人一生中只能担任一次,不得连任。在这10个人或5个人内部,没有上下级之分,没有这个“长”那个“长”,因为他们同时履职,没有资历的差别。他们都是一个个分工不同的整体。
按《雅典政制》的说法,抽选原本在不同层级进行,比较重要的职位从整个部落中抽签选出,不那么重要的职位从各个德谟中抽签选出。但后来由于某些德谟开始出售官职,抽选便基本上都集中到了部落一级,只有极少例外。

行政官抽选到底采取哪些具体步骤并不清楚。但依据考古发现的抽签片,有人推测这也是一种双重抽选。首先在忒修斯神庙进行一次初步抽签,其目的不是抽出当选人,而是确定哪一个职位将出自哪一个德谟或部落。第二次抽选将在选中的德谟或部落进行,它们负责收集该职位的全部合资格报名者名单,并从中抽签选出最终获胜人。如果第二次抽选的单位是德谟,由于德谟内合资格人士的数目有限,可以想象,某些富有的报名者可以买通其他潜在报名者退选,以增大自己当选的机会。这也许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出售官职”。在第二次抽选的单位提升至部落后,合资格报名者的数目会大幅度增加,在抽选中靠取巧获胜的机会肯定会相应大跌。这种双重抽选程序还有一个优势:它很容易执行一人不得多次担任某职务的禁令:只要在第二次抽选的合资格报名者中排除曾经担任过该职务的人即可。


图1.11雅典的抽签片
图片来源:http://www.agathe.gr/democracy/political_organization_of_attica.html。
至于抽选工具,早期使用的是盛有黑、白豆粒的容器,白色豆粒的数目等于应选人数,黑、白两色豆粒的总数等于候选人数,抽到白色豆粒者中选。到公元前4世纪,抽签机开始得到广泛运用。考古发现的抽签机形状基本相同,但大小不一,插名牌孔隙的行数与列数各异,显然用于不同类型的抽选。除了前面描述过那种用于审判员的抽签机外,估计也有专门用于抽选各类行政官的抽签机。
在雅典民主制下,抽选是常态。但只要是常态,就会有例外。在雅典,例外是仍有一部分公职人员由票选的方式产生,包括两大类职务:与军事指挥相关的职务、与财务相关的职务,其中最重要的职务是十将军(见表1.1)。
 这些都是一些需要特殊才能与技能的职务,假如只讲民主理念,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担任这些职务的人,恐怕他们难以胜任这些关键职务。票选职位的存在说明,雅典既信守民主理念,又实事求是。
这些都是一些需要特殊才能与技能的职务,假如只讲民主理念,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用抽签的方式产生担任这些职务的人,恐怕他们难以胜任这些关键职务。票选职位的存在说明,雅典既信守民主理念,又实事求是。
下面以十将军为例介绍一下雅典的票选。按《雅典政制》的记载,公元前501年以前,十将军分别由10个部落各自选出,每个部落一人。此后则改由公民大会通过举手表决,选出所有军事官员,包括十名将军,不过依然是每一部落选一人。
 公元前5世纪中期,十将军的挑选方式再次出现重大变化,使得某一部落可以同时有多于一人担任将军。票选方式具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并不清楚,但在公元前441年至前5世纪末,至少可以确定六桩某部落在同一年内有两人出任将军的事例,甚至出现过同一年有两个部落分别有两人出任将军的情况。雅典此时处于战争状态也许是这个变化的原因。我们知道,在公元前444—前430年间,伯利克里(Pericles,约前495—前429)曾连续多年出任将军。如果沿袭以前的制度,在此期间,伯利克里所在部落的任何人都没有机会担任将军,无论他们军事指挥才能有多高。这种选举规则的变化可能意在让那些能力超凡的将军得以连选连任,但又不至于剥夺同族其他人出任将军的机会。不过,这种变化未必意味着部落平等原则已被打破,因为某部落在同一年有多于一人担任将军的情况毕竟是例外,而不是常态。
公元前5世纪中期,十将军的挑选方式再次出现重大变化,使得某一部落可以同时有多于一人担任将军。票选方式具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并不清楚,但在公元前441年至前5世纪末,至少可以确定六桩某部落在同一年内有两人出任将军的事例,甚至出现过同一年有两个部落分别有两人出任将军的情况。雅典此时处于战争状态也许是这个变化的原因。我们知道,在公元前444—前430年间,伯利克里(Pericles,约前495—前429)曾连续多年出任将军。如果沿袭以前的制度,在此期间,伯利克里所在部落的任何人都没有机会担任将军,无论他们军事指挥才能有多高。这种选举规则的变化可能意在让那些能力超凡的将军得以连选连任,但又不至于剥夺同族其他人出任将军的机会。不过,这种变化未必意味着部落平等原则已被打破,因为某部落在同一年有多于一人担任将军的情况毕竟是例外,而不是常态。
 然而到了公元前357—前328年,部落平等的原则可能被彻底放弃了,《雅典政制》第61章说,十位将军由“全体人民”选举,也可以这么解读。
然而到了公元前357—前328年,部落平等的原则可能被彻底放弃了,《雅典政制》第61章说,十位将军由“全体人民”选举,也可以这么解读。

抽选与票选是完全不同的游戏,其中的玩家也大不相同。在抽选游戏中,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票选游戏中,才能与技能固然重要,但出身、财富、人脉、经历、声誉、相貌、口才都有助于当选。抽选的玩家是普通人,是无名之辈;而票选的玩家往往是精英,是出类拔萃之辈。在抽选中,人人都有当选的可能;而在票选中,只有极少数人是有当选机会的幸运儿。
正是因为票选具有内在的精英化倾向,雅典民主不仅对这种游戏规定了不大的适用范围(抽选是常态,票选是例外),而且外加了其他限制条件。如每年担任将军职务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十个人。即使是声望最高的将军,也必须与来自其他部落的同事们一起集体履行其职责。不仅票选出来的将军如此,其他票选出来的官员也大多如此。我们在表1.1中看到,在票选产生的16类职务中,有6类由10人组成,基本上都是每个部落每年出1人,涉及74人中的60人,比重高达81.1%,高于抽选出来的那些官员。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雅典在公职分配上同时坚守了民主的两个原则:参与性与代表性。
就参与性而言,稍加计算,我们就会发现,在雅典民主制下,除参加公民大会和担任审判员以外,很大比例的公民都有机会担任公职。假设公元前4世纪雅典有3万成年男性公民,其中大约2万人年满30岁,够资格担任公职。在2万人中,每年需要1200人担任公职,包括500位议事会成员,外加700位其他公职人员。除少数例外,每种职位的任期是一年,且不准连任(议事会成员可以任职两届)。这样,几乎每位公民一生中或迟或早都有机会担任公职,而且可能不止一次(不包括担任审判员)。由此形成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全体公民轮流担任公职的局面:今年我是木匠,明年我出任公职,此后我又回到老本行。担任公职时,我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退出公职后,我服从在职者的指挥。担任公职时,我荣耀,受到他人的尊重;退出公职后,我没有怨言,尊重那些行使权力的人;每个人都能上能下、进退自如。回到老本行后,每天打交道的公职人员就是我的街坊、亲戚、同行、熟人、朋友;即使不认识他们,但我很清楚,他们就是与我一样的普通人,没有任何神秘感、距离感。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是亦民亦官,没有僵死的分工;每个人都是被统治者,每个人也是统治者。不存在“公”与“私”的严格分界,不存在“政府”与“非政府”的严格分界,不存在职业官员与普通民众的严格分界。城邦政府即是城邦公民,城邦公民即是城邦政府,两者浑然一体,难解难分。这种政府不是高高在上的政府,不是让人感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政府,而是自家的政府、亲近的政府。公职的广泛参与性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亚里士多德把担任公职作为定义“公民”的要件:能担任公职的人才是公民;是公民才能担任公职。

就代表性而言,政府多数职务由来自各个部落的人共同承担,而不是由某些个人独占。即使某些职务只需要一个人,这些职务往往由来自各个部落的人轮流担任。多人同时或轮流分享某项权威不仅可以防止腐败,而且有利于培养合作、协商精神,有利于强化人民主权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