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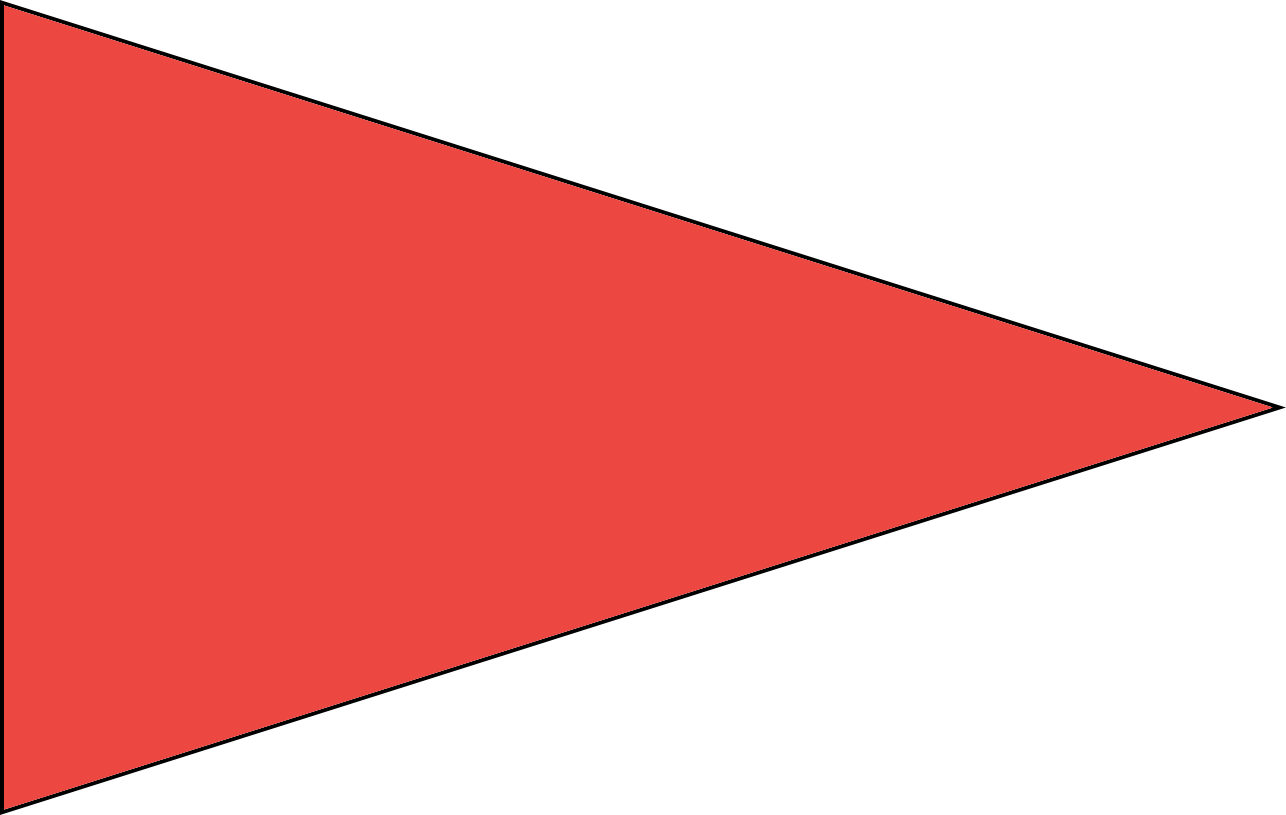 第七章
第七章

次日下午,我从我们在山间的第一个救护车站回到镇上,把车停在医疗后送站
 。在那里,人们会根据伤病员的病历对其分类,然后在他们的病历上注明将去的医院。那天一直由我开车。这时,我坐在车里,驾驶员把伤病员的病历送进站。天气很热,蔚蓝的天空一片晴朗,发白的马路满是尘土。我坐在菲亚特救护车
。在那里,人们会根据伤病员的病历对其分类,然后在他们的病历上注明将去的医院。那天一直由我开车。这时,我坐在车里,驾驶员把伤病员的病历送进站。天气很热,蔚蓝的天空一片晴朗,发白的马路满是尘土。我坐在菲亚特救护车
 高高的座位上,脑中一片空白。一个团沿路走来,我看着他们经过,人人热得大汗淋漓。有些人头戴钢盔,但大部分人把钢盔挂在背包上。钢盔大都过大,几乎盖住佩戴者的双耳。军官都戴着钢盔——他们的钢盔大小比较合适。巴西利卡塔旅
高高的座位上,脑中一片空白。一个团沿路走来,我看着他们经过,人人热得大汗淋漓。有些人头戴钢盔,但大部分人把钢盔挂在背包上。钢盔大都过大,几乎盖住佩戴者的双耳。军官都戴着钢盔——他们的钢盔大小比较合适。巴西利卡塔旅
 一半的兵力都在这了。一看红白条纹的领章就知道他们属于那个旅。整支队伍过去很久以后,又走来几波没跟上所在队伍的掉队散兵。他们汗流浃背,灰头土脸,疲惫不堪,有些人看上去状况非常不妙。最后一波散兵经过后,出现一名形单影只的士兵。他一瘸一拐地走来,接着停下脚步,在路边坐下。我跳下车,走了过去。
一半的兵力都在这了。一看红白条纹的领章就知道他们属于那个旅。整支队伍过去很久以后,又走来几波没跟上所在队伍的掉队散兵。他们汗流浃背,灰头土脸,疲惫不堪,有些人看上去状况非常不妙。最后一波散兵经过后,出现一名形单影只的士兵。他一瘸一拐地走来,接着停下脚步,在路边坐下。我跳下车,走了过去。
“怎么回事?”
那人看着我,站了起来。
“我马上就走。”
“到底怎么了?”
“——战争。”
“你的腿怎么了?”
“不是腿的问题。我得了疝气。”
“为什么不坐车呢?”我问,“为什么不上医院呢?”
“他们不让。中尉说我故意丢掉疝气带
 。”
。”
“让我摸摸看。”
“鼓得非常大。”
“在哪边?”
“这边。”
我摸了摸。
“咳嗽一下。”我说。
“我怕这会让它变得更大。现在已经比早上大了一倍。”
“坐着休息一下。”我说,“一拿到伤员的病历,我就带你赶上大部队,把你交给你们的医务官。”
“他会说我是故意丢掉疝气带的。”
“他们不能拿你怎么样。”我说,“这又不是外伤。你以前就得过疝气,对吗?”
“可我弄丢了疝气带。”
“他们会送你上医院的。”
“我不能留在这里吗,中尉
 ?”
?”
“不行。我没有你的病历。”
驾驶员拿着车上伤员的病历,从医疗后送站的大门出来了。
“四个到105医院,两个到132医院。”驾驶员说。这两所医院位于河对岸。
“你来开车。”说完,我扶患疝气的士兵上车,让他跟我们坐在一起。
“你会说英语?”士兵问。
“当然。”
“你怎么看这场该死的战争?”
“烂透了。”
“烂透了。天哪,真的烂透了。”
“你在美国待过?”
“是啊,在匹兹堡待过。我知道你是美国人。”
“因为意大利语说得不够好?”
“我非常肯定你是美国人。”
“又一个美国人。”驾驶员看着得疝气的士兵,用意大利语说。
“对了,中尉
 ,你非得把我送到那个团里去吗?”
,你非得把我送到那个团里去吗?”
“是的。”
“那个团的上尉医生知道我得了疝气。我丢了该死的疝气带好让疝气变得严重,就不必再上前线了。”
“原来如此。”
“你不能送我去其他地方吗?”
“如果是在前线附近,我可以送你去急救站。但在这里的话,你得有病历。”
“如果回去,他们会对我动手术,然后把我送去前线,永远回不来。”
我仔细想了想。
“你也不想老是待在前线,对吧?”他问。
“不想。”
“主啊,这是一场该死的战争,难道不是吗?”
“听着。”我说,“你下车去,然后故意摔倒在路边,在脑袋上磕个包出来。我们回来时我会捎上你,送你去医院。在这里停一下,阿尔多。”我们在路边停住车,我把那名士兵扶了下去。
“我就在这儿等你,中尉。”他说。
“再见!”我向他道别。我们继续赶路,往前开了大概一英里的时候追上了刚才经过的那个团,接着过了河。浑浊的雪水湍急地从桥墩之间流过。过河后,我们顺着马路穿过平原,把伤员分别送往两所医院。返回时,我驾驶空车飞快赶往约定地点,去接那名在匹兹堡待过的士兵。我们经过了那个团——人人浑身是汗、步履维艰,又经过了那些掉队的散兵,最后看到路边停着一辆救护马车。两人正抬着那名得了疝气的士兵,准备把他放进马车。他们回来找他了。那名士兵冲我摇摇头,他的钢盔掉了,额头发际线下淌着血,鼻子擦破了皮,血淋淋的伤口和头发上沾满尘土。
“瞧我脑门上的包,中尉!”那名士兵喊道,“没什么用,他们回来找我了。”
回到所住的别墅,已是下午五点。我走到外面洗车处,冲了个澡。回到自己房间后,我只穿长裤和背心,坐在打开的窗户前写报告。进攻定于两天后发动,我也将随车队前往普拉瓦。我已很久未给在美国的亲人写信。虽然知道应该写信,但因为一拖再拖,现在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写了。其实也没什么好写的。我曾寄去两三张军方定制的“战地”明信片——划去上面印制的所有条目,只留下“我很好”这一条
 。这应该能敷衍他们了。那些明信片显得既陌生又神秘,在美国可能很受欢迎。这个战区也既陌生又神秘,不过我估计,与史上奥地利的历次战争相比,这次奥地利人已经算得上组织有序、意志顽强。奥地利军队的存在,纯粹是为了给拿破仑——不管哪个拿破仑——增添功绩。真希望我们也有一位拿破仑,但可惜,我们只有肥胖而富有的卡多尔纳将军
。这应该能敷衍他们了。那些明信片显得既陌生又神秘,在美国可能很受欢迎。这个战区也既陌生又神秘,不过我估计,与史上奥地利的历次战争相比,这次奥地利人已经算得上组织有序、意志顽强。奥地利军队的存在,纯粹是为了给拿破仑——不管哪个拿破仑——增添功绩。真希望我们也有一位拿破仑,但可惜,我们只有肥胖而富有的卡多尔纳将军
 和脖颈细长、蓄山羊胡的小个子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
和脖颈细长、蓄山羊胡的小个子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
 ,再边上是奥斯塔公爵
,再边上是奥斯塔公爵
 ,也许他英俊得不像伟大的将军,但起码看着像那么回事儿。许多意大利人可能希望这位公爵当国王。他看着就像一位国王。他是国王的叔叔,任第三军统帅。我们属于第二军。第三军里有几支英国炮兵连。在米兰,我曾遇见两名第三军的英国炮兵,人非常不错,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他俩都是大个子,性格腼腆,爱难为情,而且无论发生什么事,总是连连道谢。真希望能跟英国人待在一起,那会省事很多。不过那样的话,我也可能已经死了。在救护车队是没有生命危险的。不,也不一定。英国救护车驾驶员就时有牺牲。呃,我知道自己不会死,不会死于此地。这场战争跟我毫无关系,而且就我看还没有电影里的战争危险。不过我仍向上帝祈祷,让战争早点结束。也许今年夏天就能结束。也许奥地利人会突然崩溃。在史上的历次战争中,他们次次都被打得溃不成军。这场战争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人人都说法国人完蛋了。里纳尔迪说法国人发生了哗变,军队转而向巴黎进军。我问他后来怎样。他回答:“噢,他们挡住了那支军队。”我想去没有战争的奥地利。我想去黑森林
,也许他英俊得不像伟大的将军,但起码看着像那么回事儿。许多意大利人可能希望这位公爵当国王。他看着就像一位国王。他是国王的叔叔,任第三军统帅。我们属于第二军。第三军里有几支英国炮兵连。在米兰,我曾遇见两名第三军的英国炮兵,人非常不错,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他俩都是大个子,性格腼腆,爱难为情,而且无论发生什么事,总是连连道谢。真希望能跟英国人待在一起,那会省事很多。不过那样的话,我也可能已经死了。在救护车队是没有生命危险的。不,也不一定。英国救护车驾驶员就时有牺牲。呃,我知道自己不会死,不会死于此地。这场战争跟我毫无关系,而且就我看还没有电影里的战争危险。不过我仍向上帝祈祷,让战争早点结束。也许今年夏天就能结束。也许奥地利人会突然崩溃。在史上的历次战争中,他们次次都被打得溃不成军。这场战争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人人都说法国人完蛋了。里纳尔迪说法国人发生了哗变,军队转而向巴黎进军。我问他后来怎样。他回答:“噢,他们挡住了那支军队。”我想去没有战争的奥地利。我想去黑森林
 。我想去哈茨山
。我想去哈茨山
 。
。
不过,哈茨山又在哪儿呢?喀尔巴阡山脉
 激战正酣。无论如何我不想去那里,虽然那地方也许不错。如果没有战争,我还可以去西班牙。太阳渐渐西沉,炎热慢慢消退。吃过晚餐,我要去见凯瑟琳·巴克利。真希望此刻她就在这里,真希望此刻我跟她在米兰。我会跟凯瑟琳·巴克利去科瓦咖啡馆共进晚餐,在闷热的夜晚沿曼佐尼大街散步,然后过街,接着拐过弯,最后沿运河回到旅馆。也许她会愿意跟我去米兰,也许她会把我当作她那个战死的男友。我们走进旅馆大门,门房摘下帽子以示敬意。我走向服务台,问侍者拿房间钥匙,她站在电梯旁等待。我们走进电梯,电梯缓缓上升,每到一层都“咔哒”一响,最后终于来到我们住的那层。侍者打开电梯门恭送我们。她先走出电梯,我紧随而出。我们沿走廊来到房间门前。我把钥匙插进钥匙孔,打开房门,走进去,拿起电话,吩咐侍者送一瓶装在盛满冰块的银制冰桶里的卡普里白葡萄酒
激战正酣。无论如何我不想去那里,虽然那地方也许不错。如果没有战争,我还可以去西班牙。太阳渐渐西沉,炎热慢慢消退。吃过晚餐,我要去见凯瑟琳·巴克利。真希望此刻她就在这里,真希望此刻我跟她在米兰。我会跟凯瑟琳·巴克利去科瓦咖啡馆共进晚餐,在闷热的夜晚沿曼佐尼大街散步,然后过街,接着拐过弯,最后沿运河回到旅馆。也许她会愿意跟我去米兰,也许她会把我当作她那个战死的男友。我们走进旅馆大门,门房摘下帽子以示敬意。我走向服务台,问侍者拿房间钥匙,她站在电梯旁等待。我们走进电梯,电梯缓缓上升,每到一层都“咔哒”一响,最后终于来到我们住的那层。侍者打开电梯门恭送我们。她先走出电梯,我紧随而出。我们沿走廊来到房间门前。我把钥匙插进钥匙孔,打开房门,走进去,拿起电话,吩咐侍者送一瓶装在盛满冰块的银制冰桶里的卡普里白葡萄酒
 。过了一会儿走廊上就传来冰块碰撞桶壁的声音。接着侍者敲了敲门。我对他说,请把酒放在门外吧。因为太热,我们什么都没穿。窗户开着,燕子在鳞次栉比的屋顶上空盘旋,夜幕降临后,走到窗边,小小的蝙蝠在房子上空捕食,然后俯冲下来掠过树梢。我们喝着卡普里白葡萄酒,房门锁着,天气很热,我们共用一条被单。我们在米兰的一个闷热夜晚里互相深爱。没有任何遮掩。整整一个夜晚。在米兰,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们缠绵到天亮。这才叫生活。我要赶紧吃完晚餐,然后去见凯瑟琳·巴克利。
。过了一会儿走廊上就传来冰块碰撞桶壁的声音。接着侍者敲了敲门。我对他说,请把酒放在门外吧。因为太热,我们什么都没穿。窗户开着,燕子在鳞次栉比的屋顶上空盘旋,夜幕降临后,走到窗边,小小的蝙蝠在房子上空捕食,然后俯冲下来掠过树梢。我们喝着卡普里白葡萄酒,房门锁着,天气很热,我们共用一条被单。我们在米兰的一个闷热夜晚里互相深爱。没有任何遮掩。整整一个夜晚。在米兰,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们缠绵到天亮。这才叫生活。我要赶紧吃完晚餐,然后去见凯瑟琳·巴克利。
在食堂,大家你一嘴我一舌,说个没完。我喝了酒,因为如果不喝点儿,今晚大家就做不成兄弟。喝酒间歇,我跟牧师聊了聊大主教爱尔兰
 。听上去那是个道德高尚的人,在美国蒙受了冤屈——尽管之前闻所未闻,但身为美国人的我也有责任。我假装知道此事,如果坦白对此一无所知感觉很不礼貌。毕竟牧师已滔滔不绝,为我详细解释了造成那些冤屈的原因,而所谓的原因,归根到底,似乎也就是一些误会。我觉得那位大主教的姓氏不错,加上又是来自明尼苏达州,读起来朗朗上口,听着就像:明尼苏达岛,威斯康星岛,密歇根岛。之所以朗朗上口,是因为该姓氏的发音近似“岛屿”一词的发音。不,不是这样,没那么简单。是的,神父。有道理,神父。也许吧,神父。不,神父。呃,也许是的,神父。你知道得比我多,神父。牧师是好人,然而无趣。那些军官不是好人,而且无趣。国王是好人,同样无趣。酒不是好酒,但喝着有趣。喝下去,会溶解你的牙釉质,并把溶解的牙釉质留在你的上颚。
。听上去那是个道德高尚的人,在美国蒙受了冤屈——尽管之前闻所未闻,但身为美国人的我也有责任。我假装知道此事,如果坦白对此一无所知感觉很不礼貌。毕竟牧师已滔滔不绝,为我详细解释了造成那些冤屈的原因,而所谓的原因,归根到底,似乎也就是一些误会。我觉得那位大主教的姓氏不错,加上又是来自明尼苏达州,读起来朗朗上口,听着就像:明尼苏达岛,威斯康星岛,密歇根岛。之所以朗朗上口,是因为该姓氏的发音近似“岛屿”一词的发音。不,不是这样,没那么简单。是的,神父。有道理,神父。也许吧,神父。不,神父。呃,也许是的,神父。你知道得比我多,神父。牧师是好人,然而无趣。那些军官不是好人,而且无趣。国王是好人,同样无趣。酒不是好酒,但喝着有趣。喝下去,会溶解你的牙釉质,并把溶解的牙釉质留在你的上颚。
“那牧师进了监狱。”罗卡说,“因为从他身上搜出了三厘息公债。当然,这事发生在法国。要是在这里,他绝对不会被抓。他否认见过任何五厘息公债。这事发生在贝济耶
 。当时我正好在那里,从报上读到这则新闻后,我去了监狱请求见这位牧师。很明显,证据确凿,他偷了那些公债。”
。当时我正好在那里,从报上读到这则新闻后,我去了监狱请求见这位牧师。很明显,证据确凿,他偷了那些公债。”
“你说的,我一个字都不信。”里纳尔迪说。
“随你的便。”罗卡说,“反正,我是说给我们这位牧师听的。这事很有教育意义。他也是牧师,他会理解的。”
牧师笑了笑。“继续说。”他说,“我在听。”
“有些公债自然已经不知去向,但在那牧师身上搜到了全部的三厘息公债和一些地方债券——具体是什么债券,这会儿我忘了。刚才说到我去了监狱,下面就是整个故事的重点。我站在牢房外,像告解时那样对他说:‘保佑我,神父,因为你犯了罪。’
 ”
”
所有人哈哈大笑。
“那他怎么回你的?”牧师问。罗卡没搭理他,而是继续向我解释那个笑话,“你听懂了吧?”如果能完全理解的话,那是一则非常幽默的笑话。他们又给我倒了些酒。我说了一名英国列兵被迫淋雨的故事。接着,少校说了十一名捷克斯洛伐克人和一名匈牙利下士的故事。又喝了些酒后,我说了一名骑师找回一枚便士的故事。少校说,意大利也有类似的故事,讲的是一名夜里睡不着觉的公爵夫人。这时,牧师走了。我又说了个一名旅行推销员清晨五点来到马赛,正赶上那里刮密史脱拉风
 的故事。少校说他听闻我很能喝酒。我否认了。他说传闻是真的,还说要凭酒神巴克斯的尸体起誓,来验证一下传闻的真伪。不要搬出巴克斯,我连连说。不要搬出巴克斯。就要搬出巴克斯,他说。我可以跟菲利波·琴扎·巴西拼酒,他一杯,我一杯。巴西说,这不公平,因为他已经比我多喝了一倍的酒。我说这是无耻的谎言,巴克斯不巴克斯的,无论菲利波·温琴扎·巴西,还是巴西·菲利波·温琴扎,整个晚上都滴酒未沾,而且他到底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反问我的名字究竟是弗雷代里科·恩里科
的故事。少校说他听闻我很能喝酒。我否认了。他说传闻是真的,还说要凭酒神巴克斯的尸体起誓,来验证一下传闻的真伪。不要搬出巴克斯,我连连说。不要搬出巴克斯。就要搬出巴克斯,他说。我可以跟菲利波·琴扎·巴西拼酒,他一杯,我一杯。巴西说,这不公平,因为他已经比我多喝了一倍的酒。我说这是无耻的谎言,巴克斯不巴克斯的,无论菲利波·温琴扎·巴西,还是巴西·菲利波·温琴扎,整个晚上都滴酒未沾,而且他到底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反问我的名字究竟是弗雷代里科·恩里科
 ,还是恩里科·费代里科。我说别管什么巴克斯,来来来,我们来决一雌雄。于是少校倒上两大杯红酒,让我们开始拼酒。喝到一半,我不想再喝了。我想起了自己将要去的地方。
,还是恩里科·费代里科。我说别管什么巴克斯,来来来,我们来决一雌雄。于是少校倒上两大杯红酒,让我们开始拼酒。喝到一半,我不想再喝了。我想起了自己将要去的地方。
“巴西赢了。”我说,“他比我强。我有事得走了。”
“他真的有事。”里纳尔迪说。“他有个约会,我可以作证。”
“我得走了。”
“改天晚上,”巴西说,“改天晚上,等你状态好了我们再好好拼一把。”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餐桌上,烛光摇曳,所有军官都非常高兴。“晚安,先生们。”我向他们道别。
里纳尔迪陪我走出食堂。在门外小草坪上,他说:“你最好不要醉醺醺地去那里。”
“我没醉,里宁
 。真的。”
。真的。”
“你最好嚼点咖啡豆。”
“胡说八道!”
“我去拿点来,老弟。你在这儿来回走一走。”他拿来一把烤咖啡豆。“来,嚼点,老弟。愿上帝与你同在。”
“巴克斯与我同在。”我说。
“我陪你一起去。”
“我一点也没醉。”
我嚼着咖啡豆,跟里纳尔迪穿街走巷,前往英国人住的别墅。走到那栋别墅的大门口,里纳尔迪向我道别。
“晚安。”我回道,“你干吗不一起进去呢?”
他摇摇头,“不。”他说,“我喜欢简单的快乐。”
“谢谢你给我拿咖啡豆。”
“没什么,老弟。没什么。”
我顺着车道往里走,车道两旁的柏树轮廓分明。我回过头,看见里纳尔迪仍站在原地望着我,我冲他挥挥手。
我坐在别墅的接待大厅,等凯瑟琳·巴克利下来。有人从走廊那头过来。我站了起来。但来人并非凯瑟琳,而是弗格森小姐。
“喂,”她招呼道,“凯瑟琳让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她不能见你,很抱歉。”
“真遗憾,希望她没得什么病。”
“她不是很舒服。”
“麻烦你转告她,我很为她担心,行吗?”
“行,我会的。”
“那我明天再来见她,你看可以吗?”
“嗯,可以。”
“非常感谢。”我说,“晚安。”
走出门后,我突然感到一阵寂寞与空虚。我并没把见凯瑟琳当回事,所以喝得半醉,差点忘了来见她。可见不到她,我又感到莫名的寂寞与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