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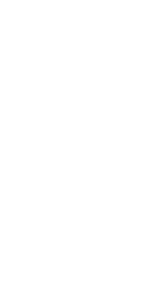
|
二、整体分析的逻辑性:以《愚公移山》为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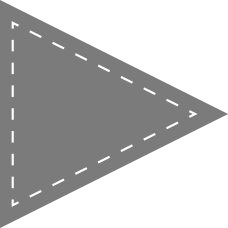 看清文本事实:是愚公移走了这两座山吗
看清文本事实:是愚公移走了这两座山吗
《愚公移山》是一篇寓言。对于寓言,我们会本能地去挖掘寓意。《愚公移山》这篇寓言的寓意,一般人认为是在困难面前,要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寓言的寓意究竟是什么,这需要实事求是的分析。而分析的基础,就是事实与逻辑。我们要把握住文本中存在的事实。
要对文本题目进行思考:既然题目是“愚公移山”,那么是不是愚公移走了这两座山呢?这个标题给我们的一般印象是愚公移走了山。然而回到文本,会发现一个事实:愚公本人并未移走这两座山。他有移山的愿望,但实际上他缺少实现这个愿望的能力。固然,“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一代一代地移,一定可以逐渐削减山的高度。但我们需要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移山的工作量巨大,“方七百里,高万仞”;移山的效率低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按照这样的效率来做这项工作,任何理智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两座山通过人力是基本上没办法移走的。那么,是谁最后移走了这两座山呢?不是人,而是神。
努力回到文本中的基本事实——文本中其实提供了很多基本事实。做文本解读,首先要去观察文本内部究竟存在哪些最基本的事实。
最基本的事实是:不是愚公把山移走了,而是“夸娥氏二子负二山”——是两个神把山背走了。
为什么神要来帮愚公把山背走?是因为有天帝的命令。
为什么天帝要发出这个命令?因为“感其诚”。天帝对愚公的诚心非常感动,于是派两个神把山移走了。
愚公固然有移山的愿望、移山的行动,但他确实没有移山的能力。事实上,他也未能依靠自己达成移山的结果。他确实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是这个主观能动性并不足以使这两座山消失。
在愚公和智叟的对话部分,我注意到了“智叟”“愚公”的名字的特征。这两个名字很有意思,是文本作者刻意安排的,有其特定含义。从整个事情的结果来看,是天帝派神把山移走了,而人类无论“智”或“愚”都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天帝为何要这样做?是因为感动于人的“诚”。这就是说,“诚”是联结人与神的方式,而“愚”和“智”不是。“愚”和“智”属于智力范畴,“诚”——诚心、赤诚,不是一个和智力有关的问题。“诚”是一种心灵的状态。这里显示的道理,其实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心诚则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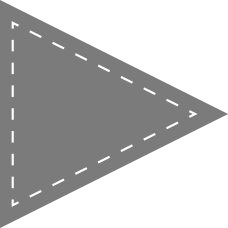 “诚”是我们接近神的唯一方式
“诚”是我们接近神的唯一方式
对此,我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表述:“诚”是我们接近神的唯一方式。它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智力没有关系。
为什么“诚”的是愚公,而不是智叟?从人类生活的一般情况来讲,“愚”和“诚”往往更可能相关联,有个词语就叫“愚诚”:一个比较愚笨的人,用心往往更容易诚;一个所谓聪明的人,反而容易流于摇摆、多疑、狡猾、奸诈。所以,“诚”的是愚公,而不是智叟。《愚公移山》这个文本最核心的就是提出了“诚”是感动上天、接近神灵的方式。
“愚”和“诚”有更高的关联度,这和道家“绝圣弃智”的思想有关系。在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愚公是正面人物,但只靠人自身的努力,可以解决一些世俗的小事情,却无法解决终极性的大问题。最终还是要靠“诚”,通过它我们才有可能抵达上帝(天)。
那么能否这样说,很多事情人是无法完成的,只有神才能完成?不能,因为移山的愿望最后是实现了的。只要有“诚”,就可以创造奇迹,就可以通过接近神灵来创造奇迹、达到目的。当我们有了“诚”,就可以接近神灵,就可以通灵,就有非凡的效果出现。这就是本文的主旨。
回顾我们的讨论过程,第一重要的就是要看清文本事实。一般人看到这个题目,就以为是愚公把山移走了。其实,“愚公移山”这个题目并没有准确地描述结果。愚公确实有移山的动机、决心、诚意,但他自己的行动并没有达成移山的结果。
下面附上郭初阳《愚公移山》课堂实录中所展示的外籍教师的看法。这种看法表明,他确实不理解中国道家的文化:
但是他开始了一项他自己都知道不能完成的工作,这让我觉得很奇怪。他的说法是:“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他指望这项工作能够持续下去,他的家人能继续他想做的事。在西方,至少如果我的父亲开始了这项工作,他不会指望我去完成,他会自己完成它。
这是一项机械的工作。它运用的是体力,而不是脑力。很显然,故事里没有提到他的女儿,没有涉及女性,除了那个寡妇。而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她失去了丈夫。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英国,故事里会出现更多的女性,可能会有一个女主角,而不像在这里,主角都是男性。
这是关于一个愚蠢的老头的故事,他有一个荒谬愚蠢的想法——移山。我想说的是,如果在西方,我们不会想到移山,我们会绕道而行。
他叫愚公,如果你了解中文,就会了解一点他的名字的含义。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愚”是愚蠢的意思,“公”的意思是老人——一个愚蠢的老头。但他愚蠢吗?这是个问题,因为在最后,他确实做到了。
也许我可以认为他是一个疯狂的老头,他有一个梦想,而且会说服他的家人追随他的梦想。我很想问的是,为什么他不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做这件事呢?(现在他这么老了还要其他人来继续他自己未完成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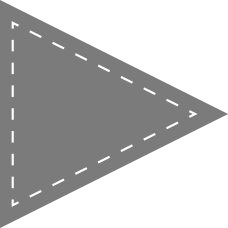 “愚公移山”的关键不是“移”而是“愚”
“愚公移山”的关键不是“移”而是“愚”
安排智叟这个人物的出现,是为了反衬愚公的一心一意吗?
是强调愚公移山的决心。他的决心很坚定,一心一意想移。“我之后,我的儿子移,我的孙子移。”“无穷匮”地移。他的决心很大,希望移山这件事情一直贯穿他的家族的整个生命系列,无限贯通,表现了他的决心之强。
这一段和愚公移山这件事情本身,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它是一个插曲,但这个插曲很重要。
首先,它引入了一个人——智叟,这样“智”和“愚”的关系才能建立起来。而智叟先是谈到了智力问题——“甚矣,汝之不惠”。按照一般的思考,凭借你这个只剩残年余力的老头儿,怎么可能把山移走?其实,他(智叟)的话是对的,至少从世俗的经验来看是对的。
其次,建立“愚”和“诚”之联系。愚公的“诚”,属于“愚诚”。愚笨的人通常心思单纯,在现象层面比较接近“诚”;聪明的人通常心思复杂,在现象层面离“诚”较远。就一般观察来讲,愚笨的人近于诚实,聪明的人近于奸猾。所以,愚公比智叟更近于“诚”,他一心一意,用心端直,比智叟更有感动上天的可能。
再次,愚公的话,强调了通过生命的序列、一代一代的努力,最后把山移走的想法。一方面,表现了他的决心;另一方面,又和后边的结果形成对比关系:并不是你或者你的子孙把山移走的,而是“帝感其诚”,派夸娥氏二子把山移走了。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对比性关联,说明奇迹最终是由神创造的,依靠神力才能创造奇迹。而这个神,是可以被人的“诚”感动的。当你的诚心感动了上天,奇迹就有可能发生,所以这一段还是很重要的。
智叟这个人物的出现,固然重要,但结局更重要。如果结局就是一代代挖下去,那它就不是寓言,完全成了写实。后面因为有神灵出现,一般人才会认为它是寓言。如果结尾是愚公不断地挖,却没有移走山,山固然会被挖掉一些,但却看不到有什么本质性的变化。你看到的,将只是人类徒劳无功的执着。
在解读和教学中,这个文本有没有一个好的切入点呢?
文本解读和阅读教学,要追求“纲举目张”。“纲举目张”就是要直击核心,抓住关键。就这个文本而言,这篇课文的题目中就有一个最关键的字,通过这个关键字,可以找到一条分析文本的线索。
“愚公移山”,关键不是“移”,而是“愚”。为什么?第一,是愚公在移山,讲“愚”可以附带着讲“移”;第二,愚和智构成一种反义,这就把智叟这个人物也盘活了。抓住了“愚”,可以尽可能地覆盖文本内容。
我已经说过:山最终是否被移走和人的聪明与否是没有关系的。抓住了“愚”,可以进一步带出“诚”,“诚”才是本文文意的真正要害。“诚”一出来,文本主旨就豁然开朗了。
在文本解读和阅读教学中,存在一个通病:用评价代替理解,评价过早地介入理解。比如这个文本,在没有真正读懂时,就率然断定文本是表现执着、进取、不断努力的民族精神,然后在课堂上找一些文本信息给其贴上这个精神标签。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文本解读,也不是尊重文本的阅读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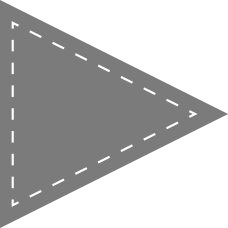 诚就是无欺之初心
诚就是无欺之初心
“诚”是心的真实、赤裸的状态,但不能简单地把它说成是人的“能动性”。
“能动性”意味着先有一个发心,然后自己去努力。愚公想要移山,这个意愿、动机,就是发心。发心之后去做,这就是行动。
“诚”不一样,“诚”是一种心灵状态,是一种纯一赤裸、朗然无欺、毫不旁骛的状态。作为状态,它是静止的。儒家经典《大学》里讲“正心诚意”,“正心”就是心归于本位,不偏不倚;“诚意”是指心地真实,明白,没有尘埃遮蔽(此处的尘埃就是六祖慧能那个著名偈子“何处惹尘埃”中的“尘埃”)。它本身没有指向性,既不指向自己,又不指向外部,就像一轮明月,自在地、明白地、安然地挂在天空。
“诚”是“无欺”的,没有欺骗,没有变形。完全是初心,垢染还没有发生。这颗心完全坦白、裸露,有点像佛教里的说法,很难描述。
要达到“诚”,其实是很难的。一般人的心,有很多杂质、杂念。每当我们突发一个念头,在不知不觉中通常会伴随另外的念头(包括与该念头相反的念头),这就叫“疑”。当一个念头在心头出现,我们的心会立即对这个念头加以审视、评估甚至怀疑,众多念头涌起,而后才会进行选择、分析和判断。这就是为什么人有很高的灵活性,随时可以转向。因为心不单一,念头复杂,思维随时变动。主要念头生起,同时也有很多次要念头暗中涌动,只是你未必意识到。人这种普遍的心灵状态,在我们应对现实世界时,表现为意念随时转换、选择随处发生。但“诚”这种状态却是纯一,只有一念,不会有其他念头伴生。愚公的心念没有转换,没有选择,这就是一心一意,就是“诚”。
很多时候,“诚”和信仰有关。心诚的人才会有真实的信仰,宗教是强调信仰的。从宗教的意义上说,“诚”是接近神的唯一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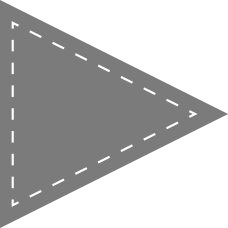 练习设计与文本解读:“课后习题”的价值何在
练习设计与文本解读:“课后习题”的价值何在
这篇课文的课后习题是:“愚公真的很愚。大山挡住了路,自己去挖山本来就傻,为什么还叫子子孙孙去吃这苦头?绕开山路或者干脆搬家不就行了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九年级下册)
有些教师觉得这样的题目很好,能让学生的思维有思辨性。其实,这类题目的设计,表现出了对文本主旨的解读不正确,没有到位,没有看到“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这类练习题的设计,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它没有考虑寓言的寓意,完全回到了世俗经验,讨论世俗的问题,不仅没有读懂,而且使这篇文章失去了价值。从世俗的生活经验来讲,当你家住深山,山挡住了路,这件事情让你极其痛苦,你的明智选择肯定是搬家,这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然而,这实际上是回到世俗经验层面,却没有扣住这个寓言的寓意,没有观察到文本的特点是寓言。
抛开课文文本来讨论这些问题,还是有价值的。但这类题目在这里并不合理,没有讨论的必要。为什么?因为文本本身并不是讨论我们是要傻乎乎地去挖山,还是要灵活地搬家;并不是“愚蠢的执着”和“聪明的灵活”的矛盾,文章是在讲“诚”。这类习题的存在,说明了编者没有读懂这篇文章。这样的题目拿到课堂上,就会出现很热闹但却偏离文意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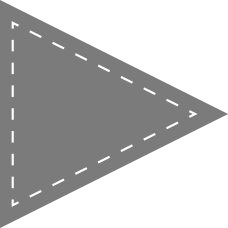 素读批注,寻找有价值的教学内容
素读批注,寻找有价值的教学内容
我们不借助参考资料自己素读课文时,作批注是一个发现有价值的教学内容的好方法。
作批注,就是写出批语注释。这个过程既是对文章的分析、品评,又是我们自己消化、吸收、转化的过程。
作批注,有两个做法很适合教师。第一,做提要。边读边思考,用精练的语言把文中的精要批写在相关语段旁边;第二,写批语。读书时,把阅读文本时产生的、自己觉得有价值的各种感想、见解、疑问,随手写在书的空白处。当然,这些东西不见得非要写在书上,写在本子上也行。
下面是我对朱光潜的《咬文嚼字》作的一个批注。作完批注之后,我觉得这篇文章所谈的主要观点,“咬文嚼字,在表面上像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实际上就是调整思想和情感”,在当今已是价值不高的老生常谈,学生不会喜欢这种说教;而其中所谈及的若干例子,倒是很能启发学生的好材料。于是这篇课文的教学,我就定位在对这些例子的分析品鉴上。
郭沫若先生的剧本《屈原》里婵娟骂宋玉说:“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排演时他自己在台下听,嫌这话不够味,想在“没有骨气的”下面加“无耻的”三个字。一位演员提醒他把“是”改为“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就够味了。他觉得这字改得很恰当,他研究这两种语法的强弱不同,以为“你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叙述语,没有更多的意义,有时或许竟会落个“不是”;“你这什么”便是坚决的判断,而且还把必须有的附带语省略去了。根据这种见解,他把另一文里“你有革命家的风度”一句话改为“你这革命家的风度”。
【批注】“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郭沫若感觉到这个句子不够味,他的感觉是对的。他想在“没有骨气的”下面加“无耻的”三个字,是企图用形容词来加强表达力量。这个思路是错误的,也是一般写作者容易犯的毛病。与动词相比,形容词其实是最缺乏力量的,因为它过于抽象。有的作家刻意避免形容词的使用,如海明威等。
在“没有骨气的”下面加“无耻的”三个字,不但无法加强表达力量,反而会造成语言的冗赘。既然“没有骨气”,当然也就近于“无耻”了。而且,“你是没有骨气的无耻的文人!”这样的句子长度增加了,作为剧本中表达强烈谴责情绪的台词,对演员的肺活量构成太大的考验。更重要的是,句子长了,就不够简洁有力了。
这是炼字的好例,我们不妨借此把炼字的道理研究一番。那位演员把“是”改为“这”,确是改得好,不过郭先生如果记得《水浒》里的用语,就会明白一般民众骂人,都用“你这什么”式语法。石秀骂梁中书说:“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杨雄醉骂潘巧云说:“你这贱人!你这淫妇!你这你这大虫口里倒涎!你这你这……”一口气就骂了六个“你这”。看这些实例,“你这什么”倒不仅是“坚决的判断”,而且是带有极端憎恶的惊叹语,表现着强烈的情感。“你是什么”便只是不带情感的判断,纵有情感也不能在文字本身上见出。不过它也不一定就是“单纯的叙述语,没有更多的含义”。《红楼梦》里茗烟骂金荣说:“你是个好小子,出来动一动你茗大爷!”这里“你是”含有假定语气,也带“你不是”一点讥刺的意味,如果改成“你这好小子!”神情就完全不对了。由此可知“你这”式语法,并非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比“你是”式语法来得更有力。其次,郭先生援例把“你有革命家的风度”改为“你这革命家的风度”,似乎改得并不很妥。“你这”式语法大半表示深恶痛疾,在赞美时便不适宜……在“你这革命家的风度”中,“风度”便变成主词,和“你(的)”平行,根本不成一句话。
【批注】朱光潜说“‘你这’式语法大半表示深恶痛疾,在赞美时便不适宜”,其实是值得再推敲的。有时候,人们表达喜爱之情,很可能会用“你这傻瓜”“你这负心郎”之类的说法。
“你是什么”与“你这什么”的不同,我觉得首要在于句型的差异。“你是什么”是完整的判断句型,完全符合语法规范。这种判断句型具有普通性和规范性,平稳、妥当、理性,较难传达特殊的情绪。在“你”与“什么”之间,隔着一个表示判断的“是”字。而“你这什么”句式特殊,直接把“你”与“什么”不假思索地等同了起来。“不假思索”这个词在这里意外地准确,在“你是什么”这种句法中,“是”表示存在一个判断的思维动作。在“你这什么”中,这个思维动作被取消了。“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一句中,“你”不假思索地等同于“没有骨气的文人”了,这个判断更多地体现出情感的而非理性的。
至于“你这革命家的风度”的说法,朱光潜分析得很对。这是个病句。“你”=“革命家的风度”,谁都知道这样的等式完全是荒谬的。“你”是人,“风度”不是人,二者在逻辑上根本不同类。
这番话不免啰嗦,但是我们原在咬文嚼字,非这样锱铢必较不可。咬文嚼字有时是一个坏习惯,所以这个成语的涵义通常不很好。但是在文学,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文学借文字表现思想情感;文字上面有含糊,就显得思想还没有透彻,情感还没有凝练。咬文嚼字,在表面上像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实际上就是调整思想和情感。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例如《史记》李广射虎一段: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这本是一段好文章,王若虚在《史记辨惑》里说它“凡多三石字”,当改为“以为虎而射之,没镞,既知其为石,因更复射,终不能入”。或改为“尝见草中有虎,射之,没镞,视之,石也”。在表面上看,似乎改得简洁些,却实在远不如原文。“见草中石,以为虎”并非“见草中有虎”。原文“视之,石也”,有发现错误而惊讶的意味,改为“既知其为石”便失去这意味。原文“终不能复入石矣”有失望而放弃得很斩截的意味,改为“终不能入”便觉索然无味。这种分别,稍有文字敏感的人细心玩索一番,自会明白。
【批注】朱光潜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到位的。至于他说“原文‘终不能复入石矣’有失望而放弃得很斩截的意味”,则不够妥当。在我看来,李广之所以“复更射”,是为了证实他自己是否有射箭入石的神力,接下来说“终不能复入石矣”,是李广尝试多次再也射不进去,“终”暗示他最后的不甘与失望,根本没有放弃得“很斩截”的意味。《史记》中这一节叙述李广射虎,说“李广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其实是人类常有的应激反应,在极端时刻,人可能表现得分外神勇。
有些人根本不了解文字和思想情感的密切关系,以为更改一两个字不过是要文字顺畅些或是漂亮些。其实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姑举一个人人皆知的实例。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为“敲”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得好听一点,都说“推敲”。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假如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平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
【批注】仅看朱光潜先生的分析,你会觉得他说得很对。但其实,朱先生这里是弄错了。我怀疑朱先生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忘了贾岛的原诗,至少他忘了查证这首诗。贾岛这首诗很著名,叫作《题李凝幽居》: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贾岛本人曾做过僧人,这首诗中的“僧”其实就是作者自己。全诗写的是作者走访友人李凝未遇这样一件寻常小事。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是历来传诵的名句。“推敲”两字还有这样的故事:一天,贾岛骑在驴上,忽然得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初拟用“推”字,又思改为“敲”字,在驴背上引手作推敲之势,不觉一头撞到京兆尹韩愈的仪仗队,随即被人押至韩愈面前。贾岛便将作诗得句下字未定的事情说了,韩愈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立马思之良久,对贾岛说:“作‘敲’字佳矣。”随后,两人竟成为朋友。
韩愈思考良久,认为“敲”优于“推”,不是没有道理的。二人从此交友,亦可见贾岛本人对韩愈的意见相当认同。我的看法也是“敲”优于“推”。
第一,有人在月下敲门,发出一点声音,才会惊动宿鸟;当树上的鸟有了动静时,诗人才会知道树上有鸟在歇宿。而且,在这种幽寂的环境中传来几下敲门的剥啄声,才更使人感到格外幽寂。这同王籍的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是同一道理,都是以声音衬托寂静。
第二,因为诗题是“题李凝幽居”,“僧”是贾岛自己,所以月下推门或敲门的是客人而非主人。若是主人,“推”是对的,因为他是主人,可以随意“推”自家的门;作为主人,他也知道门没有锁闭,只是虚掩。若是来客,当然就只能“敲”,因为他不知门是否关闭,关着的门你“推”也推不开;而且,“推”门而入,未免唐突无礼。
第三,朱先生说“推”可以无声,其实“推”更可能是有声的。如果“推”的力道比较大,这声音将可能比“敲”更雷人。
第四,“敲”字更能突出李凝居处的“幽”,更好地突出隐居避人的隐士形象。在这一联诗句中,鸟儿已经归巢,而人还在“敲”门寻找。找到隐士没有呢?能否通过“敲”门问询找到呢?不知道。这就在果与未果之间形成张力。
第五,有的研究者提出,“敲”字在音节上更为响亮(周振甫)。
无论是阅读或是写作,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字有直指的意义,有联想的意义。比如说“烟”,它的直指的意义,凡见过燃烧体冒烟的人都会明白。只是它的联想的意义迷离不易捉摸,它可以联想到燃烧弹,鸦片烟榻,庙里焚香,“一川烟草”“杨柳万条烟”“烟光凝而暮山紫”“蓝田日暖玉生烟”……种种境界。直指的意义载在字典上,有如月轮,明显而确实;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上所累积的种种关系,有如轮外圆晕,晕外霞光,其浓淡大小随人随时随地而各个不同,变化莫测。科学的文字愈限于直指的意义就愈精确,文学的文字有时却必须顾到联想的意义,尤其是在诗方面。直指的意义易用,联想的意义却难用。因为前者是固定的,后者是游离的;前者偏于类型,后者偏于个性。既是游离的,个别的,它就不易控制,而且它可以使意蕴丰富,也可以使意义含糊甚至于支离。比如说苏东坡的《惠山烹小龙团》诗里的三、四两句“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天上小团月”是由“小龙团”茶联想起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关联,原文就简直读不通;如果你不了解明月照着泉水和清茶泡在泉水里那一点共同的清沁肺腑的意味,也就失去原文的妙处。这两句诗的妙处就在不即不离、若隐若现之中。它比用“惠山泉水泡小龙团茶”一句话来得较丰富,也来得较含混有蕴藉。难处就在于含混中显得丰富,由“独携小龙团,来试惠山泉”变成“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这是点铁成金。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这一点生发上面。
【批注】“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意思说白了就是“带来小龙团茶,用惠山泉水泡”。但正如朱先生所说,苏轼的诗句“来得较丰富,也来得较含混有蕴藉”是“点铁成金”。“较含混有蕴藉”,因为东坡诗句说得不那么直白,这一点很容易理解。那为什么说它“较丰富”呢?
仔细分析,东坡这句诗的妙处,在于它写的是“惠山泉水泡小龙团茶”,又不只是“惠山泉水泡小龙团茶”。“独携”的主语是谁?就是东坡。而这个东坡不是“东坡”而是“坡仙”,他把自己想象为神仙了。他携带着天上的月亮,带着一片月光,来试一试这“人间第二泉”。于是,东坡用惠山泉水泡小龙团茶之时逍遥超然的美妙心境在诗句里也透露出一些。
这诗句里有双关,有想象,有主观情意的注入,很有味道。“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这一点生发上面。”
这是一个善用联想意义的例子。联想意义也最易误用而生流弊。联想起于习惯,习惯老是欢喜走熟路。熟路抵抗力最低,引诱性最大,一人走过,人人就都跟着走,愈走就愈平滑俗滥,没有一点新奇的意味。字被人用得太滥,也是如此。……美人都是“柳腰桃面”“王嫱、西施”,才子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谈风景必是“春花秋月”,叙离别不离“柳岸灞桥”;做买卖都有“端木遗风”,到现在用铅字排印书籍还是“付梓”“杀青”。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它们是从前人所谓“套语”,我们所谓“滥调”。一件事物发生时立即使你联想到一些套语滥调,而你也就安于套语滥调,毫不斟酌地使用它们,并且自鸣得意。这就是近代文艺心理学家们所说的“套板反应”。一个人的心理习惯如果老是倾向“套板反应”,他就根本与文艺无缘。因为就作者说,“套板反应”和创造的动机是仇敌;就读者说,它引不起新鲜而真切的情趣。一个作者在用字用词上面离不掉“套板反应”,在运思布局上面,甚至在整个人生态度方面也就难免如此。不过习惯力量的深广常非我们意料所及,沿着习惯去做,总比新创较省力,人生来有惰性,常使我们不知不觉地一滑就滑到“套板反应”里去。你如果随便在报章杂志或是尺牍宣言里面挑一段文章来分析,你就会发现那里面的思想情感和语言大半都由“套板反应”起来的。韩愈谈他自己做古文,“惟陈言之务去”。这是一句最紧要的教训。语言跟着思维情感走,你不肯用俗滥的语言,自然也就不肯用俗滥的思想情感,你遇事就会朝深一层去想,你的文章也就真正是“作”出来的,不致落入下乘。
【批注】“套板反应”是文学的敌人。我们听说过,第一个把美女比作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便是蠢材。为什么呢?因为第二个、第三个沿用既有的比喻,属于典型的“套板反应”。“套板反应”意味着艺术创作者偷懒,他实际上没有真正努力去感觉他所描写的对象,只是在重复别人的感觉。他的感觉力钝化或退化了,落入了窠臼。
看到杨柳,就是离别;写到美人,就是“柳腰桃面”。这不只是文字有没有“新奇的意味”的问题,而且是对对象有无真切感受和体会的问题。
以上只是随便举实例,说明咬文嚼字的道理。例子举不胜举,道理也说不完。我希望读者从这粗枝大叶的讨论中,可以领略运用文字所应有的谨严精神。本着这个精神,你随处留心玩索,无论是阅读或写作,就会逐渐养成创作和欣赏都必需的好习惯。你不能懒,不能粗心,不能受一时兴会所生的幻觉迷惑而轻易自满。文学是艰苦的事,只有刻苦自励,推陈翻新,时时求思想情感和语文的精练与吻合,你才会逐渐达到艺术的完美。
作出这样的批注之后,我得出一个教学判断:教这篇课文,不妨把对这些例子的探讨作为教学内容。首先,对《咬文嚼字》来一番“咬文嚼字”,算是贯彻了这篇课文主张的精神和方法;其次,对于学生来说,“从具象到抽象”比“从抽象到抽象”更易把握,一个好的案例胜过一大堆的说教。如果把《咬文嚼字》当作一篇讲文艺的寻常议论文来教,很可能无法让学生领受到它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