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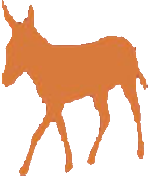 第二章
第二章
我出了奥维多城,走上贝尼弗罗大道,周围都是旷野,从此我自己做主了,而且有一头劣等骡子和四十枚响当当的杜加,我从那位有体面的舅舅那儿偷来的几个瑞阿尔
 还没算在里面。我头一件事是让那骡子遂着性儿走,那就是让它慢慢踱去。我把缰绳撂在它脖子上,口袋里掏出杜加,摘下帽子来盛着,一遍两遍地数。我从没见过那么多钱,赏玩个不休。我大概数了二十来遍,忽然骡子昂头竖耳,路中心站住不走了。我想它吃了什么惊,仔细去看个究竟。只见地上一只帽子,口儿朝天,里面一串粗粒子的念珠。一壁听得凄声惨气地喊道:“过路的大爷啊,发发慈悲,可怜我这个残废军人吧!请你往帽子里扔几个钱,生前行好事,死后自有好报哇!”我赶忙随着声音转眼去瞧,看见二三十步外一丛灌木底下,一个兵士模样的人把两根棍子交叉着支起一杆马枪,看来比长枪还长,枪口正瞄着我。我一看吓得发抖,生怕教堂里得来的财产要保不住了。我立刻止步,忙把杜加藏好,抓出几个瑞阿尔,走近那只向心惊胆战的信徒募化的帽子,一个一个往里扔,让这位军人看我多么大方。他见我这样慷慨很满意,就一声一声连连祝福我,我也一脚一脚连连踢那骡子的肚子,要赶快走开。偏生这头该死的骡子满不理会我慌忙,还是慢条斯理地走;它多年来只惯驮着我舅舅稳步徐行,早跑不快了。
还没算在里面。我头一件事是让那骡子遂着性儿走,那就是让它慢慢踱去。我把缰绳撂在它脖子上,口袋里掏出杜加,摘下帽子来盛着,一遍两遍地数。我从没见过那么多钱,赏玩个不休。我大概数了二十来遍,忽然骡子昂头竖耳,路中心站住不走了。我想它吃了什么惊,仔细去看个究竟。只见地上一只帽子,口儿朝天,里面一串粗粒子的念珠。一壁听得凄声惨气地喊道:“过路的大爷啊,发发慈悲,可怜我这个残废军人吧!请你往帽子里扔几个钱,生前行好事,死后自有好报哇!”我赶忙随着声音转眼去瞧,看见二三十步外一丛灌木底下,一个兵士模样的人把两根棍子交叉着支起一杆马枪,看来比长枪还长,枪口正瞄着我。我一看吓得发抖,生怕教堂里得来的财产要保不住了。我立刻止步,忙把杜加藏好,抓出几个瑞阿尔,走近那只向心惊胆战的信徒募化的帽子,一个一个往里扔,让这位军人看我多么大方。他见我这样慷慨很满意,就一声一声连连祝福我,我也一脚一脚连连踢那骡子的肚子,要赶快走开。偏生这头该死的骡子满不理会我慌忙,还是慢条斯理地走;它多年来只惯驮着我舅舅稳步徐行,早跑不快了。
我出门碰见这件事,觉得兆头不妙。我想萨拉曼卡还远着呢,难保不碰到更倒霉的事,心里怪舅舅疏忽,没把我交托给骡夫照顾。他应当那样办才对;不过他只想到给了我这头骡子可以省些旅费,算计了这方面,没估到我路上的风险。我要为他补过,打定主意,如果侥幸到达贝尼弗罗,就卖掉骡子,雇一头包程骡子到阿斯托加,从那里再雇包程骡子到萨拉曼卡。我虽然没离开过奥维多,动身前先打听过这些必经之路,所以都知道。
我安抵贝尼弗罗,在一家像样的旅店门口停下;脚没落地,这旅店主人早满面春风地出来迎接。他亲手解下皮包,扛在肩上,领我到一间客房里,他的手下人也把骡子牵到马房里去。这位店主人可算阿斯杜利亚境内嚼舌根儿多说话的第一名,动不动无谓扯淡,讲自己的事,又爱管闲账打听人家的事。他说,他名叫安德瑞·高居罗,在皇家军队里当过好多年军曹,十五个月以前为了要娶个卡斯托坡尔的姑娘,所以退伍的;又说那姑娘皮肤稍为黑些,却是店里一块活招牌。他还说了许多话,我都懒得理会。他讲了这些体己,觉得有权来盘问我了,问我哪里来,哪里去,又问我是谁。我只得一一回答,因为他每问一句,就对我深深鞠躬道歉,请我别怪他多问,弄得我不好意思不理他。这就招得彼此长谈起来。说话中间,我讲起打算卖掉骡子改雇包程骡子的事。他十分赞成,不是干脆说赞成,而是就题发挥,告诉我路上会碰到各种麻烦,还叙述了旅客身经的许多恐怖。我只怕他一辈子讲不完,他也有讲完的时候。末了他说,如果我要卖掉骡子,他认得一个可靠的马贩子也许要买。我烦他把那人找来,他立刻亲自找去了。
一会儿他带了那人来见我,满嘴称赞他诚实可靠。我们三人跑到院子里,骡子也牵来了,在马贩子前面走了几个来回。马贩子把骡子从头到脚细看,少不了指出许多毛病。老实说,这头骡子可赞之处不多,不过即使它是教皇的坐骑
 ,那马贩子也会挑剔出些坏处来。他一口咬定我那骡子百病俱全,怕我不信,抬出店主人来作证;店主人自有他的道理,句句附和。那马贩子冷冷地说道:“好吧,你这头骡子很次想卖多少钱哪?”我听了他的品评,又以为高居罗先生为人诚恳,并且是鉴别骡马的大行家,既有他从旁坐实,那骡儿是不值一文钱的了。所以我对马贩子说,我相信他是个老实人,请他凭良心说个价钱,估定多少,我一无异议。他摆出正人君子的嘴脸,说我请出他的良心来,恰捉住他的短处了。良心果然不是他的长处;我舅舅估计这骡子值十二个比斯多,他却大胆老脸,只估了三个杜加。我收下钱,满心欣喜,好像这买卖是我占了便宜。
,那马贩子也会挑剔出些坏处来。他一口咬定我那骡子百病俱全,怕我不信,抬出店主人来作证;店主人自有他的道理,句句附和。那马贩子冷冷地说道:“好吧,你这头骡子很次想卖多少钱哪?”我听了他的品评,又以为高居罗先生为人诚恳,并且是鉴别骡马的大行家,既有他从旁坐实,那骡儿是不值一文钱的了。所以我对马贩子说,我相信他是个老实人,请他凭良心说个价钱,估定多少,我一无异议。他摆出正人君子的嘴脸,说我请出他的良心来,恰捉住他的短处了。良心果然不是他的长处;我舅舅估计这骡子值十二个比斯多,他却大胆老脸,只估了三个杜加。我收下钱,满心欣喜,好像这买卖是我占了便宜。
我出脱骡子,占了这般便宜。店主人就领我去找一个明天上阿斯托加的骡夫。据他说:天不亮就要动身,到时会来叫醒我。我们讲定了雇费和一路的伙食费,一切停当,我和高居罗同回旅店。一路上他对我讲那骡夫的身世,又讲这城里人对那骡夫的口碑。总而言之,他又要烦絮得我头涨了。幸喜这时来了个人,相貌还漂亮,跟他打招呼,礼数周到,把他话头截断。我走我的路,让他们俩说话去,没想到他们的话会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一到旅店,就叫晚饭。这天是不吃肉的斋日,只好将就吃鸡蛋。我这时候才见到女掌柜;我等着店家做菜,先跟她闲聊。我觉得她长得不错;尽管她丈夫没讲,我一见她那股子风骚劲儿,就断定这旅店一定生意兴隆。我等炒鸡子儿送了上来,一人坐下吃晚饭;第一口还没到嘴,只见店主人进来了,背后跟着那位在路上招呼他的人。这位绅士带着一把长剑,大概有三十来岁年纪。他急忙赶过来,说道:“学士先生!我刚知道您就是吉尔·布拉斯·德·山悌良那先生!奥维多的光彩!哲学界的明灯!哪里想得到您就是那位大名鼎鼎、博而又博的大学者大才子!”又转向店主夫妇道:“你们还不知道光临你家的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你们店里落下个宝贝了!这位年轻先生是世界上第八件稀罕物儿!”
 他于是抱住我脖子道:“别怪我乐得发狂,我看见了您高兴得忘形了。”
他于是抱住我脖子道:“别怪我乐得发狂,我看见了您高兴得忘形了。”
我一时答不出话,给他搂得太紧,气都回不过来。直等他松了手,我才说道:“先生,我想不到贝尼弗罗的人会知道我的名字。”他依然那种腔吻,说道:“何止听到您的名字呀!这里周围二十哩
 以内的大人物,我们都有记录。您是我们这儿公认的奇才。我相信西班牙出了一个您这样的人,大可引以自豪,就好比希腊有了七哲
以内的大人物,我们都有记录。您是我们这儿公认的奇才。我相信西班牙出了一个您这样的人,大可引以自豪,就好比希腊有了七哲
 那样。”他说完这话,又把我拥抱一番。我只得生受他,险的没像安泰
那样。”他说完这话,又把我拥抱一番。我只得生受他,险的没像安泰
 一般结局。我要是稍通人情世故,就不会给他那种奉承夸张哄倒,一听他恭维过火,就会知道这是个吃白食的篾片,各处城市里多的是,只要有外方人到了,赶快攀附上去,哄这冤桶花钱,乘机大吃一顿。可是我年轻爱吃马屁,看错了人。我以为这位仰慕我的是上等君子,就留他同吃晚饭。他嚷道:“啊!那就好极了!我多承福星高照,碰到大名鼎鼎的吉尔·布拉斯·德·山悌良那先生!我能多跟您盘桓一刻,还有不乐意的么!”接着又道:“我胃口不好,不过是坐下来陪陪您,吃几口应个景儿。”
一般结局。我要是稍通人情世故,就不会给他那种奉承夸张哄倒,一听他恭维过火,就会知道这是个吃白食的篾片,各处城市里多的是,只要有外方人到了,赶快攀附上去,哄这冤桶花钱,乘机大吃一顿。可是我年轻爱吃马屁,看错了人。我以为这位仰慕我的是上等君子,就留他同吃晚饭。他嚷道:“啊!那就好极了!我多承福星高照,碰到大名鼎鼎的吉尔·布拉斯·德·山悌良那先生!我能多跟您盘桓一刻,还有不乐意的么!”接着又道:“我胃口不好,不过是坐下来陪陪您,吃几口应个景儿。”
这位恭维我的人说着就对面坐下。店家添上一份刀叉。他认定炒鸡蛋狠命地吃,好像饿了三天似的。我看他那副应个景儿的神气,知道立刻就要盘底朝天了。我又叫了一盘炒鸡蛋,厨房里菜做得快,我们——其实竟是他一人吃完了那第一盘,第二盘接着就来。他依然吃得飞快,一张嘴不停地咀嚼,却还能腾出空儿来把我奉承了又奉承,奉承得我志得意满。他又一杯杯喝酒,一会儿喝酒祝我健康,一会儿祝我父母健康,说他们能有我这么个儿子,真使他不胜赞叹。同时他又替我斟上酒,要我赏他面子也喝点儿。我干杯还祝他健康。这样一杯杯地喝,又有他的马屁下酒,我不知不觉兴致勃发,眼看第二盘炒鸡子儿又吃去一半,就问店主人能不能来一条鱼。这位高居罗先生看来是和这篾片通同一气的,说道:“我有一条顶好的鲟鱼,不过谁想吃它,价钱可不小!这东西太精致,你们还不配。”我的拍马朋友提高了嗓子嚷道:“什么话!太精致?朋友啊,你说话太不知进退了。我告诉你,你这儿没有吉尔·布拉斯·德·山悌良那先生不配享用的东西。你应该把他当王爷一般供奉!”
他把店主人驳倒,正中我意,我也要说那句话。我觉得店主人得罪了我,所以傲然吩咐说:“你把那鲟鱼做上来就得了,别的事不用你管。”店主人巴不得我说这一句,连忙动手,一会儿送上菜来。这位篾片见了新上的菜,我看他乐得两眼放光,又要重新应个景儿,拿出方才吃炒鸡蛋的狠劲儿来对付这条鲟鱼。他吃得撑肠拄肚,怕要涨破肚皮,只得罢休。他酒醉饭饱,觉得这幕滑稽戏该收场了,就站起来说道:“吉尔·布拉斯先生,承你请我吃好东西,我很快乐;看来得有人指点你一句要紧话,所以我告辞之前,特地向你说说。从今以后,小心别相信人家奉承,对陌生人防着些儿。你将来还会碰到些人,也像我这样,看你老实可欺,就捉弄你,也许恶作剧还要厉害呢!下回可别上当了!别听了人家一句话,就当真相信世界上第八件稀罕物儿就是你先生!”他说完当面打个哈哈,扬长而去。
我上了这个当,无地自容,往后我还有好多更丢脸的事,可是羞愧也不过如此。我气的是做了那么个大冤桶,说得好听点,我的自尊心受了磨折。我心想:“嗨!怎么!这奸贼原来是捉弄我么?他刚才招呼店主人,原来是要套问我的底细,也许他们俩竟是串通一气的!啊,可怜的吉尔·布拉斯!活活的羞死人啊!让这起混蛋抓住个好把柄来捉弄你!他们还要把这事编成笑话,说不定会传到奥维多,替你大扬名气呢!你爹妈那般苦口教导你这傻瓜,一定要后悔了。他们不该劝我别欺骗人,该教我别受人家欺骗才对。”我给这些扫兴的念头搅得心烦,又加愤火中烧,便关了门上床睡觉。可是我哪里睡得着,翻来覆去了半夜,刚合上眼,我的骡夫已经来叫我了。他说只等我去,就可以动身。我赶忙起来,正穿衣服,高居罗送上账来,那鲟鱼是不会漏掉的。我只得尽他敲竹杠,而且我付钱时看出那混蛋在回想昨宵的事,越发羞愤不堪。昨夜那顿食而难化的饭害我出了好一笔冤钱;于是我拿了皮包到骡夫家去,一面咒骂着那骗子、那旅店主人和他的旅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