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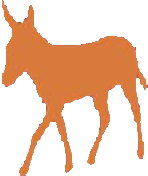 第三章
第三章
不久以后,堂文森病了。病势很凶,即使他没上年纪,只怕也不会好。他一有病,家里就把马德里最有名的两位大夫请来。一个叫做安德罗斯大夫,一个叫做奥克托斯大夫。他们聚精会神地瞧了病,又把征候仔细研究一番,同声说病由是身体里津液激荡,可是此外他们就各说各的。一位大夫要当天就用泻药,那一位主张缓一缓。安德罗斯说:“虽然津液还生,
 应该乘它动荡回旋很厉害的时候就打清它,免得留滞在心肺胃脑那些要害器官里。”奥克托斯的主张适得其反,他说应该等津液熟透再打。第一个大夫道:“可是你这个方法跟医学祖师的遗教恰好相反了。希波克拉底说,病人发高烧,一开头就该用泻药。并且说得明明白白,应该乘津液亢旺,赶紧清泻。‘亢旺’就是指津液激荡。”奥克托斯辩道:“唷!你这可是弄错了。希波克拉底所谓‘亢旺’,不是说津液激荡,是说津液融洽。”
应该乘它动荡回旋很厉害的时候就打清它,免得留滞在心肺胃脑那些要害器官里。”奥克托斯的主张适得其反,他说应该等津液熟透再打。第一个大夫道:“可是你这个方法跟医学祖师的遗教恰好相反了。希波克拉底说,病人发高烧,一开头就该用泻药。并且说得明明白白,应该乘津液亢旺,赶紧清泻。‘亢旺’就是指津液激荡。”奥克托斯辩道:“唷!你这可是弄错了。希波克拉底所谓‘亢旺’,不是说津液激荡,是说津液融洽。”
我们这两位大夫争吵得热闹起来。一个引证希腊原本,还举出许多书都像他这样解释的。那一个根据拉丁译本,说来更振振有词。谁是谁非呢?堂文森无从判断。可是他一看非得挑定一位不可,就相信了那位杀人较多,也就是年纪较老的一位大夫。安德罗斯是年轻的一个,立刻起身告辞,可是不免还借“亢旺”两字对那年老的挖苦几句。这回奥克托斯得意了。他的手法跟桑格拉都大夫一样,所以一上来就狠狠地抽血,要等他身体里的津液熟透再用泻药。他慎重得很,泻药还要缓着用呢。准是死神怕那剂清泻药救了病人的性命,所以不等津液熟透,就把我主人抢去了。堂文森大爷只为医生不懂希腊文,送了一条性命,他是这样下场的。
奥若尔按照她父亲的身份体面办了丧葬,从此自己掌管家私。她这回一切自主,就辞退几个用人,按功劳给了些酬谢。她家有个田庄,在塔古河边、萨瑟东和比安狄亚之间,她不久就到那田庄上去住。留下的几个用人都跟到那乡下去,我也在内,而且我有幸是她少不掉的人了。她虽然听我据实讲过堂路易的为人,还是爱着这位大爷。她实在是抑制不下爱情,只好随爱情摆布。她现在私下见我不必顾忌。她对我叹息道:“吉尔·布拉斯,我忘不了堂路易。我极力不想他,可是老想着他。我心目中,他是个温柔多情、有始有终的如意郎君,并不像你形容的那么任性胡闹。”她说着伤心,不禁掉下泪来。我看她下泪也很难过,险的陪眼泪。我对她的烦恼这样同情,真是讨她喜欢的无上妙法。她擦干了美目,说道:“朋友,我看你天性很厚,我也喜欢你这样忠心,一定要好好儿谢你。亲爱的吉尔·布拉斯,我现在更非你帮助不可了。我心上有个打算,该说给你听听,你一定觉得很奇怪。我告诉你,我不久就要到萨拉曼卡去。我准备到那里改扮男装,自称堂斐利克斯,于是去和巴洽果结交,设法跟他结为心腹朋友。我只算奥若尔·德·古斯曼的表哥,常常谈起这位表妹。他也许会想见见她,这就堕我计中了。咱们到萨拉曼卡弄两所房子。我在这一处是堂斐利克斯·曼多斯,在那一处是奥若尔。我有时候装了男人和堂路易见面,有时候穿我原来的服装见他。照这样一步步拉拢,我想就能如愿以偿。”她又道:“我承认这是个很荒唐的计划,不过爱情驱使着我,而且我心地清白,所以敢不顾一切地冒这个险。”
我和奥若尔所见相同,认为这计划是胡闹。不过我尽管觉得这事荒唐,绝不去训戒她。我反而渲染一番,把这个疯疯癫癫的计划说成个有趣的玩意儿,没什么大不了。我记不起还举了些什么凭据,反正她全相信;痴情人想入非非,喜欢人家附和。我们把这件轻举妄动的事当做一出喜剧,以为只消想法好好儿排演就完了。我们挑了几个用人来串这戏,分派好角色。我们不是吃戏子饭的,并没有你争我抢。当时选定奥蒂斯扮奥若尔的伯母,取名齐梅娜·德·古斯曼,她手下用一个男用人、一个女用人。奥若尔扮了大爷,我就做亲随,另外叫个女佣人扮做小僮儿贴身服侍。我们把登场人物照这样分配停当,就回马德里。我们打听得堂路易还在那里,不日要动身到萨拉曼卡去。我们就把有用的行头赶紧置办。小姐等一切齐备,吩咐立刻打上包裹,因为还不到穿着的当儿呢。于是她把家事交托给管家,带了这出戏里要上场的用人,乘一辆四骡车向雷翁境进发。
我们已经过了旧加斯狄尔境,忽然车轴断了。那地方正在阿维拉和维拉富罗之间,遥遥望见三四百步之外山脚下有一个田庄。暮色渐深,我们非常狼狈。恰巧有个农夫经过,随口一句话救了我们出难。他说,我们望见的是堂娜艾尔维拉的田庄,她是堂彼德罗·德·比那瑞斯的寡妇。那农夫把这位太太极口称扬,因此小姐就派我去借宿。那农夫的确没有过赞,当然也亏我措辞得体,艾尔维拉即使不是个顶有礼貌的人,听了也会接待我们。她见了我很客气,我代主人致意,她的回答正合我的希望。于是骡子慢慢地拉着车,我们大伙儿都到那田庄上去。堂彼德罗的寡妇在门口迎接小姐。她们相见的客套我这里不提了。且说这位艾尔维拉老太太比交际场中的夫人还招待周到。她请奥若尔到一个极华丽的房间里去歇一会儿,又来招呼我们,无微不至。晚饭做得,她吩咐摆在奥若尔房里,两人同吃。堂彼德罗的寡妇很能尽东道之谊,不像有种主人,吃饭心不在焉,或者脸色不快。她高高兴兴,有说有讲。她谈吐很高雅,我佩服她聪明、心思细致。奥若尔好像也一样喜欢她。她们俩做了朋友,还约定要通信呢。我们的车要过一天才修理得好,恐怕动身的时候天太晚了,所以决定在她家多住一宵走。我们底下人的饭菜也很丰盛,而且不但吃得好,睡得也舒服。
第二天,我们小姐跟艾尔维拉谈得更相投了。她们俩在一间大厅上吃饭,壁上挂着好几幅画。有一幅特别惹眼,画得栩栩欲活,而画的景物很凄惨。画着一个绅士朝天倒在血泊里,看来已经死了,脸上还是一副恶狠狠的神气。他旁边横着个年轻女人,她另是一种神情。她胸口戳着一把剑,还没有咽气,眼光欲敛,还恋恋不舍地望着个少年人。那少年要和她永诀了,仿佛痛不欲生的样子。我留心画上还有个人。这是个慈祥的老者,他触目伤心,脸上的悲痛跟那少年人不相上下。看来他们两人对着这血淋淋的景象都有切肤之痛,只是感触不同。那老人悲深痛切,已经不能自支;那少年人伤心之中带着愤怒。画里把那些形形色色都传出神来,我们看得目不转睛。小姐便问这是画的什么惨事。艾尔维拉道:“小姐,这是一幅写真,写着我家的一桩痛史。”奥若尔听了心痒,很想更知一二。堂彼德罗的寡妇见她那么好奇,只得依她。当时奥蒂斯和她两个伙伴还有我都在旁边,听见她这样答应的,所以等她们吃完饭,我们四个都赖在那厅上不走。我女主人要把我们遣开,可是艾尔维拉看透我们心痒痒的要听她讲那画上的情节,就很体谅,说那事不是秘密,我们不必走开。一会儿,她就讲了下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