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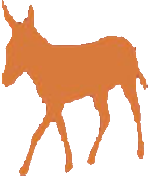 第一章
第一章
我在这年轻理发师家里住了些时候。随后我跟一个路过奥尔梅都的塞哥维亚商人一同上路。这商人带了四头骡子运货物到瓦拉多利,现在空身回去。我们在路上相识,他跟我非常要好,到了塞哥维亚一定要我住在他家里。他留我住了两天,看我要乘包程骡子到马德里去,就交给我一封信,没说明是介绍信,只叫我按照姓名住址亲自送去。我一点不误事,把信送给马狄欧·梅朗代斯先生。他是开呢绒店的,住在太阳门箱子匠街拐弯儿。他拆信一看,满面春风,说道:“吉尔·布拉斯先生,彼德柔·巴拉西欧来信说得你真好,我一定要留你住在我家里。他还托我替你找个好东家,我也愿意帮忙。为你觅个好位置,我想不难的。”
我眼看身边的钱越花越少,梅朗代斯请我住,来得正好。可是我并没有打扰他多久。八天以后,他说有位相识的绅士要找亲随,他刚保荐了我,看来这位置跑不掉是我的。果然,那绅士立刻来了。梅朗代斯指着我说道:“大爷,这就是我刚才和您谈起的小伙子。这孩子又诚实又规矩,我要是担保不了他,就连自己都不能担保了。”这绅士目不转睛地看我,说我样子长得不错,就想雇用。又道:“他跟我回去得了;他做的事,我会教他。”他说完对那商人道声早安,就带我顺着圣斐利普教堂前面的大街走。我们到一宅很漂亮的房子里,他住的是侧面一溜屋;上了五六级台阶是两重很结实的门,第一重门上有一个安栅栏的窗洞,进去是一间房,从这间穿进去又是一间,铺着张床,还有些陈设,都说不上富丽,只是很干净。
我的新主人在梅朗代斯家里仔细端详过我,我也留心看了他一番。这人有五十多岁,神气沉静严肃。我看他是个好脾气,觉得他不错。他问了几句我家里的情形,对我的回答都很满意,说道:“吉尔·布拉斯,我瞧你这孩子很明白,你做我的亲随,我可以放心。在你呢,这个位置也不委屈你。我每天给你六个瑞阿尔,折你的饭食、衣着和工钱,外快不算。而且我这人不难伺候,我在外边吃饭,家里不开火。你每天早晨把我的衣服拾掇干净,此外整天都没事儿。我只吩咐你一句话,你记着天黑了要早早回来,在门口等我;我就责成你这一点。”他把我的职司吩咐完毕,就履行契约,从口袋里掏给我六个瑞阿尔。我们俩一同出来,他亲自锁上门,把钥匙带在身上,对我说道:“朋友,不要跟我;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满城溜达去得了。不过我晚上回来的时候,你得先在这儿楼梯边等着。”他说完走了,由我自在逍遥。
我对自己说:“吉尔·布拉斯,你实在没处再找更好的主人了!怎么的呀!这人只要你掸掸他衣裳上的灰,拾掇拾掇房间,一天给你六个瑞阿尔,还让你自由自在地溜达消遣,像放了假的学生!谢天,这事称心极了。怪不得我那么急煎煎地要到马德里来,一定是预先觉得有好运气在这儿等我呢。”我白天在街上逛,看看没见过的新鲜东西,也就够忙。傍晚,我在寓所邻近小饭店里吃过晚饭,就赶到主人指定的地方去等。过了三刻钟,他回来了,瞧我准时不误,好像很高兴,说道:“很好,这就不错,我喜欢用人做事认真。”他说着开了那两重大门;我们一进去,他立刻把两重门都关好。我们是在暗地里,他用火石火绒儿打个火,点上一支蜡烛,于是我伺候他脱掉衣裳。我等他上了床,照他吩咐,点了壁炉架上的灯,把蜡烛拿到外间。那里有一张没帐子的小床,我就躺下睡觉。第二天早上九十点钟,主人起来,我替他掸干净衣裳。他数了六个瑞阿尔给我,打发我出门一天。他仔细把门锁好,也就出去,我们这一整天就各走各的了。
我们每天如此,我非常称心。最妙的是我不知道主人的姓名,梅朗代斯也茫然,只晓得是位主顾,常买他的呢绒。我打听街坊,都说不上来,我主人虽然在那里住过两年,他们全不认得。据说他和邻居一无来往。有人惯爱冒冒失失地下断语,就咬定他不是好东西。后来人家越发胡猜乱讲,疑心他是葡萄牙皇帝派来的奸细,还好意警告我防着点儿。我听了很着急,这话要是确凿,我就保不住要光顾马德里的监牢了,想来不会比别处监牢里舒服的。我遭过殃,对法院有戒心,尽管无罪无辜,也不敢托大。法院即使不要无辜良民的性命,至少招待不周,谁上他的门就是活倒霉,我尝过两次风味了。
我这事很尴尬,就去请教梅朗代斯。他也没了主意。他不信我主人是奸细,但又无从断定他不是。我决计对东家留心察看,假如真是我们国家的敌人,就撇了他走。不过我觉得做事应该仔细,而且这是个好饭碗儿,得打听着实再辞。我就留心他的行动。一天晚上我替他脱衣裳,想探他口气,就说:“先生,我不知道为人在世应该怎样才免得人家闲话。天下人真恶毒!别人不说,咱们这些街坊实在不是东西。那起混账人!您再也想不到他们怎么说您来着。”他答道:“是么!吉尔·布拉斯。哎,朋友,他们能说我什么呢?”我答道:“啊,真是,要说坏话总有得说的,随你头等好品行,人家一样会造谣言。他们说咱们是坏人,法院应该注意。干脆说吧,他们以为您是葡萄牙皇帝的奸细。”我一面说,一面瞅着我主人的脸,仿佛亚历山大大帝瞅他医生那样
 ,我全神贯注,要看这番话有什么效验。我主人好像发了一阵抖,可见街坊的猜测不错;他又呆呆地出神,看来很可疑。不过他立刻神色如常,若无其事地说道:“吉尔·布拉斯,街坊爱怎么想,随他们想去,咱们别挂在心上。咱们没干坏事,不必怕人家议论。”
,我全神贯注,要看这番话有什么效验。我主人好像发了一阵抖,可见街坊的猜测不错;他又呆呆地出神,看来很可疑。不过他立刻神色如常,若无其事地说道:“吉尔·布拉斯,街坊爱怎么想,随他们想去,咱们别挂在心上。咱们没干坏事,不必怕人家议论。”
他说完就睡了,我也上床,不知道对这件事究竟应该怎么个看法。第二天早上,我们正要出门,听得临台阶的大门打得一片响。我主人开了里面一重门,从小窗口的栅栏往外张望。只见一个衣服整齐的人,说道:“大爷,我是个公差,特来通知你,本地法官老爷要找你说话。”我主人道:“他找我干吗?”公差道:“大爷,这个我可不知道,你见了他就会明白。”我主人道:“我向他致敬,我跟他毫无交涉。”他说完砰地把里面那重门关上,于是在房里踱了一会儿,仿佛听了公差的话很上心事。他给我六个瑞阿尔,说道:“吉尔·布拉斯朋友,你可以出去随意逛一天了,我这会子还不出门,今儿早上也不用你伺候。”我听了这话,想他是怕给人抓去,只好躲在家里。我撇他在家,要瞧瞧我猜测得对不对,就找个地方躲着,他要是出门,那儿看得见。我真会耐心守他一上午,只是他省了我的事。一个钟头以后,我看见他打街上过去,神气很安闲,我一上来真看不透他了。可是我对他有成见,他那外貌哄不倒我,我决不相信。我想他那副神气准是假装的,甚至于想他在家无非要收拾金子宝石,大概这会子急急逃命去了。我满以为跟他没有再见之缘,想他大难临头,从此溜出马德里,也许我晚上都不必在门口等他了。可是我还回去等着,想不到主人竟照常回家。他上床睡觉,好像一点没什么心事;第二天早上起来,照样没事人儿一般。
我主人刚穿好衣裳,忽听得打门。他隔着栅栏一看,认得是昨天来的公差,就问有什么事。公差道:“开门,法官老爷来了。”我一听见这个威风凛凛的头衔,吓得浑身冰冷。我受过这班老爷收拾,怕得要命,这时恨不得身子远在马德里一百公哩之外。我主人不像我那样害怕,他开了门恭恭敬敬请法官进来。法官道:“你瞧,我愿意把事情干得悄悄默默的,没带着大队人上你家来。尽管你名声不好听,我觉得还不该下辣手。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在马德里干什么事。”我主人道:“先生,我是从新加斯狄尔来的,我名叫堂贝尔那·德·加斯狄尔·布拉左。我干的事就是散散步,看看戏,每天跟几个意气相投的人一同玩玩。”法官道:“你收入一定很多了?”我主人打断他道:“不,先生,我没房没地,没有收入。”法官道:“那么你靠什么过日子呢?”堂贝尔那道:“我靠什么过,我来给你瞧。”他就掀起一幅壁衣,后面有扇门,我从没见过;他开了这门,又开了后面一重门,把法官让进这个小房间,里面有只大箱子,打开一看,满满的都是金元。
他对法官道:“先生,你知道西班牙人都不爱做事;不过他们虽然懒,总懒不过我。我天生懒骨头,什么事都做不来。我要是把自己的短处说成长处,我的懒惰可说是哲人的物外逍遥,世人攘攘追逐的一切,我可说都看破了,我潜心修养,到了这个境地。不过我直认自己生性懒惰,而且懒得厉害,假如我非得做事才有饭吃,准要饿死的。我要过得随心如意,不必费神经营财产,尤其可以不用总管,就把承袭来的几份大家私全换了现钱。这一箱有五万杜加。我已经五十开外,一年花不到一千杜加,就是活到一百多岁也享用不尽。我不忧来日,谢天!破家荡产的那三种通病我都不犯。我不贪吃喝,赌钱不过是消遣,对女人也腻味了,我老来决不会做那种千金买笑的老色鬼。”
法官听了道:“我瞧你实在好福气!人家怀疑你当奸细,真是大错。你这样性格绝不是那种人。好,堂贝尔那,你照常过你的日子得了。我非但不来打扰你的清静,还声明要加以保障呢。我愿意跟你做个朋友,希望你不弃。”我主人听他说得恳切,大为感动,说道:“啊呀!先生,难得你这片好意,我欢欢喜喜、恭恭敬敬地领你的情。承你见爱,我就更加富足,我的福分就十全了。”这段谈话,我和公差在门外都听得清楚。于是法官告辞,堂贝尔那对他说不尽的感激。我要帮东家做主人,对公差非常多礼。一切好人对公差自然的又怕又恨,我心里也有同感,可是我还对他深深鞠躬了不知多少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