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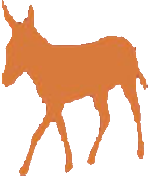 第八章
第八章
狄艾果·德·拉·夫安特先生还讲了些以后的经历,我以为不值得转述,所以不提了。我当时只好听他的长篇大章,一路听到彭特·德·居若。我们就在那镇上歇半天。两人在客店里要了一个白菜汤、一只烤野兔子,先留神看过烤的确是兔子。第二天清早,我们把皮袋盛满了酒,那酒还不坏,又把几块面包和晚饭吃剩的半只野兔子塞在口袋里,仍旧赶路。
我们走了二哩路左右,有点饿了,看见离大道二百步上下有几株大树、一片清阴,就去歇脚。有个二十七八岁的人,也在那里,拿了干面包头儿在泉水里蘸。旁边草地上横着一把长剑,还有一个卸下的背包。他衣衫褴褛,可是身材相貌都不错。我们客客气气和他招呼,他也照样还礼。于是他拿着干面包头儿,笑容可掬地请我们同吃。我们领情,只要求把我们带的早点凑上,可以好好吃一顿。他欣然答应,我们立刻把身边的口粮陈列出来,这位陌路相逢的人看了很快活,喜不自胜地嚷道:“啊呀,两位先生,你们的口粮好丰富!我看你们真是有成算的人。我啊,出门从无准备,多半碰运气。可是你们别瞧我这样子,不是我夸口,我有时候也很出风头呢。你们可知道,人家常常把我当王爷看待,我背后还跟着卫队。”狄艾果道:“我懂了,你无非说你是个戏子。”那人道:“你一猜正着。我少说也演了十五年的戏。我从小就扮童角儿。”那理发的摇头道:“不瞒你说,我不大相信。我知道戏子是怎么样的人,他们那起先生出门,不像你这样凭两条腿走路,也不像圣安东尼
 一般吃斋,只怕你只是个戏班子里打杂儿的。”那戏子道:“随你想吧,不过我扮的还是头等角色,我是扮情人的
一般吃斋,只怕你只是个戏班子里打杂儿的。”那戏子道:“随你想吧,不过我扮的还是头等角色,我是扮情人的
 。”我的同伴道:“既然如此,我恭喜你。吉尔·布拉斯先生和我能奉陪这样一位大人物用早点,荣幸得很。”
。”我的同伴道:“既然如此,我恭喜你。吉尔·布拉斯先生和我能奉陪这样一位大人物用早点,荣幸得很。”
我们就啃面包头儿,吃那剩下的几块宝贝也似的野兔子肉,又抱起皮袋来大口喝酒,一会儿把那袋酒喝个精光。我们三人吃得很认真,说话都没工夫。吃完之后,我们又闲聊起来。理发的对戏子说:“我奇怪,怎么你光景很艰难似的。一个戏院里的要角,像你这样子未免太寒窘了。我说话太直,你可别见怪。”那戏子嚷道:“太直啊,你真没知道我梅尔希华·萨巴塔呢!谢天,我脾气一点儿不别扭,我喜欢你直言,因为我心上有什么就说什么。老实讲,我穷得很。”他叫我们瞧他袄儿里衬的都是戏招子,一面说道:“瞧,我通常用这东西做衣里子。你们若要见识见识我的行头,我可以给你们看。”他说着,从背包里拉出一套衣裳,钉满了旧的假银花边儿;一只宽檐儿破帽子,上面插几支零落的羽毛;一双丝袜子,全是窟窿;一双红摩洛哥皮鞋,也破烂不堪。他道:“你们瞧,我穷虽穷,还勉强过得。”狄艾果道:“这倒没有想到。那么你是无妻无女的了?”萨巴塔道:“我有个少年美貌的老婆,可是无济于事。我的坏运气实在是少有的!我娶了个漂亮女戏子,指望靠她养活,可是活倒霉,她偏是个引诱不动的正经女人。谁保得住不上这个当呢?走码头的女戏子里只那么一个正经女人,偏偏落在我手里了。”理发的道:“那真是运气不好,不过你为什么不娶个马德里大戏班子里的女戏子呢?你就拿得稳了。”那戏子道:“这话很对,可是,他妈的,一个走码头的小戏子怎么敢高攀那些有名的女角儿呀!要皇家戏班里的戏子才轮得到呢。可是他们中间还有许多人只能娶市民家的女人。亏得马德里女人多的是,有好些真不输戏房里的公主。”
我的同伴说道:“哎,你倒不想进他们那戏班子?是不是非要有了不起的本事不行?”梅尔希华道:“好哇,说什么了不起的本事呢!你不是笑话人吗?那班子里有二十个戏子。你向人家打听打听去,口碑好着呢!大半还只配背上包裹走码头。不过话是这么说,要进他们那班子可不容易。你要是有钱,或者有权势显赫的朋友,本领不行也不要紧。我刚在马德里首次登台,还会不知道底细吗?观众应该喝我的彩,可是他们狠命地喝我倒彩。我叫啊,嚷啊,怪声怪调,矫揉造作,念台词的时候,把拳头直伸到女主角脖子底下,总而言之,我学的是国内第一流名伶的腔调。可是观众看了他们喜欢,看了我就受不了。你们瞧,这可不是横着个成见么?我演戏不吃香,要是有门路可走,尽管看客喝倒彩,依然可以进那个戏班子,偏偏我又没有,只得回萨莫拉去。我要去找我的老婆和我们班子里那些伙伴儿,他们生意不大好,几回都东挪西借才动得了身上别处去,但愿这回不至于那样窘。”
这位戏里的王爷说完起身,背上背包,挂上宝剑,满脸正经地对我们说道:
“——告辞了,二公再见;
老天爷,保你们洪福无边!”
狄艾果学着他那腔调答道:“你也洪福无边,愿你回到萨莫拉,老婆已经变节,有阔佬包定了。”萨巴塔先生一转背,就且走且做手势背台词。理发师和我立刻喝起倒彩来,叫他不忘记首次登台的情景。他听得喝倒彩,还道是马德里人的倒彩呢,回头看见是我们开玩笑,一点不生气,随我们取笑,打着哈哈走了。我们也笑了个畅,才回到大道上,走我们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