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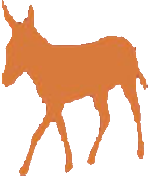 第七章
第七章
我从头讲起。我祖父范尔南·彼瑞斯·德·拉·夫安特在奥尔梅都村做了五十年理发师去世,遗下四个儿子。老大尼果拉斯接管了他的店,承继他那行手艺;老二贝特朗要做买卖,开了个丝绸铺;老三托马斯是个教书先生。那老四呢,名叫彼德柔,自以为生性跟文学相近,把遗产分来的一小块地卖掉,到马德里住下,指望凭自己那份才学有一天会享大名。他三个哥哥一直没分开,都在奥尔梅都成家立业,娶的都是农家女儿。她们陪嫁不多,子息却不少,恰好来个扯直。几个妯娌竞赛似的生孩子。我妈妈是理发师的老婆,结婚五年,生了六个孩子,我是其中一个。我爹老早教我剃胡子,到我十五岁,就把你看见的那只口袋搭在我肩膀上,替我挂上一把长剑,说道:“走吧,狄艾果,你现在可以自己谋生了,各处跑跑去。你该出门走走,磨炼一番,把手艺学到家。去吧,不走遍西班牙,别回奥尔梅都;回家以前,别让我听到你的消息。”他说完,亲亲热热把我拥抱一下,就推我出门。
我爹是这样跟我分别的。我妈不那么粗率,好像不大舍得我走。她掉了几点眼泪,还偷偷儿塞给我一个杜加。我就此离开奥尔梅都,取道上塞哥维亚。我没走上两百步,就歇下查看那只口袋。我急要看里面是什么,我到底得了些什么家当。只见一个盒子装着两把千磨万磨的剃刀,好像剃过了十代人似的;一条磨剃刀的皮带和一块胰子;此外是一件簇新的粗布衬衫,一双爹的旧鞋,还有一件我最喜欢的东西,是破布里裹的二十个瑞阿尔。这是我的全份家当。你由此可见尼果拉斯理发师很相信我的本事,只给了这点东西就打发我出门了。可是一个从来没钱的小子,有一个杜加二十个瑞阿尔就足以让他晕头转向。我觉得这笔钱一辈子也花不完,喜滋滋仍旧赶路,一面频频看那剑柄上的护手。一路上,那把长剑不是打我的腿肚子,就是绊我的脚。
我当晚走到阿达基内斯村,肚里饿得不得了。我下了客店,摆出一副有钱人的气派,高声叫店家开晚饭。店主把我端详一番,看透我是什么主顾,就和颜悦色地说:“得!我的小爷,准叫你称心,我们这儿把你当王爷般款待呢!”他说着领我到个小房间里,一刻钟后,送上一锅炖的公猫肉。我吃得满口香甜,仿佛那是家兔或野兔的肉。他给我吃这种佳肴,还送上些美酒,说皇帝喝的也不过如此。我吃得出那酒已经变味,不过还喝了不少,就像吃猫肉一样的尽量。他要把我当王爷般款待到底,给我的一张床不是供人睡觉倒是叫人失眠的。试想一张又狭又短的床,我个子虽小,躺下去还伸不直腿。上面只有一床草垫,蒙着一条双叠儿的被单,就算是褥子和羽毛被;那条被单,大概洗过之后又盖过一百个人了。亏得我年纪轻、脾气好,虽然躺在这种床上,填了一肚子猫肉和店家的美酒,还睡得很甜,一夜过去,胃里没积食。
第二天,我吃过早饭,又为昨夜那顿酒席付了好一笔账,就一口气赶到塞哥维亚。我一到那里,可巧有个理发店要我,管饭供宿,不给工钱。我只待了六个月,因为我相识的一个理发店伙计要上马德里,把我勾引出来,我就跟着同去。我在马德里又顺顺利利找到了事,待遇跟在塞哥维亚的一样。那一家的生意非常兴旺。那店挨着圣十字教堂,附近又是“皇家剧院”,所以招徕好多主顾。我东家和两个大伙计还有我伺候剃胡子,简直忙不过来。各式各样的顾客都有,也有戏子,也有作家。有一天,两个作家碰在一起。他们谈起当代的诗人和诗,我听见提起我叔叔的名字,本来没留心,这时忙机灵起耳朵来。一个说:“我以为观众不必尊重堂如安·德·萨华雷塔这种作家,他没有气魄,不善于想象。人家对他最近的剧本批评得真厉害。”一个说:“还有路易·费雷斯·德·盖华拉呢,他不是刚出版了一本大作么?比那本书更恶劣的东西还没见过呢。”他们又讲到不知多少别的诗人,我记不得名字,只记得都说是不行。他们对我叔叔口气还算不坏,说他有点才情。一个说:“是啊,堂彼德柔·德·拉·夫安特是个好作家,他写的书有风趣而很挖苦,又加上博学,所以很辛辣有味。怪不得他朝野闻名,许多阔人给他年俸。”那一个说:“这好多年来,他收入很可观。梅狄那·赛利公爵家供他吃供他住,他又没什么开销,手里一定好着呢!”
这两位诗人议论我叔叔的话,我一字没漏全听进去。我们家里曾经听说他在马德里有了文名,人家路过奥尔梅都讲的,可是他既然不屑通消息,和家里很疏远,我们也漠不关心了。不过骨肉之间总有天性;我一听说他光景很好,又知道他的地址,就心痒痒的想去找他。我只为一事踌躇,那两位作家称的是堂彼德柔,我为这个“堂”的称呼不大放心,恐怕说的不是我叔叔,是另外一个诗人。我却并不就此罢休,心想他既成才子,也会变贵人,决计去看看他。一天早晨,我向东家请了假,尽力修饰了一番出门。我有这么一位才大名大的叔叔,心里颇为得意。理发师也跟天下人一样爱面子。我自以为很了不起,一路上神气活现,问讯找到梅狄那·赛利公爵府。我向门上说,要找堂彼德柔·德·拉·夫安特大爷。门房指了院子尽头的小楼梯说:“从那儿上去,右手第一个门,敲门就是。”我照话走去打门。一个年轻人来开门,我问他堂彼德柔·德·拉·夫安特大爷是否就住这里。他回答道:“是的,不过他这会儿不见客。”我说:“我很想跟他谈谈,我带了他老家的消息来了。”他回答说:“你就是带了教皇的消息来,这会子也不能进去。他正在写文章,他动笔的时候切不可打搅他的文思。他要到中午才见客;你出去绕个弯儿,中午再来吧。”
我出来在城里溜达了整半天,一心盘算叔叔会怎样相待。我想:“他见了我准高兴。”我以己之心,度他之心,满以为叔侄相认一定会衷肠感动。到了时候,我急急赶回他家。他那佣人说:“你来得正好,我主人一会儿就要出门了。你在这儿等一等,让我通报。”他叫我在外间等着,过了一会儿,就来领我到他主人房里。我一看他主人的脸,活脱儿是我们家里人的脸,我仿佛见了托马斯叔叔,他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我恭恭敬敬行了个礼,说我就是奥尔梅都理发师尼果拉斯·德·拉·夫安特先生的儿子,到马德里已经三个星期。我承继爹的行业在一家理发店里当伙计,还准备走遍西班牙,把手艺学到家。我说着只觉得我叔叔在出神。他大概是打不定主意,还是不认我这个侄儿呢,还是慢慢想法子甩掉我。他用了第二个办法,装出一副笑容,说道:“哎!老侄!你爹跟你叔叔都好么?他们光景怎样啊?”我就把家里人丁兴旺的情形讲给他听,替一个个男孩子女孩子报了名字,连他们教父教母的名字都报出来。他听我这样委曲详尽好像并不兴味无穷,只直捷爽快道:“狄艾果,我很赞成你到各地游历,学成手艺。我劝你不要再待在马德里,青年人在这地方很有害处,孩子,你在马德里要堕落的。你还是上别的城市去,别处的风气不像这里荒唐。”接着说道:“你可以走了,你几时准备动身再来看我,到时我给你一个比斯多,贴补你周游全国的旅费。”他一面轻轻推我出门,把我撵走。
我太糊涂,没明白他无非要我离他远着些。我回到店里,把这次的拜访讲给我主人听。他也没看破堂彼德柔的心思,说道:“我跟你叔叔的意思不同。他不该劝你游历,该留你在这里。他认识那么些贵人,毫不费事就可以把你安插在阔人家,让你慢慢地撑起一份大家业。”这话正中我意,就此痴心妄想,过了两天又去找叔叔,请他仗面子荐我到朝里贵人家去当差。他不以为然。他是个爱摆架子的人,在阔人家出出进进,天天陪阔人吃饭,要是看见侄儿在底下人桌上吃,自己在主人桌上也不安心,堂彼德柔大爷的面子就给狄艾果小子扫尽了!他当然拒绝,而且很不客气。他怒冲冲道:“什么?你这小混虫!你要丢掉本行么?滚你的蛋!谁替你出这种馊主意,你就跟着他们去吧。快出去,再别上我的门,不然的话,给你一顿好打才是你活该呢!”我听了叔叔这泡话,尤其他那口气,不禁目瞪口呆。我含着一包眼泪出来。他那样无情,我很伤感。可是我一向心高气傲,立刻擦干眼泪。我不悲而怒,打定主意,从此再不理会这门子混账亲戚;直到如今,我从没有依仗他。我一心想学成本领,干活儿很勤。我整天剃胡子,到晚上学弹吉他琴散散心。教我弹琴的是一位年老的侍从先生,我常替他剃胡子。他也教我音律,他精通这一门,原来从前在大教堂里唱过诗的。这人叫马果斯·德·奥布瑞贡。他为人规矩,很聪明,阅历也多,把我当儿子一般喜欢。他就在离我们那儿三十来步的医生家里当太太的侍从。我每天傍晚一歇工就去找他,两人坐在门槛上奏乐,街坊听着也不讨厌。这倒并非我们嗓子好,不过我们一面拨弄琴弦,有板有眼地和声齐唱,听来也还悦耳。医生太太梅日丽娜尤其喜欢,她跑进过道来听,听到中意的调子就叫我们再奏唱一遍。她丈夫并不阻挡她这么消遣。那人虽然是西班牙人,年纪又老,却毫不拈酸吃醋,而且专心干他那一行,出诊了一天,晚上回来精疲力竭,老早就上床睡觉;他太太对我们奏乐有兴,他并不放在心上。大概他以为这种音乐不会坏人心术。我该声明一句,他对那位太太不必担心,梅日丽娜确是少年美貌,不过正经得厉害,男人瞧一眼都不许的。医生以为这种消遣纯洁正当,不是桩坏事,随我们唱个尽兴。
一天黄昏,我想照例娱乐一下,刚到医生门口,只见那老侍从正在等我。他拉住我手说,我们先出去遛个弯儿再来。他拉我转进一条背道,看看左右没人,面带愁容说道:“狄艾果,我的孩子,我有要事相告。孩子,咱们天天在我东家门口奏乐消遣,只怕你我都得懊悔呢。我当然很喜欢你,满情愿教你弹吉他唱歌儿,不过我要是早看到会有祸事临头,天啊,我就另外找地方教你了。”这话吓我一跳。我请他说说明白,究竟怕的什么,因为我不是个胆大冒险的人,况且我还要去游历西班牙呢。他解释道:“你要明白咱们处的险境,我非得先讲些事给你听。
“一年前我到医生家做事,他一天早上领我见他太太,说道:‘马果斯,见见你的女主人。你得陪侍的就是这位太太。’我仰慕堂娜梅日丽娜,觉得她漂亮得很,像画里的美人,尤其喜欢她举止温文。我回答说:‘先生,叫我伺候这么漂亮的一位太太,我福分真不小。’这句话触犯了梅日丽娜,她不耐烦道:‘瞧这人,真放肆!唉,我顶不喜欢人家对我甜言蜜语。’这样妩媚的嘴会说出这话来,我大吃一惊,觉得谈吐粗犷,跟她那温文的气派不称。她丈夫是见惯的,太太品性这样希奇他还很得意,说道:‘马果斯,我太太的品德真是世上少见。’他看见太太披上斗篷要去望弥撒,就叫我陪她上教堂。我们一到街上,碰到几个男人,他们看见梅日丽娜光艳夺目,对她迎面而过的时候就恭维几句。这本来不足为奇。她接口应对,说的话愚蠢可笑,出人意外。那些人想不到世上会有这种不识抬举的女人,都愣住了。我起初还对她说:‘哎,太太,别理会人家对你说的话,宁可不开口,别恶声恶气。’她道:‘不是这么说。我要叫这些大胆冒昧的家伙知道,我不许人家对我失礼的。’她还说了许多不讲理的话,我忍不住了,不顾她生气,把我的心思全说出来。我措词很宛转,告诉她说,这种暴戾的脾气不近人情,把她许多好处都毁了;女人温文有礼,不必相貌好也讨人喜欢,要不然,尽管长得漂亮也是个厌物。我要矫正她的态度,还讲了不知多少一类的道理。我训了她一大顿,只怕直言劝谏惹得女主人动火,反唇相讥。可是她听了并不生气,只置之不理;我以后几天还痴心告诫,她都当耳边风。
“我劝谏无效,也就懒了,随她脾气厉害吧。可是你相信么?这个性子烈、骨气傲的女人,两个月来完全变了,对谁都客客气气,非常温文。从前的梅日丽娜听了男人恭维就给钉子碰,现在不然了。她喜欢人家称赞、说她美、说男人一见她就颠倒;她爱听人家恭维,好像换了个人似的。她这一变简直不可思议,你要是知道那是你运的神通,还要吃惊呢。哎,亲爱的狄艾果,是你把堂娜梅日丽娜变成这样的,你把雌老虎驯伏得像个绵羊。总而言之,她心神贯注在你身上,我留心到不止一回了。要是我摸得准女人的性情,我敢说她对你痴心得厉害。孩子,这就是我要讲的糟心事儿,也就是咱们为难之处。”
我对老头儿道:“我不明白咱们为什么要这样担忧,我承蒙漂亮太太相爱,也不算倒霉呀。”他答道:“啊,狄艾果,这是年轻人的识见,只看香饵,毫不提防钓钩;你只图快乐,我却看到以后的一切麻烦。到头来事情要闹穿的。你要是照常到这门上来唱歌,撩得梅日丽娜火上加油,也许她把持不住,会给丈夫奥罗柔索大夫识破私情。这位丈夫现在无须吃醋,看来很随和,到那时候就要发狠报仇,可以叫咱们俩大吃苦头呢。”我说:“好吧,马果斯先生,我服你的理,听你的话。你说我该怎么才可以免祸呢?”他道:“咱们只要别再一起奏乐。你别再到我女主人面前来,她眼不见,心就冷了。你待在主人家,我会来找你。咱们在你那边弹吉他就没有危险。”我道:“很好,我决不再上你们家来。”我果然打定主意,再不到医生门上去唱歌。既然我这人一露面就会惹祸,从此要躲在自己店里了。
马果斯这好侍从尽管乖觉,过了两天,方知他设法叫梅日丽娜心冷反撩得她越发情热了。这位太太第二晚听不见我唱歌,就问他为什么我们不合奏,为什么我不去。他说我忙不开,没工夫作乐。她听了这个推托,也就罢了。以后三天,她不见我去,还是咬牙忍耐。于是这位公主娘娘耐不住了,对她侍从道:“马果斯,你哄我呢,狄艾果不来准有缘故。里面什么玄妙,我要问个明白。我命令你说出来,一字不许隐瞒。”他又编了一套话道:“太太,你一定要追根究底,我就说吧。他奏乐回去,那边往往晚饭都吃完了;他不敢再自讨苦吃,弄得饿着肚子上床。”她发急道:“什么?不吃晚饭啊?你怎么不早说呀?饿着肚子上床!啊!那可怜的孩子!你快去找他,叫他今夜就来,以后叫他吃了东西回去,这里总有他的一份晚饭。”
老侍从听了这话,假装诧异道:“我没听错么?天啊,你真是变了!太太,你怎么会说这种话呀?你几时起这样心软肠热的呀?”她不耐烦道:“自从你来之后,竟可以说,自从你怪我傲慢、极力劝我要温文、不要暴戾,我就变成这样了。”她又款款地说:“可是,唉!我矫枉过正,从前那么骄傲狠心,现在又太温柔多情了。我不由自主地爱上了你的小朋友狄艾果。他不来,我的情有增无减。”老头儿道:“那小子相貌又不漂亮,身段又不俊俏,怎么会叫你这样痴心呢?假如你爱上个人才出众的绅士,还情有可原……”梅日丽娜打断了他道:“啊,马果斯,这就见得我和别的女人不同了。还有一说,你要是以为女人爱男人是赏识他们人才,那么你阅历虽多,还没摸透女人的脾气呢。如果我以己度人,我以为女人对男人倾心是不假思考的。爱情是失心疯,支使得我们迷恋着一个人依依不舍,自己做不得主。这是我们害的病,好比畜生发的疯病。所以你不用对我说狄艾果不配我钟情。你看不出他的好,也许他压根儿并不好,可是只要我爱他,自会看得他说不尽的好。你尽管说他相貌身材一无足取,我瞧他模样动人,容光焕发;而且我心醉他的声音柔媚,觉得他弹琴也别具风致。”马果斯道:“可是太太,你也想想狄艾果是个什么样的人么?他出身下贱……”她又接口道:“我并不比他高贵多少,即使我是个贵妇人,也不在乎这点。”
这一席谈话之后,老侍从知道女主人的心劝不转,就随她执迷不悟,不再苦谏;好比飓风把船只吹出了原定的航线,有本领的舵手就顺着风向开驶。他索性让女主人如愿。他跑来找我,把我拉过一边,把上面的话讲给我听,还说:“你瞧,狄艾果,咱们免不了还得在梅日丽娜门前一同奏乐。朋友啊,这位太太非再见你的面不可,要不然,她会干出傻事情来,弄得声名狼藉的。”我也狠不下心,就答应马果斯当天傍晚带了吉他到他家去,叫他把这喜信回报女主人。他当然回报,这位痴情人知道晚上能见我面、听我唱歌,大为高兴。
可是事不凑巧,险的叫她白等。我到天黑才有工夫出门,也是天罚我,外面已经一片昏黑。我一路摸索,大约走到半道,忽然一个窗口里劈头向我倒下一罐儿香汤,那味道实在刺鼻。我淋个正着,竟可说涓滴都归我受用了。我当场打不定主意。回去吧,伙伴瞧见像什么样,我就成了他们的笑柄了;这般淋漓尽致地上梅日丽娜家去吧,又自觉丢脸。可是我决计还是到医生家去。老侍从在门口等我,说奥罗柔索大夫刚睡下,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作乐。我说头一件事得把我衣服擦干净,我就告诉他我那倒霉事儿。他很关心,带我到客堂里见他女主人。这位太太听了这件事,看我那副模样,怜惜得仿佛我遭了什么天大的灾难,又把那个灌溉我的人百般诅咒。马果斯道:“哎,太太,请你平平火气,事出偶然,不必这样痛恨。”她发火道:“人家欺负了这头小羊、这只心无恶意的小鸽子,他受了欺负也没嘀咕一声儿,你为什么不让我痛恨呢?啊!但愿我这会子是个男人,可以替他报仇!”
她说的许多话跟她的举动都见得她情不自禁。马果斯拿一方布替我擦抹,她就跑到房里,拿出个装满各种香料的匣儿。她烧上些香来熏我的衣服,又洒上好些香露。熏香滴露以后,这位心慈肠软的女人亲到厨下拿了为我留的面包、酒和几块烤羊肉。她劝我吃,在旁伺候着,一会儿切肉,一会儿斟酒,乐此不疲,我和马果斯两人极力拦也拦不住。我吃完晚饭,两位合唱的先生就调准嗓子,要和着吉他琴声唱歌。我们奏的一套梅日丽娜很喜欢。其实我们故意唱些辞句助她情兴的歌儿,而且我觉得这玩意儿有趣起来了,唱歌的时候几次三番的瞟她,瞟得她火上加油。弹唱了好一会儿,我一点不厌倦。那位太太觉得一个个钟头快得像一分一秒钟,可是老侍从却觉得一分一秒都长得像一点钟那么久,要不是他只管说时候不早,她恨不能听我们唱个通宵呢。他催促了十遍,她还不理会。不过他绝不放松,直等我出了门才罢休。他持重谨慎,眼看女主人任情胡闹,担心要出乱子。他的确不是过虑。那医生也许怀疑我们捣鬼,也许一向没打开的醋罐子这番倒翻了,忽然讨厌起我们奏乐来,而且还拿出主人身份,禁止这事。他没讲缘故,只声明从此不准闲人上门。
这个声明是为我而发,马果斯赶来通知,我非常懊丧。我已经生了妄想,不愿甘休。不过我既然叙事要像信史,不妨告诉你,我遭了这件不如意的事很平心静气。梅日丽娜就不然,她越发情热了。她对那侍从说:“亲爱的马果斯,我只仰仗你了,求你想个法子让我私下见见狄艾果吧。”那老头儿生气道:“这是什么话?我已经太纵你了。我要是遂了你的痴情,就要装主人的幌子,你名誉扫地,我当用人一向清白无瑕,从此也声名狼藉,我不肯那样的。我宁可走,也不愿意当这种不要脸的差使。”那太太听了这两句话,发慌起来,打断他道:“唉,马果斯,你说要走,直刺我的心。你真是个忍心人!你把我害到这个田地,却想撇下我不顾了么?你把我从前的傲气、狠性子都改掉了,现在还我吧!我要是依然有那些毛病,多福气呀!我到今天还能够心里太平。我都是听了你冒失的劝谏,就此不得安静。你要矫正我的品性,反教坏了我的品性。”又哭道:“我这可怜人胡说些什么呀,干吗平白埋怨你啊?我的老爹,你并没有害我,是我苦命,注定要有这许多烦恼。请别理会我信口胡说八道。唉!我给爱情搅得七颠八倒,请你可怜我不争气,我只靠你宽慰了。你要是以我性命为重,请帮帮忙吧。”
她说着越发热泪夺眶,话都说不下去。她掏出手绢儿掩住脸,倒在椅子里,悲不自胜。马果斯老头儿大概是从古以来做侍从的头等材料,看她这样可怜,不禁恻然心动,竟陪了几点同情之泪,和蔼可亲地说道:“唉,太太,你真叫人拿不定主意!我不忍看你苦恼,把道德也撇开了。我一定帮忙。这一点悯怜之心就害得我失职,无怪爱情摆布得你把本分全忘了。”这侍从虽然品行清白无瑕,这会子却一心要成全梅日丽娜的私情了。一天早上,他把这些事来告诉我,临走说,他胸有成算,可以让我和那太太幽会一次。我又起了痴念,可是两个钟头之后,听到一个坏消息。我们有个主顾是邻近药剂师的伙计,他来修胡子。我正要替他刮脸,他说道:“狄艾果先生,那个老侍从马果斯·德·奥布瑞贡是你朋友,你跟他相与得怎么样?可知道他在奥罗柔索大夫家快要待不住了?”我说不知道。他道:“已经无可挽回,今天就要叫他走了。他东家和我东家刚才谈论这事,我在旁边,他们这样谈的。那大夫说:‘阿本塔多先生,我求你一件事情,我家里那老侍从不行,我想找个诚实严厉而且善于防范的女监护来管我老婆。’我东家打断他道:‘我懂你的意思,你用得着美朗霞大娘。她从前管着我的老婆,我老婆死了六星期,她还在我那儿。我家里少不了她,但是我以你的名誉为重,愿意把她让给你。你有了她,保管头上不添幌子
 。她是女监护里的尖儿顶儿,像条恶龙般看住女人,不许她失节。你知道我老婆算得少年美貌,她在我老婆身边整整十二年之间,家里没见过一个情人的影子。哎,老天,这事可不是玩儿的!我还可以告诉你,我那去世的老婆起初很轻佻,可是美朗霞大娘不久就管得她冷若冰霜,好修女德。总而言之,这女监护是件宝贝,我把她让给你,你将来对我感激不尽呢。’那医生很高兴,两人约定,叫那女监护今天就过去填那老侍从的缺。”
。她是女监护里的尖儿顶儿,像条恶龙般看住女人,不许她失节。你知道我老婆算得少年美貌,她在我老婆身边整整十二年之间,家里没见过一个情人的影子。哎,老天,这事可不是玩儿的!我还可以告诉你,我那去世的老婆起初很轻佻,可是美朗霞大娘不久就管得她冷若冰霜,好修女德。总而言之,这女监护是件宝贝,我把她让给你,你将来对我感激不尽呢。’那医生很高兴,两人约定,叫那女监护今天就过去填那老侍从的缺。”
这个消息千真万确,我听了也知道不假,本来满腔寻欢取乐的心,这会子觉得靠不住了。饭后马果斯告诉我药剂师伙计的话不虚,把我那些心念一扫而空。那位好侍从说:“亲爱的狄艾果,奥罗柔索大夫把我撵走,我很快活,这来省了我不少烦恼。我本来不愿意干那种丑事,而且要让你跟梅日丽娜私会,还得使种种诡计,说种种谎话,多麻烦呀!谢天,这些烦恼操心,还有潜伏的祸害,我都免了。至于你呢,孩子,片刻欢娱会有无穷的后患,还是没有的好,你该这样自譬自慰。”我既然没什么指望,就领了马果斯的教,这玩意儿就此罢休了。老实说,就算我是个一往情深、百折不回的情人,美朗霞大娘也会逼得我放手,何况我不是呢。我听了这位女监护的名气,觉得她能叫一切情人死心。可是随人家说得她多么厉害,两三天以后,我知道医生太太把这千只眼的警卫稳住了,或者买通了。我出去替一个邻居剃胡子,路上一个老婆子叫住我,问我是不是狄艾果·德·拉·夫安特。我说是。她道:“那么我正要找你。你今晚到堂娜梅日丽娜家的门口,你做个暗号,人家就会放你进去。”我说:“好吧,咱们得约定个暗号,我学猫叫活脱儿的像,我做几声猫叫吧。”那拉纤的说:“成,我就替你回报去。狄艾果先生,我听你差遣,愿天保佑你!哎,你多漂亮啊!圣阿妮斯在上,我但愿还是个十五岁的姑娘,我就不为别人来找你了。”那殷勤的老婆子说完走了。
你可以想象,这消息撩得我心烦意乱,马果斯的教训都撇在脑后了。我急焦焦等天黑,算定奥罗柔索大夫已经睡下,就上他家去。我在门外学猫叫,老远都听得见,真没亏负了传授的师父。不一会儿,梅日丽娜亲自悄悄地开门放我进去,忙又关上门。我们进了上次奏乐的客堂,壁炉架上点着一盏昏灯。我们并肩坐下,两人都心里怦怦然,不过她是一心想寻欢作乐的缘故,我却不免有点害怕,这是不同之处。这位太太叫我放心,不用怕她丈夫;可是没用,我只觉得战战栗栗,不能尽兴。我说:“太太,你怎么会逃过那女监护的防范呢,我听得美朗霞大娘的名气,以为你没法再来通消息,更别说幽会了。”堂娜梅日丽娜微微一笑,答道:“你听了我跟那女监护的一段交涉,就觉得咱们俩今晚私会不足为奇了。她一到这儿,我丈夫把她捧得不得了,对我说:‘梅日丽娜,我把你交给这位持重的大娘指导,她简直是一本道德大全,你应该把她当做一面镜子,时刻放在眼前,学她的贤惠。这位可敬可佩的人监护我一个药剂师朋友的太太十二年,她那种监护真是从来没有的,把那太太管得成了个圣人。’
“美朗霞大娘相貌严厉,足见这篇颂赞的话并非虚言,害得我流了不少眼泪,灰心到底。我料想从此一天到晚得听她教训,每日得受她责备。总而言之,我等着做天下最倒霉的女人了。我准备着受苦,索性无所顾忌,等左右没人,就对那女监护很不客气地说道:‘你当然准备好好来收拾我了,可是我得通知你一声,我是受不住气的,我也会千方百计地糟蹋你。我告诉你,我有一段私情,任你劝导也拔不掉我心里的情根,你去斟酌怎么对付吧。你尽管加倍防范,我对你说,我要想尽方法,叫你防不胜防。’我以为这位恶狠狠的女监护听了要来个下马威,把我大大训斥一顿;谁知她展开眉头,含笑说道:‘你这性子真叫我喜欢,你直爽我也直爽。看来咱们俩性情正相投。啊,美丽的梅日丽娜,你要是单凭你丈夫的赞扬,或者凭我仪表严厉来断定我的为人,你就错了。我最不反对寻欢作乐,我所以替醋罐子丈夫当差,正是要替漂亮太太出力。戴假面具的大本领我学会了已经多年;我可算是占了双重便宜,既可以干坏事取乐,又坐享贤德的美名。咱们私下说说吧,世人所谓贤德不过是这么回事。要底子里也贤德实在所费不赀,这年头只要面子上贤德就够了。’
“那女监护又道:‘让我来指点你,咱们在奥罗柔索大夫的脑袋上多装些幌子。你瞧着吧,准叫他的运道跟阿本塔多先生的一样。我觉得医生的脑袋并不比药剂师的脑袋尊贵呀!可怜的阿本塔多!他老婆和我把他作弄得好啊!那位太太真可爱!那好性儿!愿上天赐她安息!我管保她没有辜负了青春。我替她牵引来的情人不知多少,没让她丈夫有半点儿知觉。太太,别对我存着偏见,你放心,你从前那侍从尽管有天大本事,换了我准不吃亏。只怕我比他更有用处哩!’”
梅日丽娜接着说道:“狄艾果,你想,这女监护打开天窗说亮话,叫我多么感激。我还以为她严正呢。真是女人不可以貌相!我听她说了由衷之言,立刻心就向她了。我喜不自胜地拥抱她,这样先让她知道我很喜欢有她做监护。于是我把心事全告诉她,求她设法快让我们幽会一次,她果然做到。今天一早她就派了找你的那老婆儿出马,那是从前帮她替药剂师太太干事的。”她又笑道:“最妙的是,美朗霞听说我丈夫向来睡得很死,这会子就顶替了我在他身边躺着。”我说:“这可不好,太太,我不赞成弄花巧,你丈夫也许会醒过来,发现是冒牌。”她忙道:“他不会发现的,你放了心。一个年轻太太对你一团好意,你跟她相会,该寻欢取乐,别让虚惊败了兴致。”
老医生的太太瞧我听了那话还心虚胆怯,就极力安慰,她千方百计,居然哄得我神思渐定。我只想及时行乐了。可是爱神带着一队欢笑戏耍的跟班正要助成好事,忽然大门打得一片响。爱神和他跟班一撒翅儿都飞掉了,好像胆怯的鸟儿,听得轰然大声,立刻吓得四散。梅日丽娜忙把我藏在客堂的桌子底下,吹灭了灯。她和女监护防有意外,早约定个办法,就按计而行,跑到丈夫卧房门外。这时大门上更打得急了,声震全宅。医生惊醒,就喊美朗霞。女监护忙跳下床,医生还道是老婆,直叫她别起来。她跑到女主人身边。女主人摸索着她,就也喊美朗霞,叫她出去看看谁在打门。女监护应道:“太太,我来了,请上床吧,我去看看怎么回事。”这个当儿,梅日丽娜已经脱掉衣裳,就上床躺在医生旁边;医生一点也没知道受骗。当然,这出戏是在黑地里串的,里面两个女角儿,一个功夫已经登峰造极,那一个也很有资质,准赶得上她。
一会儿,女监护穿件便服,拿支蜡烛,跑来对东家说:“医士大爷,麻烦您起来吧,咱们街坊上那开书铺的斐南代斯·德·比安狄亚中风了,人家请您去瞧他,快去吧。”医生连忙穿上衣服出门。他老婆穿件便服,和女监护同到我那间客堂里。她们从桌子底下拉我出来,我已经吓得七死八活。梅日丽娜道:“没事儿,狄艾果,你放心。”她就把方才的事三言两语讲了。她还想和我断欢重续,可是女监护不赞成。她说:“太太,也许你丈夫跑去一看,书铺掌柜已经死了,立刻就会回来。”她瞧我吓呆了,又说道:“况且这可怜的孩子中什么用呀,他不能跟你欢叙了。还是叫他回去好。”堂娜梅日丽娜一心贪眼前欢乐,嘴里答应,满不情愿。她替医生新制了一顶帽子,没给他戴上,我想她一定很懊丧。
我倒不懊恼没成好事,只私幸免了祸害。我回到主人家,把这事想到天亮。来晚究竟去不去幽会很费踌躇。我只怕第二次去偷情还一般的不顺手。可是魔鬼老在诱惑我们,碰到这类事,竟把我们迷昏了头,所以我想我如果好事半途而废就是大傻瓜了。我着了鬼迷,心目中的梅日丽娜越变得妩媚;等我去领略的乐趣也越见得可贵。我决计到底不懈,发愿这回要有些毅力。我第二晚十一二点钟又到医生家门口。天色很黑,一颗星都不见。我做了两三声猫叫,向里面报信我到了。我因为没人来开门,不愿意老叫一个调儿,就把猫儿各种叫声都学了一遍,那是从前奥尔梅都一个牧童教我的。我叫得真像,有个街坊恰好回家,真以为是一只叫春猫儿,就捡起脚边一块石子,使足劲儿向我掷来,一面骂了声:“这死猫儿!”我头上打个正着,当时头昏眼花,险地仰面摔倒。我自觉受伤不轻。我这一来尝饱了风流的滋味,热情随着热血流掉了。我回到主人家,闹得全家人都起来。我主人瞧了我的伤口,认为很凶险,替我包扎好。可是总算没事,三星期后伤口就平复。这些时候梅日丽娜什么消息也没有。大概美朗霞大娘要她撇下我,另外替她找到了好相识。我满不在乎,因为我伤口一好,立刻离开马德里去周游全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