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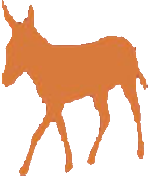 第六章
第六章
我走得很快,常回头看看那个凶狠的比斯盖人是否跟在后面。我只想着他,简直草木皆兵,直在心惊胆战。我走了足足一哩路,心才放下。我想上马德里,就放慢脚步行去。我对瓦拉多利毫无顾恋,只恨跟我那位亲如皮拉得斯
 的法布利斯分手,连告辞都来不及。我不做医生没什么不乐意;倒要求天饶恕我行了那一程子的医。我数着衣袋里的钱很得意,尽管是杀了人赚来的。我恰像妓女弃邪归正,还把卖笑攒下的钱一辈子好好儿藏着。我的钱都是瑞阿尔,约值五个杜加,这就是我的全份家当。我打算靠这几个钱到马德里,到了那儿准会找到好事情。并且我急想看看那座富丽的都会,人家常对我夸说那是天下一切珍奇荟萃之所。
的法布利斯分手,连告辞都来不及。我不做医生没什么不乐意;倒要求天饶恕我行了那一程子的医。我数着衣袋里的钱很得意,尽管是杀了人赚来的。我恰像妓女弃邪归正,还把卖笑攒下的钱一辈子好好儿藏着。我的钱都是瑞阿尔,约值五个杜加,这就是我的全份家当。我打算靠这几个钱到马德里,到了那儿准会找到好事情。并且我急想看看那座富丽的都会,人家常对我夸说那是天下一切珍奇荟萃之所。
我正在记起人家讲马德里的形形色色,想象到了那里怎样快乐,只听得背后有人拉着嗓子唱歌。这人背一只皮口袋,脖子上挂个吉他琴,带着一把长剑。他走得真快,不久就追上来了。他原来就是戒指案里陪我坐牢的两个理发店伙计之一。我们都改了装,可是彼此一见相识,都很诧异会在大道上晤面。他看得出我喜欢和他结个旅伴儿,我也看得出他碰见了我非常快活。我告诉他离开瓦拉多利的原因,他也把他的事讲给我听,说跟东家闹翻,天长地久再不相见了。他说:“我要是愿意待在瓦拉多利,要找理发店的事多的是呢!不是我夸口,全西班牙的理发师,要讲鬈胡子刮脸、顺着毛剃、逆着毛剃,谁也比不上我的手段。可是我离开家乡已经整整十年,急想回去,等不得了。我要去呼吸故乡的空气,瞧瞧我家里人什么情形。他们住的地方叫奥尔梅都,是在塞哥维亚这一边的一个大村子,后天我就可以到家了。”
我决计陪这理发师到家,然后上塞哥维亚找个什么车辆牲口到马德里。我们一路上闲话消遣。这个小伙子兴致很好,也有风趣。我们讲了一个钟头的话,他问我有没有胃口吃东西。我说:“回头下店打尖,你就知道我的胃口了。”他说:“咱们没到客店也可以歇歇,我口袋里带着早饭呢。我出门总记着带些干粮。我不带衣服衬衫和那些没用的衣着,一切不必需的东西我都不要。我口袋里只装些食品,还有几把剃刀和一块胰子头儿。我只用得着这几件。”我称赞他想得周到,很愿意照他的主张先歇一歇。我肚子饿了,想好好吃一顿;听了他刚才的话,指望着吃顿好饭。我们离开大道,觅一片草地坐下。这位理发店伙计把他带的干粮一一搬出来:五六个葱头、几片面包、几片奶饼,还有一件无上妙品——一只皮袋,据他说,里面装着醇醪美酒。那些干粮虽然不怎么可口,我们饿肚子吃来觉得味道不错;我们把皮袋里两品脱左右的酒也分着喝光。那种酒他大可不必卖弄。我们吃喝完毕,兴冲冲起身上路。这理发师听法布利斯说我身经许多奇事,请我亲口讲一遍。我觉得吃了他那么好的一顿饭不便拒绝,就依了他。我讲完了说,我既然随顺了他的意思,他该有来有往,也把身世讲给我听。他说道:“啊,我的身世不值一听,都是些平常经历。不过咱们反正闲着没事,我就据实讲给你听吧。”他所讲大略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