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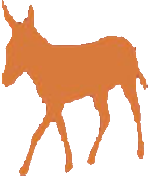 第五章
第五章
我们照法布利斯的计策干完事,从加米尔家出来,都欣欣得意,因为当初只打算捞回一只戒指,没想到这样成功。我们老实不客气把许多别的东西都拿走。我们抢劫了婊子不但于心无愧,反自以为干了件好事。到了街上,法布利斯对大家说道:“诸位,咱们这样马到成功,难道就此分手,不喝杯酒贺贺么?我不赞成,我主张回那酒店去乐个通宵,明天把蜡台、项圈、耳坠子都卖了钱,大家平分,然后分头回家,想个好法子对主人圆谎。”大家都以为公差先生的主意很好。我们都回酒店,有的觉得编个通夜不归的借口并非难事,有的是砸了饭碗压根儿不在乎。
我们叫了一桌好菜,坐下大吃,胃口既好,兴致也高。大家谈得有趣,吃得越有滋味。尤其法布利斯说话逗乐儿,呕得人人发笑。他说了不知多少俏皮话,都有地道的西班牙风味,可以跟雅典式的诙谐
 比美。我们正在欢笑,不料乐极悲生,出了倒霉事。一个相貌还漂亮的人跑到我们吃晚饭的屋里来,跟着两人,长得很凶恶。后面三个三个陆续进来,一数共有十二人。他们都扛着马枪,挂着剑,带着刺刀。我们一望而知这是巡逻的警卫,来意也不难推测。我们起初还想抗捕,不过他们人又多,又有兵器,立刻包围起来,把我们镇住。警卫队长含讥带讽地说道:“诸位,我知道你们方才使个妙计,从女骗子手里要回了一只戒指。你们这事干得实在巧,公家应该奖赏,你们也辞不掉的。法律决不白让你们干这等聪明勾当,所以在宫里安排好了房间等你们去住呢!”挨骂的人都局促不安。方才我们叫加米尔吃的惊慌轮到自己身上,我们吓得变了颜色。法布利斯虽然脸白唇青,慌做一团,却还想替大家辩白,说道:“先生,我们并没有为非作歹的心,玩个小小的把戏也情有可原。”警卫队长冒火道:“什么话!你还说那是个小小的把戏么?可知道那是犯绞刑的勾当?法律不由你们自己执行,而且你们还拿了人家一只蜡台、一串项圈、一对耳坠子;单就你们乔装警卫去打劫这件事来说,分明就是该上绞架的罪。你们这起匪徒乔装正人去干坏事!罚到海船上去做一辈子苦工还是太便宜了。”我们当初还不知道案情这样严重,这会儿听了都跪在他脚边,求他可怜我们年轻不懂事;可是我们恳求也没用处。而且还有绝顶怪事:我们愿把项圈、耳坠子、蜡台交出来,他不接受;连我的戒指都不要,大概因为在场的几个人有些身份,碍着不便。总而言之,他绝不容情。他缴去了我伙伴的兵器,把我们一伙都带进城去坐牢。一个押送我们的警卫在路上告诉我,和加米尔同住的老太婆怀疑我们是冒牌的警察,一路跟到酒店;她疑团打破,就去报告巡逻的警卫,出了口恶气。
比美。我们正在欢笑,不料乐极悲生,出了倒霉事。一个相貌还漂亮的人跑到我们吃晚饭的屋里来,跟着两人,长得很凶恶。后面三个三个陆续进来,一数共有十二人。他们都扛着马枪,挂着剑,带着刺刀。我们一望而知这是巡逻的警卫,来意也不难推测。我们起初还想抗捕,不过他们人又多,又有兵器,立刻包围起来,把我们镇住。警卫队长含讥带讽地说道:“诸位,我知道你们方才使个妙计,从女骗子手里要回了一只戒指。你们这事干得实在巧,公家应该奖赏,你们也辞不掉的。法律决不白让你们干这等聪明勾当,所以在宫里安排好了房间等你们去住呢!”挨骂的人都局促不安。方才我们叫加米尔吃的惊慌轮到自己身上,我们吓得变了颜色。法布利斯虽然脸白唇青,慌做一团,却还想替大家辩白,说道:“先生,我们并没有为非作歹的心,玩个小小的把戏也情有可原。”警卫队长冒火道:“什么话!你还说那是个小小的把戏么?可知道那是犯绞刑的勾当?法律不由你们自己执行,而且你们还拿了人家一只蜡台、一串项圈、一对耳坠子;单就你们乔装警卫去打劫这件事来说,分明就是该上绞架的罪。你们这起匪徒乔装正人去干坏事!罚到海船上去做一辈子苦工还是太便宜了。”我们当初还不知道案情这样严重,这会儿听了都跪在他脚边,求他可怜我们年轻不懂事;可是我们恳求也没用处。而且还有绝顶怪事:我们愿把项圈、耳坠子、蜡台交出来,他不接受;连我的戒指都不要,大概因为在场的几个人有些身份,碍着不便。总而言之,他绝不容情。他缴去了我伙伴的兵器,把我们一伙都带进城去坐牢。一个押送我们的警卫在路上告诉我,和加米尔同住的老太婆怀疑我们是冒牌的警察,一路跟到酒店;她疑团打破,就去报告巡逻的警卫,出了口恶气。
一到牢里,先有人把我们浑身搜查。项圈、耳坠子和蜡台都拿去了,我的钻戒还有菲律宾群岛来的红宝石不巧正在衣袋里,也搜去了;连我那天出诊赚的瑞阿尔也一个没留下。由此可见瓦拉多利的司法官吏办事老练,不亚于阿斯托加的官吏,这些老爷的行为都一模一样的。他们搜掉我金刚钻、红宝石和零钱的时候,警卫队长在旁,把案情讲给搜查的警卫听。他们认为这事闹得不小,好多人以为我们该处死刑。有几个比较宽大,说我们每人该打二百皮鞭,罚到海船上去做几年苦工。我们暂时关在一个牢里,等法官判罪,睡的是干草铺,像马房里的草荐。我们也许要在那里待上好久,等送到海船上去做苦工才能出来;亏得第二天马尼艾尔·奥东内斯大爷听人家说起这件事,他要救法布利斯,就不得不把我们一齐救出来。这人在本城很有声望,又不怕麻烦,四处请托;一半靠他情面,一半靠他朋友的情面,三天以后我们都放出监牢。不过我们出来的时候和进去的时候大不相同,蜡台、项圈、耳坠子、我的钻戒和红宝石都留在里面了。我因此想起维吉尔这样开头的几句诗:“这般辛苦为他人……”

我们放了出来,立刻各回主人家。桑格拉都大夫倒很和气,对我说道:“可怜的吉尔·布拉斯,我今天早上才知道你犯了事,正预备出力替你去求情。朋友,别把这事放在心上,从此应该越加专心学医。”我说正是这般打算,我果然把全副精神都花在这上面。这时候我们够忙的。我主人的话说准了,病人多得很。天花和恶性寒热病在城乡流行。瓦拉多利的一切医生都有生意,我们尤其生意好。我们每人一天总要有八个到十个病人,喝进去的热水和抽出来的血该有多少,可想而知。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病人没一个活的,也许我们的治法只会送命,也许他们害的都是不治之症。我们瞧一个病人难得满三次的;两次之后,或者病家通知,病人已经埋了,或者跑去看病的时候,病人正在咽气。我才是个初学,还没有杀惯人,病人死了我就担心,怕人家会怪我。有一晚,我对桑格拉都大夫说:“先生,我对天发誓,我完全照您的办法医病,可是我的病人全到阴间去了,仿佛是要推翻咱们的医道,故意死的。我今天就有两个病人抬出去埋了。”他答道:“孩子,我也跟你情形差不多,落在我手里的病人难得一个治好的。要不是我深信自己的道理,就要以为这治法跟我瞧的病症全不合适了。”我道:“您要是肯听我的话,先生,咱们换个办法吧。咱们试个新鲜法子,配些化学药品给病人吃,用点儿锑朱砂试试,大不了也不过像喝热水抽血一样的效果。”他答道:“要是这种试验无关紧要,我很愿意尝试,可是我刚出版了一本书,宣扬抽血和喝水的功效,你要我自打嘴巴么?”我道:“啊,你说得对,咱们不能让冤家得意,他们回头说你痛悔前非,你就名誉扫地了。随那些平民呀、贵族呀、教士呀,一个个送命,咱们还是照老样子干。好在咱们同行虽然恨抽血,手段也并不高明,我相信他们配的药跟咱们的验方正是不相上下。”
我们加劲干去,不到六星期,造成的寡妇孤儿和特洛亚被围的时候一样多。
 处处都在办丧事,仿佛瓦拉多利遭了瘟疫了。每天总有个把做父亲的因为儿子给我们送掉,就上门来算账;或者叔父伯父跑来责问怎么侄儿死在我们手里了。至于那些做儿子侄儿的,父亲叔伯给我们医死,从没来追究过。做丈夫的也一样谨慎,绝不怪我们害掉老婆。我们的确不能逃罪,不过死者的家属有时悲痛得厉害,骂我们是庸医,是杀人犯,什么话都骂出来。我听了很难受,可是我主人挨惯了骂,声色不动。我也许会像他一样,听惯了满不在乎,可是天要替瓦拉多利的病人除掉一害,特意生出件事来。我行医本来没什么成绩,此后一发憎厌了。我不怕读者嗤笑,要把那事详细讲讲。
处处都在办丧事,仿佛瓦拉多利遭了瘟疫了。每天总有个把做父亲的因为儿子给我们送掉,就上门来算账;或者叔父伯父跑来责问怎么侄儿死在我们手里了。至于那些做儿子侄儿的,父亲叔伯给我们医死,从没来追究过。做丈夫的也一样谨慎,绝不怪我们害掉老婆。我们的确不能逃罪,不过死者的家属有时悲痛得厉害,骂我们是庸医,是杀人犯,什么话都骂出来。我听了很难受,可是我主人挨惯了骂,声色不动。我也许会像他一样,听惯了满不在乎,可是天要替瓦拉多利的病人除掉一害,特意生出件事来。我行医本来没什么成绩,此后一发憎厌了。我不怕读者嗤笑,要把那事详细讲讲。
我们附近有个赌场,城里游手好闲的人每天聚在那儿。赌场上常有些打手称雄称霸,有什么争吵由他们裁断。这里有个打手是比斯盖人,自称堂罗德利克·德·蒙德拉贡。他约摸三十来岁,中等身材,瘦削有劲;脸上一双炯炯有光的小眼睛骨碌碌转动,眼光射到谁身上,谁就凛凛然;一个塌鼻子,底下两撇红胡子,胡子的尖角儿翘耸耸直勾到鬓边。他说话蛮横粗暴,开口就叫人害怕。这个骄横的家伙是赌场一霸,赌场上有什么争端,凭他一言断定,谁敢道个不字,就得准备他明天来下决斗的挑战书。堂罗德利克大爷是这样的人。而且他尽管冒了“堂”的尊称,盖不了他的下贱出身。可是赌场老板娘对他却钟情得很。这女人四十岁,手里有钱,相貌过得去,丈夫刚死了十五个月。我不懂她怎么会看中那男人的,决非赏识他的相貌,准有什么妙处难言。这些都不去管它,她反正是爱这个人,打定主意要嫁他。她正忙着准备婚事,忽然病了;该是她晦气,请了我去瞧病。即使她害的不是恶性热病,经我着手就转成险症。四天之后我害得赌场里的人都戴了孝。我把老板娘送到了我打发一切病人的去处,她亲属得了她的财产。堂罗德利克失掉了情人,其实是这门大有好处的亲事落了空,失望极了,不但恨得我无名火直冒,还发誓要一剑把我戳个透明窟窿,几时瞧见我,立刻结果了我。有个邻居心肠慈悲,把这话告诉了我。我向来知道蒙德拉贡的为人,哪里敢置之不理,直吓作一团。我不敢出门,怕碰到这位魔头;又老想象他怒冲冲冲进寓所来,惶恐得坐立不安。我因此无心学医,只求别担惊受恐。我又穿上自己的绣花衣裳,向主人告辞,他也留不住我了。我清早出城,一路上只怕碰到了堂罗德利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