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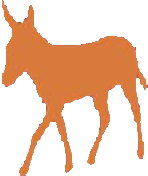 第四章
第四章
我刚到寓所,桑格拉都大夫也回来了。我告诉他看了些什么病人,把十二个瑞阿尔诊金花剩的八个交出来。他数一数,说道:“出诊两处只有八个瑞阿尔,太少了;可是不论多少,都得收下。”所以他差不多照数全收。他拿去六个,给我两个,说道:“拿去吧,吉尔·布拉斯,让你攒起家当来。我跟你还要订个约,很便宜你:你赚来的钱,四分之一归你。朋友,你就要发财了,因为靠天照应,今年害病的人也许很多。”
把诊金这样分法我该称心,因为我蓄意先打四分之一的偏手,再加上余款四分之一,那么,除非算术这门学问靠不大住,我就几乎一半到手了。因此我对医学越发热心。第二天,我吃完饭就换上替身医生的行头,出去看病。我看了好几家由我挂号的病人,虽然病情不同,我一概用同样的方子。到此为止,还没有闹出什么乱子来。谢天照应,没人反对过我的方子。不过医生的手段尽管高明,总不免挨骂招忌。我到一个杂货店主家去看他儿子的水肿病,碰见一位同道,他是个黑不溜秋的矮个子,人家管他叫居希罗大夫。他由店主人的亲戚介绍来的。我对每个人都深深行礼,我知道这位医生是东家请来会诊的,对他尤其恭敬。他正经严肃,还了个礼,把我仔细端详一番,说道:“医士大爷,请别怪我好奇,我相信瓦拉多利行医的同行我都认识,可是没见过你的脸。你准是新搬来的。”我说我还是个后生新进,掮了桑格拉都大夫的牌子替人家看看病。他很客气道:“我恭喜你传了这位大人物的妙法。你看来很年轻,可是我相信你一定很有手段了。”他说来态度自然,我不知道他是认真还是打趣。我正在想怎么回答,杂货店主乘这个当儿说道:“两位先生,我相信两位医道都很高明,请你们瞧瞧我儿子,诊断一下他的病该怎么治法。”
那小矮子医生就去瞧病人;把病征一一指给我看,然后请教我该怎么医治。我道:“我以为应当天天抽血,多多喝热水。”小矮子医生听了微笑,笑意很不善,说道:“你以为这样就救得他命么?”我口气坚决,说道:“那还用说!你可以眼看病人有起色,这是必然之事,因为我这方法是医治百病的良方,不信你去问桑格拉都大夫。”他道:“如此说来,赛尔斯完全错了,他以为治水肿最简捷的办法是叫病人又饿又渴。”我道:“啊,我并不信奉赛尔斯,他跟旁人一样,也会有失着。我有时候直欣幸没听他的话,违背了他并不错。”居希罗道:“一听你的高论,就知道是桑格拉都大夫传授门徒的验方妙法。抽血和喝水是他的万应良方。怪不得那么许多好人在他手里送了命……”我疾言厉色打断他道:“别破口骂人啊!真是的,吃你们这行饭的人,好意思骂出这种话来么?罢了,罢了,医士先生,人家不抽病人的血,不叫他喝热水,送掉的性命多着呢!说不定你手里断送的就比人家还多。你跟桑格拉都先生有仇,不妨写文章攻击他,他可以反驳你;咱们看看到头来究竟谁闹笑话。”他也怒冲冲打断我道:“圣雅各在上!圣德尼在上!你还没认得我居希罗大夫呢!可知道我自有随身本领,不怕什么桑格拉都。他尽管自以为了不得,我看来不过是个怪物罢了。”他那副嘴脸惹起我的火来。我尖嘴薄舌回驳了两句,他也如法还敬,两人马上扭打起来。杂货店主和他亲戚忙上来劝开,我们俩已经彼此互挨了几拳,各拉掉一把头发。他们觉得我那敌手高明得多,就把他留下,付了我诊金打发我走。
一波乍平,差点儿一波又起。一个唱圣诗的胖子发烧,请我去看。他一听说要喝热水,就狠命拒绝这种灵药,竟破口咒骂。他把我臭骂一顿,还恫吓说,如果不快快滚蛋,就把我从窗子里扔出去。我不用他说第二遍,赶快逃走。这一天我没兴致再看病,就到约会法布利斯的酒店里去。他已经在那儿。两人当时都有酒兴,尽情大喝了一顿,各回主人家的时候都有点醺醺然,换句话说,都已经半醉了。桑格拉都大夫一点没看出我醉,我指手画脚讲我跟小矮子医生吵架的事,他只以为我打架之后,余怒未消,所以那么激愤。而且我讲的事,牵涉他自己。他对居希罗很生气,说道:“吉尔·布拉斯,你替咱们的方法争光,跟那三寸丁医生挺一挺是不错的。他以为害了水肿病不该喝水么?真是个愚昧无知的小子!我呀,我说一定得给他水喝。”接着道:“哎,这水啊,治得各种水肿,也治得骨节风痛以及脸色灰白,又是疟疾的对症良药;此外身体里津液太寒、太稀、太滞、痰太多,种种病症,都是喝水最灵。居希罗这种小伙子听了我的主张觉得希奇,其实这在医学上有根有据;要是这起人别一味跟我抬杠,能够按照论理学推理一番,准会对我这方法钦佩,心悦诚服的归依我。”
我要把他对矮子医生的火气扇得旺些,不免在报告他的那篇话里加油加酱;他怒极了,一点也没怀疑我喝酒。可是他虽然一心只想着那篇话,也看出我这晚上喝的水比往常多。
我喝了酒实在口渴得很。换了别人,看我那样渴,大口的直喝水,一定会起疑心。可是他认真以为我喝水喝出滋味来了,笑笑说道:“吉尔·布拉斯,照我看来,你不像从前那样厌恶白水了。天啊,你喝来仿佛琼浆玉液似的。朋友,我并不奇怪,我很知道喝喝会惯。”我答道:“先生,一切东西都有个当景的时候。我这会子宁可把一大桶酒换两杯白水来喝。”医生听了很高兴,不肯坐失良机,又把水的妙处赞扬一番。他这次换了个调儿,简直似疯似狂,不是平心静气的口吻了。他说:“古时候的热水站,品又高,又没害处,比起现在的酒店来,好得千万倍呢!那时候大家上热水站去,一起喝热水消遣,不失体面,又没害处;并非灌了一肚子酒,费钱伤身,丧尽廉耻。古代执政的人真有先见之明,叫人钦佩不已。他们造了这种公共场所,谁都可以来喝水;酒只许药房里卖,不凭医生的药方就买不到。这办法多聪明呀!”又道:“上古风气俭朴,不愧称为黄金时代。幸而余风犹在,所以还有你我这种人,只喝白水,相信喝了没煮开的热水能身健病除,因为我留心到开水性子太重,喝到胃里不大合适。”
他滔滔议论,我好几次险的要笑。可是我装出一脸正经,还随声附和。我说喝酒是个恶习,那些人不幸喝上了这种毒汁,真是可怜。我觉得酒渴还没解尽,又满满斟上一大杯白水,一口气灌下肚去。我对主人道:“好哇,先生,咱们且喝这健身汤!您既然对古代的热水站这样思慕,就在您府上复兴起来吧!”他大为赞成,还花了整一个钟头劝我一辈子只喝白水。我要喝惯这种饮料,就答应他每天晚上一定大喝;我这句话说到要做到,所以临睡下个决心,以后要天天去光顾酒店。
我在杂货店主家碰到了那场麻烦若无其事,依然行我的医,第二天又照常处方,吩咐病人抽血喝热水。我刚瞧了一个神志昏迷的诗人出来,碰到个老太婆,问我是不是医生。我说是的。她道:“那么,医士大爷,恕我冒昧,奉请您到我家去,我侄女儿昨天病了,不知是什么征候。”我就跟她家去。她领我到一间精致的屋里,床上躺着个人。我近前去看,第一眼觉得脸熟,细细一认,分明就是扮演加米尔很出色的女骗子。她似乎不认得我,也许因为病里昏迷,也许因为我穿了医生服装,认不出来。我替她把脉,看见她手上正戴着我的戒指。我见了分内应得的东西,大为激动,恨不能一把抢到手;可是我提防这两个女人一叫喊,堂拉斐尔或其他替女人当保镖的听见了会赶来,就极力捺住性子。我想还是不露声色,先和法布利斯商量商量。我决计这么办。老太婆钉着问侄女儿害的什么病。我不是傻瓜,哪里肯说不知道,就假充内行,学着我主人的腔调,一本正经说:病人不出汗,这是病根,应当赶紧抽血,因为抽血替代出汗是自然之理;我又照规矩吩咐喝热水。
我赶紧瞧完病,跑去找尼聂斯理发师的儿子,正碰见他出门替主人办事。我讲了这件新闻,问他应该不应该报告警察,把加米尔抓起来。他说:“哎,不行!天爷爷,你千万别去报告,一报告,你的戒指就拿不回来了。那些人不喜欢物归原主。你该记得那阿斯托加的监狱,你的马、你的钱以及你的衣裳,可不是都落在他们手里么?咱们还是自己费点儿心把你那钻戒捞回来。这条计策归我来想。我现在奉主人的命要到慈惠院去吩咐采办粮食的人几句话,一路上就替你打起算盘来。你先到咱们那酒店去等着,别性急,我一会儿就来。”
我在约会的地方等了三个多钟头他才到。一上来我不认得他了。他换了衣裳,编扎起头发,还带上一部大胡子,遮掉半个脸。他带一把长剑,剑柄的护手,圆周至少有三尺。背后一队五人,都像他一样,雄赳赳的,一脸大胡子,带着长剑。他走来说道:“吉尔·布拉斯先生,我替你当差。我是个新牌公差,跟我的这几位壮士都是和我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卫士。你只要带我们到骗你钻戒的女人家里去,我管保叫她还你。”我听了把法布利斯拥抱一番。他告诉我设了怎么个计策,我十分赞成。我又招呼了这队假卫士,里面三个是当用人的,两个是理发店的伙计,都是法布利斯请来帮忙的朋友。我请这队人喝酒,等到傍晚,就一起上加米尔家去。她家大门已经关了,我们就上去打门。那老太婆开门,吃一大惊,以为我带来的这伙人真是法院的警犬,上门必有缘故。法布利斯对她说道:“我的老妈妈,你放心,我们只有一点小事情,立刻就了的。我们这起人办事爽利极了。”于是老太婆领路,拿一只点着蜡烛的银蜡台,照我们到病人屋里。我接过蜡烛,走向床前,让加米尔看看清我的嘴脸,一面说道:“骗子!认认死心眼儿上你当的吉尔·布拉斯!啊,混蛋!我找了你好久,也有给我找着的一天!司法官已经准我告状,派这几位公差来逮捕你。”又对法布利斯道:“来啊!公差先生,办你的公事吧。”他提高了嗓子说道:“不用你说,我自会办我的公事。我认得这位花姑娘,十年前就用红笔把她的名字记在我本子上了。”接着道:“起床呀,我的公主娘娘!快穿上衣服!你要是不嫌,我就充你的侍从,伺候你到本城牢里去。”
加米尔听了这话,又看见两个大胡子的卫士准备硬拉她下床,虽然病得有气无力,只得硬撑着坐起来,合掌哀求,满眼畏惧地望着我道:“吉尔·布拉斯先生,可怜可怜我,看你大贤大德的妈妈面上,可怜我吧。我不是坏人,实在是没法儿。你要是肯听我讲讲身世,就会相信。”我嚷道:“不用讲,加米尔姑娘,我不要听。我还不知道你惯会编故事么?”她道:“唉,罢了!你既然不让我辩白,我且把钻戒还了你,别送我死路上去。”一面说,一面脱下戒指给我。可是我说,单还我一个钻戒算得什么,还有公寓里拐去的一千杜加呢。她道:“啊,先生,你的杜加可别问我要。堂拉斐尔那骗子当夜就拿走了,我到今天还没看见他的影儿。”法布利斯道:“唷!我的小乖乖,你只要说一声没有分肥,就撇清了么?哼!没那么便宜的!你既是堂拉斐尔同党,我们就该查究你的旧账。你干下的昧心事一定不少,请到牢里去整个儿忏悔一通吧。”又道:“这位老太太我也带了走,我想她知道的奇怪事情一定不知多少,法官准爱听。”
两个女人听了这话,忙使出通身本领向我们求情。屋里一片诉苦乞怜之声。那老太婆一会儿向公差下跪,一会儿向那些卫士下跪,想叫他们大发慈悲;加米尔也做出宛转动人的样子求我援手,别让法院抓她去。这时候的情景煞是好看。我假装心软了,对尼聂斯理发师的儿子道:“公差先生,我得了钻戒,别的也就算了。我并不要这个可怜女人受罪,并不要这个犯人送命。”他道:“咄!你心肠好得很!你可不配做公差。”接着又道:“我得尽我的责任。上面明令叫我来逮这两位公主娘娘,法官正要借她们做个榜样给人看看。”我说:“哎,看我面子,请你们开恩吧;况且两位太太还有东西谢你,看这个分上,执法不要太严。”他道:“唷!这就又当别论了!你这话可算措辞得体!好,咱们瞧吧,她们有什么东西送我啊?”加米尔道:“我有一串珍珠项圈,还有一对很值钱的耳坠子。”法布利斯凶狠狠地插口道:“好哇!要是菲律宾群岛来的货
 我可不要。”她道:“你放心拿去,我担保东西是真的。”她一面叫老太婆拿来一只小盒儿,取出一串项圈和一对耳坠子,交给公差。他和我一样不识宝石,可是他相信耳坠子上镶的宝石和那串珠子都是真的。他细细看了一回,说道:“这些珠宝看来货色不错。你再给饶上吉尔·布拉斯先生手里拿的银蜡台,我就顾不得奉公守法了。”我对加米尔说:“这番调停是便宜你的,我想你不至于为那一点小东西又弄到翻脸。”一面说,就拔下蜡烛,交给老太婆,把银蜡台递给法布利斯。他大概看屋里再没什么可拿的东西,也就满意了,对那两个女人道:“再见吧,两位太太,一切放心,我回头见了司法官,一定替你们洗刷得比雪还清白。是非曲直由得我们说,我们对他不必撒谎的时候才肯据实报告呢。”
我可不要。”她道:“你放心拿去,我担保东西是真的。”她一面叫老太婆拿来一只小盒儿,取出一串项圈和一对耳坠子,交给公差。他和我一样不识宝石,可是他相信耳坠子上镶的宝石和那串珠子都是真的。他细细看了一回,说道:“这些珠宝看来货色不错。你再给饶上吉尔·布拉斯先生手里拿的银蜡台,我就顾不得奉公守法了。”我对加米尔说:“这番调停是便宜你的,我想你不至于为那一点小东西又弄到翻脸。”一面说,就拔下蜡烛,交给老太婆,把银蜡台递给法布利斯。他大概看屋里再没什么可拿的东西,也就满意了,对那两个女人道:“再见吧,两位太太,一切放心,我回头见了司法官,一定替你们洗刷得比雪还清白。是非曲直由得我们说,我们对他不必撒谎的时候才肯据实报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