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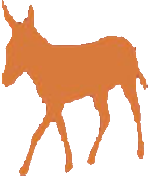 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
我尽情怨了一回命,也没用处,我想还是不要一味懊恼,该挺起脊梁,不怕坏运。我就鼓起勇气,一面穿衣裳,一面自慰道:“还算大幸,那些坏蛋没把我的衣裳和衣袋里几个杜加一股脑儿拿走。”我多承他们这等体谅。而且他们还很大量,留下了我的皮靴;我就按原价三分之一卖给房东。感谢上帝,我跑出公寓,不用谁来扛我的行李了。我先跑到那客店里去瞧骡子在不在,料想安布华斯不会放过它们。我若一上来就看出他的为人,岂不好呢?店家说,安布华斯昨晚就把骡子牵走。我料定我的骡子跟那宝贝皮包都一去不返了。我在街上惘惘独行,想个计较。我很想回布果斯,再求堂娜曼茜亚帮忙,可是觉得不该诛求无厌,而且也不愿显得我是个糊涂虫,因此又死了这条心。我发誓从此要提防女人;那时就是对贞洁的苏珊娜
 也不敢信任。我不时看看手上的戒指,想到这是加米尔的礼物,又伤心叹息。我想:“唉!我对红宝石全不识货,可是我认得贩卖宝石的人,我相信这次准做了傻瓜,不必去请教珠宝商人了。”
也不敢信任。我不时看看手上的戒指,想到这是加米尔的礼物,又伤心叹息。我想:“唉!我对红宝石全不识货,可是我认得贩卖宝石的人,我相信这次准做了傻瓜,不必去请教珠宝商人了。”
我还想知道那戒指究竟值多少,就去给一个宝石匠看,他说值三个杜加。我虽然料到那东西不会值钱,不禁把那菲律宾总督的侄女狠狠咒骂,其实我已咒骂得她够了。我从宝石匠那里出来,一个年轻人打身边过,站住仔细看我。我觉得他很面熟,只是一时记不起是谁。那人道:“怎么的,吉尔·布拉斯,你假装不认识我么?两年不见,尼聂斯理发师的儿子竟变得认不得了么?你还记得你同乡同学法布利斯么?咱们俩在郭狄内斯博士家里,把共相和物性层次
 等等问题辩论过多少多少回啊!”
等等问题辩论过多少多少回啊!”
我不等他说完就记起来了。我们俩亲热拥抱一番。他说:“哎,朋友,我碰到了你真是快活!说不出心上多乐!”又诧异道:“你多神气啊!老天爷!你打扮得像一个王爷!好一把宝剑!丝袜子!丝绒的袄儿和斗篷!上面还绣着银花儿
 !嗳呀呀!一望而知你有了什么艳遇了!我可以打赌,准有个花钱不心疼的老太太在倒贴你。”我道:“没那事儿。你想我那么阔气,其实并不然。”他道:“去你的吧!去你的吧!你装正经呢!请问你,吉尔·布拉斯先生,你手上戴的大红宝石哪儿来的呀?”我答道:“那是个地道的女拆白给我的。法布利斯,亲爱的法布利斯啊,别以为我风魔了瓦拉多利的女人。我告诉你吧,朋友啊,我是受她们捉弄的冤桶!”
!嗳呀呀!一望而知你有了什么艳遇了!我可以打赌,准有个花钱不心疼的老太太在倒贴你。”我道:“没那事儿。你想我那么阔气,其实并不然。”他道:“去你的吧!去你的吧!你装正经呢!请问你,吉尔·布拉斯先生,你手上戴的大红宝石哪儿来的呀?”我答道:“那是个地道的女拆白给我的。法布利斯,亲爱的法布利斯啊,别以为我风魔了瓦拉多利的女人。我告诉你吧,朋友啊,我是受她们捉弄的冤桶!”
我说这话时形容沮丧,法布利斯一看就知道我做了瘟生了。他追问我为什么对女人如此怨恨。我很愿意告诉他听,只是说来话长,我们也舍不得马上分手,就上一家酒店,讲话方便些。我一面吃早点,一面把我离开奥维多以来的事一一讲给他听。他觉得我的遭遇很离奇,又十分关切我目前的窘况,说道:“朋友,碰到人生一切不如意的事,应该自己会譬解,品性坚强的人跟懦夫就是这点不同。聪明人落了难,就捺下心等时来运转。西塞罗说得好:千万别丧气,忘掉自己是一个人
 。我就是那种性格,尽管失意,绝不颓丧,永远不给坏运气压倒。譬如说吧,我爱上奥维多一个大家闺秀,她也爱我,我去向她爸爸求婚,碰了个钉子。换了别人就气坏了,可是我啊,你该佩服我的气魄,我拐了那小娘儿跑了!她那人热辣辣的,又没脑子,又风骚,只要可以寻欢作乐,就把本分事儿撇在脑后。我带她在加利西亚各处闲逛了六个月,她尝到了游历的滋味,想到葡萄牙去,不过她这回找到了别人做她的旅伴儿了。这又可以叫我垂头丧气。但是我吃了这个新的亏,并不认输。我比墨涅拉俄斯乖得多,帕里斯拐掉了我那海伦,我非但不向他宣战,反而感激他替我顶了缸。此后我怕吃官司,不愿意回阿斯杜利亚,就到雷翁去。当初我带那公主娘娘离开奥维多的时候,两人各卷了一大笔钱,行头也都不坏,所以我身边还有余钱,一路使用;可是一会儿就花光了。我到巴伦西亚,身上只有一个杜加,还得买一双鞋,剩下的钱更难维持我多少时候。我光景很窘,已经得收紧腰带,不得不赶快想办法。我决计去当用人。我先帮一家,主人是个卖呢绒的胖子,有个儿子很荒唐。我在他家不愁挨饿,却有一件事为难。老子吩咐我去监视儿子,儿子又请求我帮他欺哄老子,我没法两面兼顾。我是吃人家软求不爱听人家命令的,因此把个饭碗砸了。接着我帮了一个老画家,承他好意,情愿教我画画。可是他只教我画,随我去饿死也不管。我因此讨厌绘画,也厌恶巴伦西亚那地方。我就到瓦拉多利,恰是天大的运气,在慈惠院院长家里找得个事。我现在还在他家,很喜欢这只饭碗儿。我主人马尼艾尔·奥东内斯先生走路时眼睛老看着地下,手里拿一大串念珠,可见他非常虔事上帝,很有道德。据说他自从少年时候,张开眼只看见穷人的福利,所以专为穷人造福,孜孜不倦。他得了好报,事事顺利。老天爷多么保佑他啊,他替穷人效劳,自己变成富翁了。”
。我就是那种性格,尽管失意,绝不颓丧,永远不给坏运气压倒。譬如说吧,我爱上奥维多一个大家闺秀,她也爱我,我去向她爸爸求婚,碰了个钉子。换了别人就气坏了,可是我啊,你该佩服我的气魄,我拐了那小娘儿跑了!她那人热辣辣的,又没脑子,又风骚,只要可以寻欢作乐,就把本分事儿撇在脑后。我带她在加利西亚各处闲逛了六个月,她尝到了游历的滋味,想到葡萄牙去,不过她这回找到了别人做她的旅伴儿了。这又可以叫我垂头丧气。但是我吃了这个新的亏,并不认输。我比墨涅拉俄斯乖得多,帕里斯拐掉了我那海伦,我非但不向他宣战,反而感激他替我顶了缸。此后我怕吃官司,不愿意回阿斯杜利亚,就到雷翁去。当初我带那公主娘娘离开奥维多的时候,两人各卷了一大笔钱,行头也都不坏,所以我身边还有余钱,一路使用;可是一会儿就花光了。我到巴伦西亚,身上只有一个杜加,还得买一双鞋,剩下的钱更难维持我多少时候。我光景很窘,已经得收紧腰带,不得不赶快想办法。我决计去当用人。我先帮一家,主人是个卖呢绒的胖子,有个儿子很荒唐。我在他家不愁挨饿,却有一件事为难。老子吩咐我去监视儿子,儿子又请求我帮他欺哄老子,我没法两面兼顾。我是吃人家软求不爱听人家命令的,因此把个饭碗砸了。接着我帮了一个老画家,承他好意,情愿教我画画。可是他只教我画,随我去饿死也不管。我因此讨厌绘画,也厌恶巴伦西亚那地方。我就到瓦拉多利,恰是天大的运气,在慈惠院院长家里找得个事。我现在还在他家,很喜欢这只饭碗儿。我主人马尼艾尔·奥东内斯先生走路时眼睛老看着地下,手里拿一大串念珠,可见他非常虔事上帝,很有道德。据说他自从少年时候,张开眼只看见穷人的福利,所以专为穷人造福,孜孜不倦。他得了好报,事事顺利。老天爷多么保佑他啊,他替穷人效劳,自己变成富翁了。”
法布利斯讲完,我就说道:“你对处境满意,我也很高兴。不过咱们私下说说,你还可以做个比用人有体面的事,像你这样人才,可以再向高枝儿上飞呢。”他答道:“你是说着玩儿吧,吉尔·布拉斯?我告诉你,像我的脾气,做这事再合适没有。当然,傻瓜做用人是很辛苦的;不过伶俐小伙子当用人就其乐无穷。高才上智当了用人,不像下愚那样死心眼儿做事。他上人家不是去伺候,倒是去指挥的。他第一先揣摩主人性格,顺着他的短处,哄得主人信任,以后主人就由他牵着鼻子走了。我在慈惠院院长家就是这个做法。我一上来就看透了那家伙,看出他要冒充圣贤人的;我只装给他蒙过了,这又不费什么事。不但如此,我还学他的样,他怎么装腔哄人,我就照样装腔哄他。这骗子受了我的骗,渐渐无论什么事都交给我了。我指望靠他提拔,有一天也能够办慈善事业。我觉得我跟他一样地爱为穷人造福,说不定我也会发财呢。”
我说道:“亲爱的法布利斯,你大有前途,恭喜恭喜。我呢,还想照我原先的计划办。我把这套绣花衣服换件道袍,到萨拉曼卡,借个大学的招牌去谋个教师的馆地。”法布利斯嚷道:“好计划!好打算!你真是个傻瓜!这点点年纪就去做教书匠!可怜东西,你打这个主意,可知道前途是什么光景?你一谋到馆地,那家的人就个个都来监视你,仔仔细细审查你一举一动。你对自己要刻刻严加约束,装出岸然道貌,仿佛是众德兼备的样子。你简直没时候寻快乐。你老得监督着你的学生,成天教他拉丁文,纠正他的胡说乱为,这就够你忙的了。费了这些心力,受了这般拘束,有什么收成呢?那位小爷要是个不成材的东西,人家怪你管教不好,东家不送谢仪,就请你滚蛋,说不定连束脩都会赖掉。所以你别跟我提教师的馆地,吃那一份薪俸,得掌管人家的灵魂。咱们还是谈谈做用人这门行业吧,这才是只领干薪、不担责任的。主人有什么短处,聪明用人就依顺着他,往往还可以从中取利。一个用人在有钱人家过的是无忧无虑的日子。他酒醉饭饱,就放倒头安心睡觉,跟阔人家公子哥儿一模一样,不用操心肉铺子面包店的账。”
他接着道:“朋友,我要是把当用人的好处一一说来,就一辈子也说不完。听我的话,吉尔·布拉斯,从此放下了做教师的心,还是学我的样。”我答道:“好是好,法布利斯,不过像慈惠院院长那类的东家不是随时找得到的;我要是决计做用人,至少得找个好饭碗儿。”他道:“哎,你说得对。这事在我身上!不说别的,单为了把你这个漂亮人从大学里挖出来,我也得包你个好事情。”
我倒不是为法布利斯这番道理,我实在是快要穷极无路,又看他得意洋洋,就决计当用人了。我们出了酒店,我那同乡说:“我立刻带你去见个人,找事情的用人多半找他;他手下有人替他刺探各家消息。这人知道谁家要用人,一部账上登载得详详细细,不但哪几家要人,连某家有什么好处坏处都写得分明。他从前在不知什么个修道院里做过修士。一句话,我现在的事就是他找的。”
我们一面谈着这个奇妙的问讯处,尼聂斯理发师的儿子带我进了一条死胡同。我们到一所小房子里,看见一个五十来岁的人,伏在桌上写字。我们向他招呼,而且礼貌,很恭敬,他却站都不站起来,只略微点了点头,不知是天生傲兀,还是平日只看见用人和车夫之类,大落落的惯了。可是他对我很注目。我知道他在诧异,怎么穿绣花丝绒衣服的人要来当用人,也许想是来托他找用人的。可是他立刻知道了我的来意,因为法布利斯劈头就说:“阿利阿斯·德·隆东那先生,你许我介绍我的好朋友么?他是大家子弟,走了背运,没法儿只好出来当用人。劳驾你给找个好事情,他明儿一定重重谢你。”阿利阿斯冷冷地答道:“先生,你们这起人都是一个样子的:事情没到手,许的愿天花乱坠;得了好事情,说的话忘个一干二净。”法布利斯道:“怎么呀?你还嘀咕我么?我对你还不够大方么?”阿利阿斯道:“你还可以大方些儿呢!你那个事抵得过书记的职位;可是你给的报酬,好像我只介绍了你到文人家去帮佣。”我就自己出场,对阿利阿斯先生说,我愿意先给报酬,好叫他知道我不是个没良心的。我一面说,就掏出两个杜加给他,又答应他如果有好饭碗,还要多多酬谢。
我这种举动仿佛很合他意。他说:“我喜欢人家这样待我。”又道:“有许多很好的位置还空着呢,我一一念给你听,随你挑好了。”他就戴上眼镜儿,打开桌上的登记簿,翻过几页,念道:“多贝利诺大尉要一个跟班。大尉性情急躁暴戾,而且古怪;把用人责备不休,还要打骂,往往打成残废。”我一听他的描写,嚷道:“念下去吧,这个大尉不合我的脾胃。”我这股子劲儿惹得阿利阿斯笑了,他往下念道:“堂娜马尼艾拉·德·桑都华尔现在缺一个跟班。她是个老寡妇,又啰嗦,又怪僻;一向只用一个人,从来用不满一整天的。她家里十年来只有一套号衣,不论身材肥瘦高矮都穿这一套。其实用人不过去试试装,那套号衣虽然有两千人上过身,还是簇新的。阿尔华·法内斯博士要一名亲随。他是医生兼配药的,他家用人吃得好,管待得不错,工钱也高,只是他制了药要在用人身上试验。他家老在找用人。”
法布利斯笑着插嘴道:“唷!那是当然的!天晓得,你尽介绍我们这些好主顾!”阿利阿斯·德·隆东那道:“别急呀,咱们还没念到底呢,自有称你们心的事。”他又往下念道:“堂娜阿尔方萨·德·索利斯已经三个星期没有跟班了。她是个老信女,每天大半在教堂里过,要个跟班时时刻刻在身边伺候。赛狄罗学士,本城神职班里一位年老的大司铎,昨晚把他的亲随撵走了……”法布利斯嚷道:“甭念了,阿利阿斯·德·隆东那先生,这个事我们要了。赛狄罗学士是我主人的朋友,他的情形我都熟悉。我知道他的女管家叫侠生德大娘,是位虔诚的老婆婆,家里事全归她做主。这是瓦拉多利数一数二的好东家,在他家里过得舒服,吃得非常好。再加那大司铎已经老态龙钟,又害痛风症,不久就得立遗嘱,还可以图他一份遗物呢。当亲随的有这指望多美呀!”他转向我道:“吉尔·布拉斯,别耽搁了,朋友,咱们立刻到学士家去吧。我想亲自介绍你去,做你的保人。”我们生怕错失这个好机会,匆匆向阿利阿斯告辞。他得了我的钱,对我担保说,如果这事不成,一定还替我找个一样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