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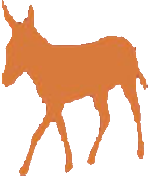 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我一天天在监狱里思前想后,聊以解闷。这时候,我口供里讲的事情已经在城里传开了。许多人好奇心动,要来看看我。我牢里有一扇小窗,可见天日,他们此来彼去,到这窗口来张望,看了一会儿,大家走开。这个新样事儿使我很诧异。我这窗外面是个静悄悄、阴惨惨的小院子,我坐牢以来,从没人在窗口露过脸。我想准是城里人知道我的事了,可是拿不定这来是吉是凶。
窗口出现的第一批人里有蒙都涅都唱圣诗的小矮个子,他也是怕吃夹棍吓跑的。我认得他,他也不装不相识。彼此招呼,两人长谈起来。我少不了又把经历说一遍,外边的人听了又笑又怜。那唱圣诗的也把我们吓跑以后、骡夫和那年轻女人在卡卡贝罗斯客店里的一段纠纷讲给我听。总之,我上文所述都是他说的。他临走答应我马上出力营救。那些好奇来看的人都同声为我惋惜,还说要帮那小矮个子为我尽力,叫我放心。
果然他们没有食言。他们打伙儿为我向法官求情。法官知道我无辜,又加那唱圣诗的把他知道的事讲了,所以在我监禁三星期之后,那法官到牢里来说道:“吉尔·布拉斯,我要是执法苛刻,还可以把你关在这儿,可是我不愿意事情尽拖下去。走吧,还你自由,随你几时出去好了。”接着道:“不过我问你,要是带你到那个树林子里,你找得出那地窟来么?”我回答道:“大爷,我找不到了。我是天黑了进去的,出来的时候天还没亮,所以认不出所在了。”法官说,他去吩咐禁子开门,就出狱去。果然过一会儿那禁子来了,带了个夹着一捆衣裳的狱卒。两人满脸正经,一言不发,剥下我身上新簇簇的细呢衣裤,换上一套旧粗布裤褂,然后推着我的肩膀,撵出门外。
犯人释放,总觉得高高兴兴,可是我一看身上衣服寒伧,未免羞惭。我直想马上溜出城去,免得众目睽睽,难以为情。可是我多承唱诗小矮个子出力帮忙,非常感激,便隐忍羞惭,找他道谢。他一见我面,忍不住大笑道:“你成了这副模样儿啊!穿了这套衣裳,一上来我认不得是你了!照此看来,法律的各种滋味你都尝遍了。”我答道:“我不怨法律,法律原是公正的。我但愿那些执法的官吏都为人公正。他们至少得留还我那套衣服,我觉得我为那套衣服出的价钱不小了。”他接着道:“我也以为然。可是他们说起来,这是向例规矩!哎,就说吧,你以为你骑的那匹马已经还给原主儿了吧?对不起,并没有!这会子在法院录事的马房里,押在那儿做盗赃的证物。可怜原主儿连一副鞍辔都未必领得回去。”接着又道:“可是咱们别谈这些事了。你有什么打算?目前想怎么办?”我说道:“我想到布果斯去找我救出来的那位太太。她会给我几个比斯多,我去买件新道袍,上萨拉曼卡,靠我肚里那点拉丁文混几个钱。我苦的是还得跑到布果斯去,一路上不能饿肚子,你知道出门人没钱要挨饿的。”他答道:“我懂得你的苦处,我的钱袋送给你吧。这钱袋实在有点儿干瘪了,不过你知道,唱圣诗的人不是主教。”他说着掏出钱袋,塞在我手里。他十分殷勤,我却之不恭,只得原封不动把钱袋收下。我十分感激,说了许多我将来补报的空话,好像他把全世界的金子都送给我了。我随就辞别出城,没去看其他帮我重获自由的人,只有千万遍为他们祝福罢了。
那唱诗的小矮个子实在不能替他那钱袋夸口,原来里面只有寥寥几文钱,而且是什么钱呢?都是不值价的小钱儿。幸喜两个月来我清苦惯了,所以我到布果斯附近彭特·德·米拉镇上的时候,还剩下几个瑞阿尔没花完。我要打听堂娜曼茜亚的消息,先在镇上歇下。我到一家客店里,那女掌柜的是个瘦小干瘪、尖利凶狠的女人。我一瞧她对我脸色难看,就知道我这件大褂不入她眼,这也怪她不得。我找个座儿,吃了些面包和奶饼,又喝了几口店里的劣酒。我吃的这餐饭和穿的衣服恰好合式。我一面吃,一面想跟女掌柜搭话。她满脸鄙夷,分明是不屑理睬。我请问她可认识加狄亚侯爵,他的田庄离这里远不远,尤其要紧问侯爵夫人近况怎样。她傲然答道:“你打听的事情倒不少啊。”她满不情愿似的告诉我说,堂安布若修的田庄离彭特·德·米拉不过短短一哩路。
吃喝了一顿,已经天黑,我说要睡了,向女掌柜讨一间房。她瞅了我一眼,看得我十分轻贱,说道:“房间轮得到你啊!吃一角奶饼当晚饭的人,我这里没他们住的房间!这儿的铺位都有主顾了,今天晚上我等着几位大客人呢。我只能招呼你在仓房里宿一宵,我想你在柴草上睡觉也不是第一遭。”她不知道恰好一语道着。我并不答话,乖乖地爬上柴草堆,困累多天,一躺下就呼呼睡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