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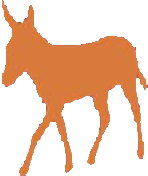 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堂娜曼茜亚讲完,哭成了个泪人儿。我并不学着塞内加的词令
 去譬解劝慰,只让她尽情哭个畅,甚至也陪她淌眼泪,因为看见人家倒运,自然会有关切之心,何况看见美人命苦呢!我正要问她,身处这般境地,作何打算。要是没有打岔,她大概就要向我请教了。偏偏这时候我们听得客店里吵成一片,不由得分了心。原来当地法官带了两个公差、一队卫兵来了。他们直闯到我们房里。同来有个年轻绅士,他先跑近来细细看我身上的衣服。他一眼就看得分明,嚷道:“圣约克在上!那就是我的袄儿呀!正是我那一件!跟我那匹马一样好认。你们凭我这句话尽管把这个强盗看起来,我不怕他来找我决斗的。我拿稳他是窝藏在本地的强盗。”
去譬解劝慰,只让她尽情哭个畅,甚至也陪她淌眼泪,因为看见人家倒运,自然会有关切之心,何况看见美人命苦呢!我正要问她,身处这般境地,作何打算。要是没有打岔,她大概就要向我请教了。偏偏这时候我们听得客店里吵成一片,不由得分了心。原来当地法官带了两个公差、一队卫兵来了。他们直闯到我们房里。同来有个年轻绅士,他先跑近来细细看我身上的衣服。他一眼就看得分明,嚷道:“圣约克在上!那就是我的袄儿呀!正是我那一件!跟我那匹马一样好认。你们凭我这句话尽管把这个强盗看起来,我不怕他来找我决斗的。我拿稳他是窝藏在本地的强盗。”
我一听知道他就是那个失主,从他身上抢来的东西偏偏都归了我,不禁惊惶失措。那司法官职责所在,见我慌张,当然以为我是畏罪,不会往好处想。他觉得那个绅士告的状有凭有据,又以为女人是我一伙的,就把我们俩分别监禁起来。这人不是那种望之凛然的法官,倒是一团和气,笑容可掬。可是天知道他也一样的厉害!我刚进监狱,他就跑来,带着两头走狗,就是那两个公差,三人都欢欢喜喜,仿佛预料好买卖到手了。他们没忘记他们那好规矩,一上来先把我通身搜遍。这几位老爷发了好一笔横财啊!他们大概从来没这样的手气。他们抓出一把一把的比斯多,喜得眼里放光,那位司法官尤其乐得不可开交。他软迷迷地对我说道:“我的孩子,我们是奉公尽职,你不要害怕;你要是没有犯罪,不会叫你吃苦。”这时候,他们从从容容把我衣袋掏摸一空;舅舅给我的四十杜加,强盗都没有碰,这次也落在他们手里。他们还不肯罢休,那几双贪手孜孜不倦,从我头上摸到脚下,把我四面旋转,又剥掉我的衣裳,看贴肉藏着钱没有。我相信他们恨不得剖开我肚子看看里面有没有钱呢。他们恪尽职守以后,司法官就来盘问。我老实陈说一遍。他叫人录下口供,带着手下人,拿了我的钱走了,扔下我一个儿赤条条坐在柴草上。
我冷冷清清的在这个境地里,不禁叹息道:“唉!人生尽是些离奇的事儿,倒霉的事儿。我自从离开奥维多,只是走背运,一波乍平,一波又起。我到这城里的时候,哪里想到就会跟司法官会面呢!”我一面无聊空想,一面把他妈的那套害人的衣服一件件穿上,于是又自己勉励道:“哎!吉尔·布拉斯啊!挺起脊梁来!设想往后也许还有好日子呢。你在地窟里都苦熬过来,倒在一个平常牢狱里心灰意懒,说得过去么!可是,唉!……”我又一阵愁:“我自哄自骗罢了!我哪里出得这个牢狱呢?人家把我的活路都断了,犯人没有钱,就好比鸟儿剪掉了翅膀。”
旅店里为我烤的野鸡和兔子,我是没福消受了;有人送进来一小块硬面包、一罐子水,任我一个儿在牢里烦躁。我整整坐了十五天牢,没见个人面,只有个禁子每天早晨送那份口粮进来。我看见他,老跟他攀谈,想解解闷,可是这位人物随我说一千句,总置之不理,一句话也逗他不出。他常常跑进跑出,正眼都不瞧我。到第十六天,司法官来了,对我说道:“朋友啊,你的苦算挨完了,你可以开怀一乐,我特来告诉你个好消息。那位跟你一起的太太,我已经叫人送到布果斯去;我在她动身前盘问了一下,她把你出脱了。据你说,你是雇了包程骡子从贝尼弗罗到卡卡贝罗斯去的,现在只要等那骡夫来作证,如果口供相符,你今天就可以出去。那骡夫在阿斯托加,我已经派人去找,正等他来。只要他说确有上夹棍那回事,我立刻放你。”
我听了满心欣喜。从此我自以为没事了。我向那司法官道谢,感激他判事又爽利又公正。我还没谢完,两名卫兵押了那骡夫进来。我立刻认得是他,可是这杀坯的骡夫准把我的皮包连装的东西都卖掉了,生怕认了我就得呕出来,所以厚着脸皮说不认得我,从来没见过。我嚷道:“啊!奸贼!你还是招出来你把我的行李卖掉了,说真话吧!你仔细认认,你在卡卡贝罗斯镇上拿夹棍来吓唬人,一群小伙子都给你吓得要命,我也在里面。”那骡夫冷冷地说,我讲的事他全不知道。他既然一口咬定不认识,我出狱又得延期。司法官对我说道:“孩子,你瞧,这骡夫没坐实你的口供,所以我尽管一心要放你,却放你不得。”我只好重新捺下性子,死心塌地,还半饥不饱地吃那干面包和白水,看那哑巴禁子的嘴脸。我一点没犯法,却跳不出法律的掌心,想到这里,我懊丧已极,倒宁可在地窟里了。我想:“其实我在监狱里比在地窟里还苦恼。我跟那群强盗大吃大喝,有说有讲,还可以做逃走的好梦;现在呢,虽然我无罪无辜,若能出牢罚充苦役,已经算大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