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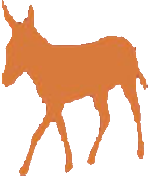 第五章
第五章
罗朗都大爷话刚说完,外面又来了六个陌生脸儿,是副头领带着队里五个大汉押了赃物回来:两个大篓子,装满了白糖、桂皮、胡椒、无花果、杏仁和葡萄干。副头领告诉大头领,刚才从贝那房特一个干货铺里抢了这两篓东西,连驮货的骡子一起牵了来。他交代完,大家把抢来的干货搬进伙食房,于是只等吃喝取乐儿了。他们厅上摆了一大桌,叫我到厨房去听雷欧娜德大娘派遣工作。我既已走上这步背运,没奈何只得隐忍着苦楚,去伺候这一群大老爷。
我先从碗柜子着手,摆上银杯,又把罗朗都大爷刚才对我卖弄的醇醪美酒摆上好几瓶。我随就送上两盘炖肉,这群人立刻坐下,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我站在他们背后伺候斟酒。我虽然没做过这种事,却非常殷勤小心,竟赢得他们赞赏。大头领把我的历史概括说了几句,大家听得很有趣。他又把我称赞了一番,可是我已经尝够了称赞的滋味,听了不会再上当。他们又一致夸奖我,说比那前任的小子好一百倍。自从我前任死后,每天原是雷欧娜德大娘斟了玉液琼浆来伺候这群地狱里的煞神,这项体面差使就归我接管。我承袭了老“赫柏”的职位,成了个新“该尼墨得斯”
 。
。
才上了炖肉,又来一大盘烧烤,一群强盗都吃得饱乎乎。他们一边大吃,一边大喝,一会儿都兴高采烈,嚷成一片。大家七嘴八舌抢着说话:一个讲故事,一个说笑话,叫的叫,唱的唱,谁都听不见谁。后来罗朗都觉得大家吵嚷着没人理会他,不耐烦了,高声喝住众人,居然全场静下来。他俨然是个首领的腔吻,说道:“诸位请听,我有个意思:咱们这样抢着说话,嚷得大家头昏脑涨,何不斯斯文文地说话儿消遣,不是好得多么?我想着咱们合伙以来,彼此都没有探问过家世,也没说起咱们干上这路买卖是什么前因后果。我觉得大可一讲。咱们何妨各谈身世,当个消遣呢?”副头领和众人好像都有一肚子趣事要说,一齐欢呼附和。于是大头领第一个讲。
“诸位,你们可知道,我是马德里富翁的独养儿子。我出世那天,合家欢喜,庆贺个不了。我爹已经上了年纪,居然盼得一个传宗接代的人,乐得无以复加。我妈亲自喂奶抚育。那时我外公还在,这老人家什么事都不管,成天念念经,又因为当兵多年,时常夸口上过火线,不免要讲讲他战场上的功劳。我渐渐成了他们三人的宝贝,你抱我抱,从不离手。我是个小娃子的时候,成天玩耍,因为他们怕我读了书要伤身体。我爹说,小孩子不宜用功,要等脑筋成熟些才行。我就一直地养脑筋,不认字,也不写字。不过我并没有光阴虚度,我爹教会了我种种玩意儿。斗牌呀,掷骰子呀,我都精通。我外公讲给我听他在军队里的许多故事,还哼诗给我听。他成天反反复复老哼那几句诗,哼了三个月之后,我也把那十一二句诗背得一字不错,我爹妈直赞我记性好。他们谈话的时候,随我畅所欲言,我插嘴乱说一通,他们只觉得我真聪明。我爹两眼着了魔似的望着我说:‘啊,看他多美啊!’我妈就来摩弄我,外公乐得眼泪都流出来。我在他们面前,无论干什么下流无耻的事都不会挨打挨骂,他们什么都原谅,他们对我真崇拜呢!一转眼我十二岁了,还没有从过老师。他们请了一位到家里来,预先切实叮嘱,不许动手责罚,只可以空言恫吓,给我几分怕惧。老师这点权力没多大用处,我不是当面嘲笑,就是含着两包眼泪找我妈或是外公去哭诉,说老师虐待我。这位可怜虫怎么辩白也没用,他们总是听我的话,把他当个凶狠家伙。有一天我故意自己抓破皮,放声叫喊,好像人家在剥我皮似的。我妈忙赶过来。我老师尽管对天发誓,说他碰都没碰我一下,我妈却把他当场撵走了。
“我照这办法把一切老师都送走,末了来了个中我意的。他是阿尔卡拉的学士,做公子哥儿的家庭教师真呱呱叫。他爱嫖、爱赌、爱喝酒;把我交托给这样一个人,真是再好没有了。他一上来竭力用软功笼络,哄得了我欢心。我爹妈因此很喜欢他,我就完全归他管教。他们不用后悔,这位老师不久就教得我精通世故。他爱去的地方都带了我同去,我受他这样熏陶,学成了个万事通,所不通的只有拉丁文。他看我无需他再教诲,就辞了我们,传授别的徒弟去了。
“我小时候在家任性胡为,成年以后一切自己做主,情形又不同了。我起初是在家里放肆,成天打趣我爹妈。他们听了不过笑笑,我说得越刻薄,他们越觉得有味儿。我又结交了一群气味相投的纨绔少年,花天酒地,无所不为。我们要天天那么乐,爹妈给的钱不够花,就拼命偷家里的钱;偷了还不够,就晚上出去做贼,倒可以大有贴补。不巧得很,当地司法官听到风声,要来逮捕我们。亏得有人报了信。我们就一溜了之,索性到官道上拦路打劫。诸位,我感谢上天保佑,虽然担惊受怕,却靠这行业过活,直到如今了。”
大头领讲完,轮到副头领。他道:“诸位,我的教养恰和罗朗都大爷的相反,但是结局相同。我爹是托雷都的屠户;他名不虚传,是那省里最凶狠的人。我妈的性子也并不比他慈善。我小时候,他们俩赌赛似的给我吃鞭子,我每天总要挨打一千下。我往往犯了小过就挨顿毒打。我一把眼泪认错求饶,也没有用,他们丝毫不肯放松。我爹打我的时候,我妈不来劝劝,反倒好像怕他打得不够狠,还要来帮一手。家里这样待我,叫我恨透了,不到十五岁就逃出来,一路讨饭,取道阿拉贡,到萨拉戈萨。我在那儿跟叫花子混在一起,他们倒也够逍遥快乐的。他们教我种种秘诀,装瞎子,装做断手折腿的,假造腿上烂疮等等。每天早上,我们好像在演习一幕喜剧,一个个派定了角色,各自扮演,每人都有一定的岗位。到晚上,我们聚在一起,把日间对我们发善心的人挖苦形容着取笑。可是我对这群花子渐渐厌烦了,想跟比较上流的人来往,因此交结了一群骗子。他们教会我好些讹人诈人的法门,可是和我们通气的一个警察翻了脸,我们在萨拉戈萨站不住脚,只好各寻生路。我觉得自己生性敢作敢为,所以跟一帮征收买路钱的好汉合伙。他们的生涯真合我脾胃,我从此就不想改行了。我很感谢我爹妈虐待了我,假如他们待得我好一点,我到现在左右不过是个倒霉的屠户,哪会荣任你们的副头领呢!”
坐在正副头领两人中间的一个年轻强盗抢着说道:“诸位,不是我夸口,方才两位讲的身世都不如我的那么错综离奇,你们听了就知道我这话不错。我是赛维尔附近一个乡下女人生的。我出世了三个礼拜,有人看她年纪轻、相貌好、奶水多,要雇她奶一个孩子。那孩子是赛维尔贵族人家的独养儿子。我妈很乐意,就上那人家去领那孩子。人家把孩子交托给她。她一领到乡下家里,发觉那孩子相貌很像我,就心生一计,要我顶替那位贵家公子,以为我将来自会报答她这番恩情。我爹是个农夫,不知轻重,也赞成掉包。于是他们把两个孩子的衣服交换一下,堂罗德利克·德·黑瑞拉的儿子顶了我的名儿寄养到另一个奶妈家去,我顶着他的名把亲娘当了奶妈。
“常言道,骨肉之间有天性感应,可是那小爷的爹娘虽然孩子换掉,却没事人儿一般。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上了当,直到我七岁还不离手地抱我。他们想要把我教成个无所不通的上等人,为我请了各种教师。可是最高明的先生也难免教出个把不肖弟子。我对他们教我做的练习毫无兴趣;他们传授我的各种学问更叫我厌倦。我倒是喜欢和底下人玩耍,不时跑到厨房或马房去找他们。可是不久我就不一味贪玩儿了,我不到十七岁就天天喝得醉醺醺的。我又把家里女用人个个都调戏到,尤其看中一个灶下丫头,觉得她最值得勾引。她是个肥头胖脸的女人,脾气好,身体结实,很中我意。我和她偷情毫无顾忌,连堂罗德利克都看见了。他疾言厉色教训了我一顿,骂我下流,又怕我见了心上人把他的劝戒当做耳边风,爽性把我的情人撵走。
“这一来我可火了,决计要出一口气。我偷了堂娜罗德利克的首饰,值好大一笔钱。我就去找我那美丽的海伦
 。她住在跟她要好的一个洗衣女人家里;我大天白日把她带走,要叫人人知道。这还不算,我把她带到她家乡,跟她正式结婚,一来气气堂罗德利克,二来也替公子哥儿们做下个好榜样。我结了这门好亲事,过三个月,听说堂罗德利克死了。我听到这消息当然动心,忙赶回赛维尔去承继他的家业,可是一到那里,才知道出了变故了。原来我生身的妈也已经过世。她临死不谨慎,当着本村神父和许多证人把掉包的勾当全盘招供。堂罗德利克的亲生儿子已经占了我的地位,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地位;大家都承认他了,他们对我越不满意,就越加喜欢他。我知道这方面再没什么指望,对我那胖老婆也腻味了,就入伙干这行没本钱的买卖。”
。她住在跟她要好的一个洗衣女人家里;我大天白日把她带走,要叫人人知道。这还不算,我把她带到她家乡,跟她正式结婚,一来气气堂罗德利克,二来也替公子哥儿们做下个好榜样。我结了这门好亲事,过三个月,听说堂罗德利克死了。我听到这消息当然动心,忙赶回赛维尔去承继他的家业,可是一到那里,才知道出了变故了。原来我生身的妈也已经过世。她临死不谨慎,当着本村神父和许多证人把掉包的勾当全盘招供。堂罗德利克的亲生儿子已经占了我的地位,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地位;大家都承认他了,他们对我越不满意,就越加喜欢他。我知道这方面再没什么指望,对我那胖老婆也腻味了,就入伙干这行没本钱的买卖。”
这个年轻强盗讲完,另一个说,他是布果斯商人的儿子,年轻的时候忽然虔诚过分,进了个戒律严紧的修会,过几年便叛教出会。长话短说,八个强盗个个都叙述了身世。我听完恍然,怪道他们会聚到一处来。他们又拨转话头,谈论下一次出马的各种计策;议定以后,大家散席,预备睡觉去。他们点上蜡烛,各自回房。我跟罗朗都头领到他房里,帮他脱衣裳,他高高兴兴地说道:“好!吉尔·布拉斯,你现在看见我们是怎么样过的了。我们总是快快活活,彼此没有怨恨,没有忌妒,也从没有什么争执,那起修士还没我们那样打成一片呢。”又道:“孩子啊,你在这儿可以过得很称心,我想你不会糊涂到不屑与强盗为伍吧?哎,普天之下,谁不是强盗?朋友,谁都是!谁都爱抢夺旁人的东西,世情一概如此,只是抢夺的方法各个不同。譬如说吧,帝王南征北伐,抢夺别人的国家;贵人借了钱不还;银行家、司库员、股票经纪人、批发零售的各种商人,谁算得诚实呀!至于司法界,我也不用说了,他们干得出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不过我承认他们比我们慈悲些;我们时常杀害无辜,他们竟会出脱该死的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