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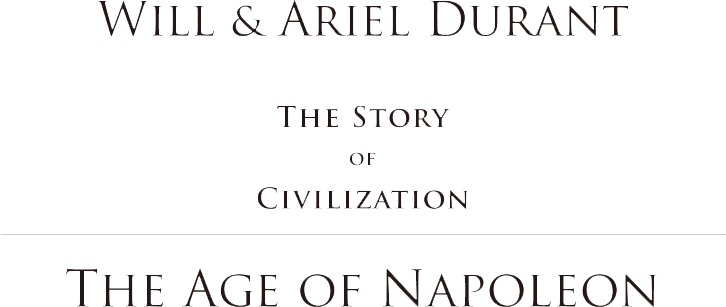
在18世纪的欧洲,法国是人口最稠密、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1780年,俄国有居民2400万人,意大利1700万人,西班牙1000万人,大不列颠900万人,普鲁士860万人,奥地利790万人,爱尔兰400万人,比利时220万人,葡萄牙210万人,瑞典200万人,荷兰190万人,瑞士140万人,丹麦80万人,挪威70万人,而法国人口为2500万人。巴黎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也是欧洲教育程度最高而且意趣盎然的城市,居民约650万人。
法国人民分为三个等级或阶级(身份):教士,约13万人;贵族,约40万人;余下的皆为平民。经济方面不断好转、政治上却处于不利地位的第三阶级,尝试取得与他们增长中的财富相称的政治力量与社会地位,由此引发了法国大革命。每一阶级又分为子群或层,以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归属人群。
最富有的阶级是教会的教阶组织——红衣主教、大主教、主教与修道院院长,而地方上的牧师与副牧师最穷。经济因素超越教义界限,在法国大革命中,阶级较低的教士与民众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上级。修道院生活已失去其吸引力,在法国,圣本笃教团的僧侣人数,由1770年的6434人减至1790年的4300人。几个不太重要的修道会,在1780年以前被解散,耶稣会则早已于1773年解散。一般说来,宗教在法国城市中衰退了,许多城市的教堂一半是空的。在农村,异教徒习惯和古老迷信积极地与教会的教义和仪式展开竞争。不过,修女仍然积极献身于教育与看护,并受到富人和穷人的一致赞誉。即使存在对基督教的怀疑,仍有成千上万的女人、小孩与男人,以敬神求其生活免受命运的打击而获得安逸,借圣人的传说来满足他们的想象,用宗教节日来缓解连续工作的劳苦,而且想从宗教中寻找一种打破困惑与拯救绝望的镇痛剂。
政府之所以支持教会,是因为政治家承认: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牧师能给予他们不可缺少的帮助。依他们的看法,人类禀赋的不同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财富分配不均。因此,为了资产阶级的安全,必须维持温和而谦恭的公议,用以补偿穷人对天堂的向往。这对法国意义甚大,因为以宗教为支撑的家庭仍然是政府兴衰、国家安危的基础。此外,牧师谆谆教诲信徒信仰国王的神圣权力,鼓励他们服从这个地位与权力的天定旨意,而国王也觉得这种神话对维护统治秩序很有助益。因此,他们几乎将各种公共教育都留给天主教教士。新教在法国的成长威胁到国家教会的权威与利益时,胡格诺派便被无情地驱逐了。
为感谢天主教士们的服务,政府允许教会从每个教区收取什一税及其他所得,允许他们从事遗嘱的制作——催促将死的“罪人”购买可去天堂的赎罪券——作为交换,罪人们把自己俗世的财产遗留给教会。政府免除教士的赋税,因此时常从教会收到丰富的“自由捐赠”。被赋予如此众多的特权,教会在法国积聚了大量的土地——总计为1/5的国土,并将这些当作封建财产来管理,征收封建税。教会将信徒的捐献转换为金银装饰品,比如镶在皇冠上的珠宝,那是历来对抗通货膨胀的方法,也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樊篱。
由于教会盘剥什一税,许多教区的教士竟失去了教区的收入,只能在虔诚的贫穷中工作,许多主教却生活得舒适优裕。高贵的大主教还可以远离他们的教区,出入王宫。法国政府濒临破产之际,按照塔列朗的估计,法国教会享有1.5亿利维尔的年收入。负担纳税的第三阶级,对政府没有迫使教会将它的财富拿出来分享而深感诧异。“不信仰”的文艺作品散布开来时,数以千计的中阶层市民与数以百计的贵族放弃了对基督的信仰,而且用哲学上的冷静态度旁观大革命侵袭那些神圣的阶级堡垒。
贵族阶级隐约发觉自己失去了许多一直赖以为生的特权:他们作为佩带剑的贵族,曾代表了军队的防卫力量、经济的“指挥者”与农业社会的“司法首领”。但是这些权益大多数被黎塞留与路易十四统治下的中央集权权力的实施取代。许多领主居于王宫,并不在意他们的领地。1789年,他们服饰华贵,风度优雅,而他们的平易亲切,让人很难想象他们拥有全国的1/4土地,并有丰足的封建税收收入。
他们中较古老的家庭自称为贵族阶级,他们的血统可追溯至5世纪征服并重新命名高卢的日耳曼法兰克人(Germanic Franks)。1789年,德穆兰称大革命为迟延已久的种族报复时,他利用这种自豪来对抗外来的侵略者。实际上,约95%的法国贵族是渐增的中产阶级与凯尔特人,他们的土地和头衔与中产阶级新的财富和伶俐的头脑合为一体了。
新兴贵族——大礼服贵族——约包括4000个家族,其家长由于被指派了司法或行政的职位,因而自动地享有贵族身份。大多数这种职位被国王或他的大臣们出售而为国家增加收益时,许多购买者认为以温和的索贿手段重新收回他们的支出已有了保证。“当政者贪财”,“在法国十分猖獗”,这样的言语,只是濒临灭亡政权的成百抱怨中的一种。这些官衔与阶级有些是世袭的,持有者加倍,特别在最高法院或各地区的法院中他们的自傲与权力增加至1787年的顶点时——巴黎的最高法院要求对国王的敕令有否决权力,以时间而言大革命开始逼近了。
在《何为第三阶级》(一本小册子,出版于1789年1月)中,作者西哀士提出并解答了三个问题:什么是第三阶级——一切东西;直到现在它是什么情形——一无所有;什么是它想要推出的——一些东西。在尚福尔的修正中,最主要者包括: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及它的10万户家庭与它的许多阶层——银行家、代理商、企业家、商人、经理、医生、科学家、教师、艺术家、作家、新闻记者、新闻界(第四“阶级”,或力量)和小民(有时称“人民”)——包括城镇的贫民与商人,在陆上或海上的运输工人和农人。
中上阶层掌握、支配正在增大并扩张中的势力:可流动货币与其他资本的力量,与静态的地产或衰微的宗教信条展开积极的竞争。他们投机于巴黎、伦敦与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所,而且依照内克的估计,中上阶层已经控制了欧洲一半的货币。他们以贷款来资助法国政府,如果贷款与费用不能偿付,则以推翻政府作为威胁手段。他们拥有或经营着法国北部迅速成长的矿业与冶矿业,里昂、特鲁瓦、阿布维尔、里尔与鲁昂的纺织业,洛林的铁工厂与盐厂,马赛的肥皂工厂,巴黎的制革业。他们经营着正在取代过去手工艺作坊与同业公会的资本主义工业。他们欢迎重农主义者的理论,因为自由企业较传统的工业规约与国家的贸易更加刺激而有生命力。他们资助并筹划由原料到制成品的转换,并将这些成品由生产者运至消费者,使双方均获得利润。他们得益于欧洲最好的3万英里道路,但是他们公然抨击法国对道路与运河征收的通行税,及由各省不遗余力地维持的度量制度。他们控制商业,使波尔多、马赛与南特富足;他们组织如英德斯与伊沃克斯这类庞大的股份公司;他们将市场由城市拓展到世界,进而通过这种贸易使法国发展为仅次于英国的海外帝国。发觉到他们——而非贵族——是法国渐增财富的创造者时,他们决定与贵族和教士均等地分享政府的利益与职位,竞争在法律上与王宫内的地位,涉足所有法国社会上的特权与恩赐的途径。罗兰夫人——高尚而有教养但属于中产阶级——应邀造访一位有爵位的夫人,却被要求在那里与仆人共餐而不得与贵族宾客同座时,她发出抗议的呼喊,得到中产阶级发自内心的共鸣。他们结合“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箴言时,愤慨与热望已经固植于他们的思想中了。这并不意味着其向下或向上,但可作为行动宗旨直到陋习得以变革。于是,中产阶级成为支持大革命最主要的力量。
他们塞满戏院,为博马舍讽刺贵族社会而喝彩。他们加入互助会分会,为生活与思想的自由而工作,其努力竟甚于贵族。他们阅读伏尔泰的作品,领略到他的腐蚀性的才智。他们赞同吉本关于“所有宗教对哲学家同样虚假,而对政治家却同样有用”的看法。他们秘密地崇拜霍尔巴赫与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认为它可能不完全是生活与思想中的指导原则,但要对抗控制大多数人心与一半法国财富的教会,它的确是便于使用的武器。他们同意狄德罗关于现存政体的一切几乎都是荒谬的看法。他们不喜欢卢梭,因为他有社会主义气味。但是他们比起法国社会任何其他等级的人们,更能感受并扩大文学和哲学的影响。
通常,哲学家在政治上是稳健的,他们接受君主政体,而且不憎恶王室的礼物。他们指望“开明的君主”像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甚至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而不将粗鄙与冲动的劳动阶级当作改革的政客。他们确信理性,即使他们知道它的极限与适应性。他们推翻由教会和国家控制的思想禁锢,开放与扩大了成百万人的心智。他们为科学在19世纪的胜利做准备,甚至——拉瓦锡、拉普拉斯与拉马克这样的科学家,也加入大革命和战争的大动乱中。
卢梭使自己脱离哲学。他尊重理性,但是他高度地屈服于情感与一种令人鼓舞、使痛苦缓和的信仰。他的《萨伏依人教区牧师的宗教职业》为罗伯斯庇尔提供了一个宗教的立场。他的坚决主张统一的国家教条,让公共安全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宣布政治邪说——起码在战时——为死罪。大革命的雅各宾派接受《社会契约论》的主张:人类是天生善良的,但受腐败制度与不公平法律的支配而变坏了;人类是天生自由的,却变成了人为的文明的奴隶。在权力方面,大革命的领袖们采取了卢梭的观念,即“公民”应接受政府的保障,发誓绝对服从政府。马莱·迪庞写道:“1788年,我在街上听到马拉朗读并评论《社会契约论》,热心的听众为之喝彩。”卢梭的人民主权在大革命时先变成国家的主权,继而变成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主权,最后竟变成一人的主权。
“人民”在大革命的词汇中,意指农人与市镇工人。即便工人占人口较少的市镇,那里没有连绵不断的工厂,而是有着哼着好听调子的屠户、面包师傅、酿造者、杂货商、厨子、小贩、理发师、零售商、旅馆老板、葡萄酒商、木匠、泥水匠、油漆匠、玻璃工人、石膏师、农夫、鞋匠、女裁缝、染匠、清洁工人、成衣匠、铁匠、用人、家具师、马具师、车匠、金匠、刀匠、织工、制革匠、印刷工人、书商、妓女与小偷的地方。这些劳动者穿着长及足踝的窄裤而非上流社会的及膝短裤(裙裤)与长袜,因此被称为“无套裤汉”(sans culottes),他们在大革命中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从新大陆流入的金银与不断发行的纸币,使欧洲各地物价上升。在法国,1741年至1789年,物价上升了65%,而工资仅上升了22%。在里昂有3万人于1787年接受救济,在巴黎有10万户家庭于1791年被列为贫困户。劳工联盟支持的经济行为受到禁止,罢工虽被禁止,仍不断发生。大革命快到来时,劳动者处在不断递增的沮丧与反叛中。只要给他们枪支与一位领袖,他们就会攻下巴士底监狱,侵入土伊勒里宫,而且废除国王。
1789年法国农民的生活境况也许较优于一个世纪以前,当时拉布吕耶尔夸张地指出一篇论文误认他们为野兽。也许除意大利北部的农民以外,大部分法国农民的境况较优裕于欧洲大陆其他各地的农民。约1/3的可耕地由自耕农占有,1/3则被贵族、教会或资产阶级所有者出租给佃户或佃农,其余则由农场雇工在所有者或管事人的监督下经营。越来越多的所有者关注以前让农民自由放牧家畜或采集木材的“公共用地”(common lands),在为成本增加及剧烈的竞争烦恼——为了耕种或畜牧之故。
除少数拥有“自由地的”(无义务的)农民外,一切土地都受制于封建税。他们受契约特许状约束,每年给领主——贵族的采邑——几天无报酬的劳务(强迫劳役),帮助领主耕作土地与修复道路。不论何时,他们在使用那些道路时,还得向领主付通行税。他们每年应付给领主一定的产品或现金,作为免役税。如果他们出售他们的土地,领主有权得到10%或15%的收益。如果在领主的河流捕鱼或在领主的农场放牧时,他们要付费用给领主。每次使用领主的磨坊、面包厂、葡萄榨汁器或榨油器时,他们都需要支付费用,因为这些费用是受特许状保护的。通货膨胀时,土地持有人因价格上升而以日渐严厉的手段来课征,从而使自己的收入有所保障。
因为教会保佑收成,并以圣礼使农民的生命尊荣,农民每年献什一税给教会——通常不及年收入的1/10。比什一税或封建税更重的是政府向他们征的税:人头税——每年收入的1/20;销售税——他们每次购买金或银器具,金属产品、酒、纸、淀粉等商品要交纳;盐税——每年必须以政府规定的价格向政府认购一定量的盐。因为贵族与教士发现很多合法与不合法的方法可以逃避许多税收——战时的征集,富有的年轻人可购买替身赴死,于是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支持政府与教会的重担均落在农民身上。
这些税收,包括什一税和封建税,收成好时可能还交得起。但是,因战争破坏或自然灾害使收成变差,一年的辛苦工作眼看着白费时,这些税赋就带来不幸了。于是,许多地主将他们的土地和劳工,出售给土地投机者。
1788年是以冷酷的天灾为特色的。一次严重的旱灾阻碍了农作物的生长;一场大冰雹,从诺曼底袭击到香槟地区,蹂躏了180英里平素肥沃的地带。1788年的冬季是18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寒的一个冬天,成千的果树冻死。1789年,水灾损失惨重,夏季发生的饥荒几乎波及每个省。政府、教会与私人慈善机构努力供给食物以抵抗饥馑,虽然只有少数人饿死,但数百万的人生活资源匮乏。从卡昂、鲁昂、南锡、奥尔良、里昂,可看到为玉米而激烈争斗的景象;在马赛可看到8000个饥饿的人,在城门口威胁着要进占与抢夺城市;在巴黎圣安托万的工人阶级区内,有3万名贫民需要照顾。同时,一项放宽与大不列颠的贸易条约(1786年),造成法国工业产品的过剩,以致本国货物跌价,并促使无数法国工人失业——里昂2.5万人,亚眠4.6万人,巴黎8万人。1789年3月,农民拒绝缴税,这加速了国家破产的厄运。
阿瑟·扬(Arthur Young)于1789年7月到法国首都以外各地旅行,遇见一名农村妇女,她抱怨税收和封建税使农民永远生活在贫困边缘。但是,她接着说,她知道“有一些伟人愿为这样贫穷的国家做一些事……因为税收与封建税正压榨着我们”。他们听说路易十六(下文简称为路易)是一位好人,他渴望改革弊病与保护穷人。他们满怀希望地遥望着凡尔赛宫,为国王的长寿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