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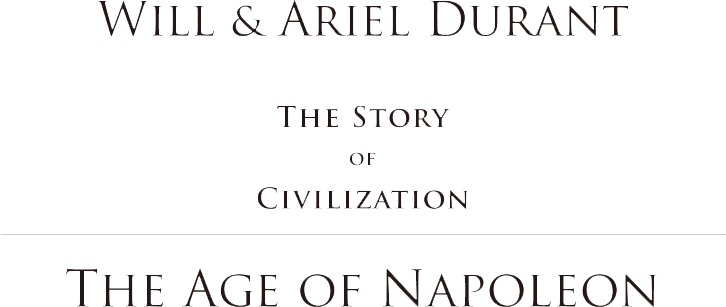
舍弃了道德的宗教基础——敬爱并恐惧着一位警觉世象、记录善恶、赏罚人类的上帝,服从属于他的法律与圣训,法国人民发现他们自己没有保障,因而只有用他们已放弃的伦理教条抑制那些产生于中古世纪的饥饿、贪婪、危亡,而且与深深扎根于他们身上的最老、最强、最个人主义的本性做斗争。他们把基督教的伦理托付于他们的妻子与儿女,在畏惧暴力的动乱社会中寻求可作为道德铁锚的新观念。他们希望在其中发现公德心,接受从有组织及有保护的社会的义务与特权的意义上来说的公民职责与权利。在每个道德选择上,个人为偿付保护与社会的许多劳务,必须认识社会的完善是占最重要地位的法律——人民利益至上(salus populi suprema lex)。建立天赋的个人道德的规范是宏大的计划。溯及整个基督教的世纪,哲学家的代表——米拉波、孔多塞、罗伯斯庇尔、维尼奥、罗兰、圣茹斯特——在正统派的历史或传说中发掘他们寻找的典型:李奥尼达、伊巴密浓达、布吕蒂斯、加图与西庇阿。因此,视爱国为至上职责的人可能为国家的利益而正义地杀死他的儿女或父母。
大革命的第一回合适当而顺利地经历新道德。第二回合开始于1792年8月10日:巴黎民众废除路易,并掌握无责任感的专制主义权力。在旧政体下,一些哲学家与圣者鼓吹贵族社会体面与人道主义的特性,以减轻人类相互掠夺与攻击的天赋癖性。但现在接着的是阴惨的行动,“九月大屠杀”,国王与王后的死刑,及恐怖时代与所有断头台牺牲的延伸,罗兰夫人描述为“各各他(Golgotha,在耶路撒冷附近,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地)的巨大屠杀”。大革命的领袖成为战争的投机者,迫使被占领地区慷慨地支付人权的代价,法国军队被吩咐依靠占领区过活,被解除束缚者或战败者的艺术珍宝归属于得胜的法国。此外,立法者与军官勾结补给者以欺骗政府与军队。在放任主义的经济中,生产者、分配者与消费者竞相诈取,或规避最大可接受的价格与工资。这些或类似的恶劣行为当然早在大革命前几千年就已存在,但是在对它们控制的尝试中,新道德鼓吹的“公德心”似乎毫无助益。
在大革命使社会秩序不稳,在生命加注不安全因素时,民众以犯罪表现他们的不安,在赌博中寻求乐趣。决斗继续着,但不像以前那么频繁。1791年和1792年曾宣布禁止赌博,但是秘密的赌场加倍,1794年前巴黎已有3000家赌场。督政府期间,富裕的上流社会人士下注金额庞大,以致许多家庭毁灭于命运的转变。1796年,督政府恢复“国家彩票”(Loterie Nationale)。巴黎公社的土伊勒里派(Tuileries section)向国民公会请愿,请求用法律废止所有的赌场和妓院。“没有道德,”它表示,“就可能没有法律与秩序,没有个人安全,也没有自由。”
大革命政府费力地给予易怒、暴力的民众一个新的法律制度,但是信仰衰落与国王的死亡让他们在道德和法律上解缆。伏尔泰要求全面修订法国的法律,并将360项省或地区的法规整合成为全法国有条理的法律。这个请求在大革命骚动时期未被准许,它必须等候拿破仑的处置。1780年,夏隆学院提供奖金给有关“不危及公共安全之下减缓法国刑罚的最好方法”的最佳论文。路易则以废除严刑拷问回应之(1780年),并于1788年宣布愿意将所有的法国刑法修订成为前后一贯的法国法律。此外,“我们将寻求各种方法缓减惩罚的严酷而不损及良好的法制”。当时掌握巴黎的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律师梅斯与贝桑松反对这个计划,国王也正为他的生存而战,遂将其搁置。
提呈至1789年三级会议的“陈情书”建议几项法律的改革:审判应予公开,被告人应允许有法律顾问的协助;国王逮捕反叛者的密令应加禁止,有陪审团的审判应予建立。6月,国王宣布逮捕反叛者的密令终止,同时其他改革立即被立宪会议确定为法律。陪审团制度曾存在于中世纪的法国,现已恢复。立法者现在可以不受教会的影响,而且留心于商业的需要——1789年10月3日宣布,索取利息不是犯罪行为。1794年的两项法律解放了法国及其殖民地的所有奴隶,并将法国公民权给予黑人。基于“一个绝对自由的国家不能允许任何社团在它的核心内”的理由,1792年至1794年的种种法律禁止所有兄弟会、学会、文艺协会、宗教组织与商业社团。令人奇怪的是,雅各宾俱乐部不受损伤,但劳工联盟被禁止。大革命迅速以万能政府取代君主专政。
旧法律的繁杂、新法律的树立及商业关系的逐渐复杂,促成律师倍增,因而律师现在取代教士成为第一阶级。自从最高法院解散后,他们并未被正式组织起来,但是他们了解所有法律上的漏洞及所有程序上的诡计与伎俩,因而变得很有权势以致政府——本身也是律师集团——发现很难加以控制。人民开始抗议法律的迟误、律师的阴险与立法的代价高昂,因为使所有人民在法官面前平等并不属实。一连串的会议尝试不同的措施,以减少律师的数量并弱化其权力。在反律师法猛烈进行时,他们禁止所有公证人的活动(1791年9月23日),关闭所有法律学校(1793年9月15日),而且宣布(1793年10月24日):“律师事务所予以撤销,诉讼当事人仅可授权代理人代表他们。”这些法规常常被规避而留有记录,一直到1800年3月18日拿破仑复原律师制为止。
大革命在刑法的修正上有较好的改进。过程较为公开,这将暂时结束秘密审查和证据匿名。监狱不再成为苛责的主要手段。在许多监狱,入狱者被准许携带书籍甚至家具,而且只要出钱还可享受由外面送进的食物,可以有限制地谈恋爱。我们听到一些温情的恋爱事件,像囚犯约瑟芬与囚犯奥什将军。国民公会批准过成百的死刑执行,在它最后会期宣布(1795年10月26日):“从和平公告之日起,法兰西共和国各处的死刑废止。”
同时,大革命宣称它能改善死刑的方法。1789年,吉约坦博士(Joseph Ignace Guillotin),三级会议的代表,建议以机械刀刃代替绞刑吏与用斧者,因为它可以在人感觉痛苦前就被砍头。这不是新想法,13世纪以来它被用于意大利与德国。在医生手术刀对尸体做若干试验后,“斩首机”于1792年4月25日被竖立在德格莱维广场(Place de Grève,现在的市政府广场),然后在别处逐渐竖立。死刑为之加速。这种死刑一时吸引许多群众,其中包括一些嬉戏的妇女与孩童。但是它们过于频繁,以致成为可以忽视的常事。“民众,”同时代一家杂志报道,“暴动发生时继续在他们的店铺中工作,甚至不因搅扰而抬起他们的头。”谦恭者活得最久。
在囚车之间,在废墟之中,爱与性幸存。大革命已忘记医院,但在医院,在战场,在贫民窟,慈善减轻了痛苦与悲伤。美德阻遏邪恶,父母的情爱同时残存于子女的自主。许多孩子看到父母的无能,因而惊服大革命的热情与新风尚,他们中一些人抛弃旧道德限制,变成无忧无虑的享乐主义者。男女乱交盛行,性病蔓延,弃儿倍增,性变态风行。
萨德侯爵出生于巴黎东南普罗万一个地位很高的家族,高升为布雷西亚与比热的总督,似乎注定终身为行政官。但是他的心中激荡并沸腾着性幻想,为了使它们成为正当的哲学而寻求不已。涉及与4名女子的风流韵事后,他在艾克斯昂省以“毒害与兽奸之罪”被判死刑(1772年)。他逃亡,被捕,再逃亡,犯了更大的罪,逃至意大利,回到法国后,在巴黎被捕,监禁在樊尚(1778—1784年)、巴士底狱和沙朗通(1789年)。1790年获释后,他支持大革命。1792年,他是皮克派(Section des Piques)的书记。大恐怖期间,由于他被误认为是一名回来的移民而被逮捕。一年之后被释放。1801年,在拿破仑的统治下,他因出版《朱斯蒂娜》(Justine,1791年)与《朱丽叶》(Juliette,1792年)而再度入狱。这些是性经验的小说,有正常与不正常的。作者偏好不正常的性行为,而且使用相当的文学手腕替自己辩护。所有的性欲——他主张——是自然的,而且应无愧内心地纵情,甚至可以从传染病毒的痛苦中获得性欲的欢乐。他以一字声名(指萨德主义)永垂不朽。他在不同的监狱度过他最后的生命,写作风采优雅的剧本,最后死于沙朗通精神病院。
我们得知在大革命期间大学生之间的同性恋,可推测它已普及于监狱。妓院一般开在王宫附近,在土伊勒里宫的花园、圣希拉尔街与白蒂沙普街,妓女极多。她们也出现在戏院与歌剧院中,甚至出现在立宪议会与国民公会的走廊上。标注着女人的住址与费用的小册子到处都是。1793年4月24日,坦普尔派(Temple Section)发布一项命令,“会议……愿意终止由公共道德毁灭及女性堕落与不忠引起的无数不幸,而且借此指派警察局局长”等。其他派系从事运动,私人的巡查被组成,一些罪犯遭到逮捕。罗伯斯庇尔支持这个措施,但是在他死后监护人的勤勉为之松懈,娼妓再度出现于督政府期间。
1792年9月20日以后,只有公证结婚是合法的,教士是不必要的,只需要在官方作证下签署共同的誓约。在较低的阶层,许多男女未婚同居。私生子数目庞大。1796年,法国登记有4.4万名弃儿。1789年至1839年,默朗的新娘在她们结婚时24%是怀孕的。法国大革命前丈夫通奸常被赦免,富有的人可能有情妇,在督政府期间情妇更是被公开夸耀。1792年9月20日的一项法令使离婚合法。女人的合法权利有所增加。由于更多不为习俗约束的年轻人逞强,父系的权威因而减少。1802年,普伦普特里在法国旅游时,在报道中引用一位园丁的话:
在大革命期间我们不敢责怪我们孩子的过错。那些自称为爱国者的,视惩罚孩子为违背自由的基本原则。这些变得十分难以控制,以致一位父亲责骂他的孩子时,后者常常会告诉他应管好他自己的事业,又说“我们是自由与平等的,共和国是我们唯一的父亲,并无其他的”……那将需要许多年使他们服从。
色情文学盛行,成为年轻人最喜爱的读物。1795年以前(如同1871年),一些曾经过激的父母开始将他们的儿子送进教士管理的学校,为的是远离一般放荡的道德与作风。一时,家庭似乎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受害者。但在拿破仑时期,风纪的恢复暂缓,一直到工业革命才较缓慢较一致地给予改正。
在旧制度期间,妇女由于优雅的风度与高尚的情操,及她们思想的教化而获得很高地位的这种情况,大多受限于贵族与中上阶层。但1789年以前,妇女团体显然在政治中脱颖而出。她们前进至凡尔赛,并将国王与王后送回巴黎作为突然得权的公社的俘虏后,几乎赢得大革命。
 1790年7月,孔多塞发表一篇文章《准许妇女有参政权》。12月,艾德夫人尝试成立俱乐部献身于女权运动。妇女在议会的旁听席上表达她们的意见,而且试图组织她们自己。她们获得若干利益:妻子与丈夫一样,能请求离婚;母亲与父亲一样,对未达限定年龄儿女的婚姻,有许可或否定的责任。督政府期间,无选举权的妇女成为政治上公开的力量,支持部长与将军,而且骄傲地展示她们在风度、道德与服装上的新自由。拿破仑于1795年26岁时,这样描述她们:
1790年7月,孔多塞发表一篇文章《准许妇女有参政权》。12月,艾德夫人尝试成立俱乐部献身于女权运动。妇女在议会的旁听席上表达她们的意见,而且试图组织她们自己。她们获得若干利益:妻子与丈夫一样,能请求离婚;母亲与父亲一样,对未达限定年龄儿女的婚姻,有许可或否定的责任。督政府期间,无选举权的妇女成为政治上公开的力量,支持部长与将军,而且骄傲地展示她们在风度、道德与服装上的新自由。拿破仑于1795年26岁时,这样描述她们:
妇女在各处——在游戏场所,在公共散步之处,在图书馆。你们在学者研究室看到非常美丽的妇女。世界各地只有此处(巴黎),女人的确具有值得男人为她们疯狂的影响力,而且男人不考虑其他,仅为了她们度过一生。一个女人为了知道什么是应给予她的、什么是她应有的权利,必须在巴黎住上6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