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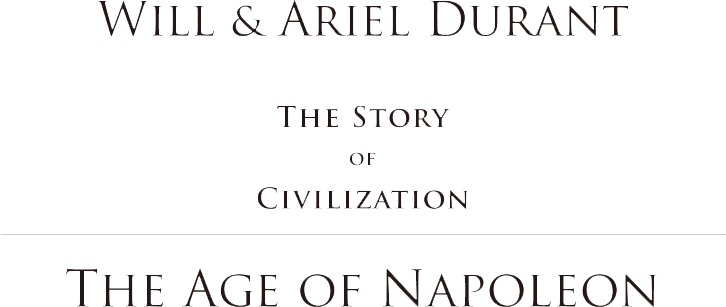
巴士底狱的占领不只是打击专制主义的象征性行动,它使国民会议不隶属于国王在凡尔赛的军队,而且使新的巴黎政府不受敌军的支配,它很不愿意支持资产阶级革命,但它给予首都人民军火与武器,允许无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发展。
杂志进一步鼓舞巴黎市民。《法国公报》、《信使报》与《巴黎日报》是旧有的报纸,具有同样的水准。目前又出现卢斯塔洛(Loustalot)的《巴黎大革命》(Les Révolutions de Paris,1789年7月17日)、布里索的《法国爱国者》(Le Patriote Français,7月28日)、马拉的《人民之友》(L'Ami du Peuple,9月12日)、德穆兰的《法国大革命》(Révolutions de France,11月28日)……除了这些,每天还有成打小册子出版。这些小册子利用出版自由,增添新偶像,损毁旧名望。从毁谤(libel)这个字出自这些小册子的名称上(Libelles),我们可想象出它们的内容。
马拉是最极端、鲁莽、无情与有力的新人物。1743年5月24日,他出生在瑞士的纳沙泰尔。他的母亲是瑞士人,而父亲则为撒丁人。他从未停止崇拜卢梭。他在波尔多与巴黎攻读医学,并在伦敦行医时获得一定的成就(1765—1777年)。有关他在那里犯罪与荒唐的事,可能是他的敌人捏造出来提供给新闻业者的。他接受由圣安德鲁斯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而这个举动,如约翰逊所说的,是“借学位变得较为富有”。马拉以英文创作《奴隶的枷锁》(The Chains of Slavery),并在伦敦出版(1774年),激烈地指责欧洲政府与国王、贵族及教士共谋欺骗人民并使他们服从。1777年,他回到巴黎,在阿图瓦伯爵的马房做兽医,后升为伯爵卫队的内科医生。他赢得肺科与眼科专家的美名。他还发表了电、光与火方面的论文,其中有些被翻译成德文。马拉认为这些将带给他科学院会员的资格。但是他对牛顿的抨击使他受到了院士们的质疑。
马拉是一个极为骄傲的人,因受连续疾病的困累而敏感到了极端容易愤怒。他患上了难以治疗的皮肤炎,但他发现在温水浴盆中坐着或写字可暂时解除痛苦。就他5英尺的身高而言,他的头是太大了,两只眼睛也不平齐。一般人了解他喜欢独居。医生经常为他放血以减轻他的痛苦。在病情相对稳定时,他赚取他人的金钱。他做事具有强烈毁灭的野心。“我仅用24个小时中的2个小时睡眠……在3年中我未曾有过15分钟娱乐。”1793年,也许由于太多的室内生活,他罹患肺部疾病。后来那个刺杀了他的科黛,并不知道他不久将离开人世。
他的个性因他的疾病受到损害——他脾气的发作,他伟大的幻想,他对内克、拉法耶特与拉瓦锡的严厉批评,他发怒所招惹的群众暴动,掩盖了他很多的勇气、勤勉与奉献。他刊物的成功,不仅是由于他的风格过分夸张,而且他对无选举权的无产者仍有更多热心、坚毅与无报酬的支持。
马拉不高估民众的才智。他见到暴动升级,就加入它。但是至少在目前,他不考虑民主政治,而是商讨易遭罢免、暴动与暗杀的独裁政治。如同罗马共和时代一般,他暗示自己将成为一个好的独裁者。有时他认为政府应受有财产的人驾驭,因其与公共福利有最大的利害关系。他认为财富集中为自然,但他建议用倡导奢侈、罪恶、饥饿及需要的神权抵消它。“只要还有人缺乏民生必需品,无任何剩余可合法属于他们……大多数教会财富应分配给穷人,并在各地设立免费公共学校”,“社会亏欠那些没有财产者,工作简直没法满足他们所需的固定维持生活之物,没有供吃饭、住宿与穿衣所需的金钱,没有照料疾病及年老者与抚养孩童的设备。那些财富必须供给那些缺乏生活必需品者”,否则穷人有权以武力取得任何他们所需的。
大多数会议代表不信任且害怕马拉,但是与他共同生活的无套裤汉,因他的哲理而宽恕他的过失,他被警察搜捕时,他们冒险隐藏他。他必然有一些可爱的德行,以致他的情妇挚爱地伴随他,直至他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