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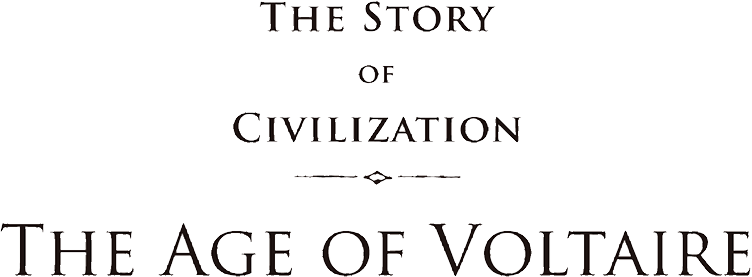
在谈到大卫·休谟之前,我们先要谈两个小人物。
伯纳德·曼德维尔是出生于荷兰的法裔伦敦医生,1705年发行6便士的10页打油诗小册子《嗡嗡不满的蜂群》(Grumbling Hive)。它的主题是似非而是的隽语:蜂群的繁盛是由于各个蜜蜂的恶习所致——由于它们的自私贪婪、繁衍的狂迷和集体的好斗。将这种观点应用在人类的群体上,这位顽皮的医生说道,国家的富强不是依赖公民的美德,而是依赖喃喃埋怨的道德之士愚蠢地谴责的恶习。现在让我们想象,如果所有的贪得无厌、虚荣、阴险和好斗突然中止,那将会发生什么情形——如果男男女女只吃他们需要的食物,只穿足以御寒的衣服,绝不彼此欺骗或伤害,绝不争吵,总是清偿债务,谴责奢侈浪费,而且忠于他们的配偶,则整个社会立刻会停顿下来:律师将会饿死,法官将无法审理案件或受贿,医生将因没有病人而消瘦,葡萄园主人将破产,酒店将因没有酒徒而倒闭,制造精美食品、装饰品、衣服或住屋的几百万技工将失业,没有人愿意当兵。不久,这个社会将被征服和奴役。
《嗡嗡不满的蜂群》的打油诗体例使它没有影响力。这位虚荣心强、贪得无厌、好斗的医生大为不平,他在1714年再度出版这本小册子。1723年又出版《蜜蜂的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一再增添序言、注释和评论,将10页的篇幅增为两册。这一回英国和法国都注意了,因为这些附注构成有史以来对人性分析最锐利的著作之一。
曼德维尔实际是以沙夫兹伯里第三伯爵为他的抗拒对象,因为这位伯爵以乐观的辩才来解说人性,还假定人类具有内在的“是非观念……像自然的情感一样是我们天生的,也是我们人身的首要原则”。曼德维尔答道,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在教育和道德训练之前,人性没有美德和恶习之分,只独受自私自利的支配。他同意神学家所说人类天生“邪恶”(不法)的说法,但不用地狱来威胁人类,他夸赞他们聪明地把个人恶习用到社会公益上。因此私娼保障了公众的贞操;贪求产品和服务刺激了发明,支持了制造和贸易;而大笔财富使博爱主义和宏伟的艺术成为可能。神学家宣扬严苛,曼德维尔则为奢华辩护,而且辩称,对奢侈品的欲望是工业和文明的根基;除掉所有的奢侈品,我们将再度成为野蛮人。卫道士要谴责战争时,曼德维尔说,一个国家得以生存是靠发动战争的能力,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是吃人的猛兽。
他看不出自然有任何道德可言。好坏是适用于人类的社会或反社会行为的字眼,但大自然本身并不注意我们的字眼或训诫。他认为美德是任何求生存的能力,而依我们存有偏见的解释,自然世界是贪婪、欲望、残酷、屠杀和无谓浪费的场面。但曼德维尔认为,在那个可怕的斗争之外,人类也有进化的语言、社会组织和道德规范,作为社会凝聚和集体生存的工具。自然并不必含褒贬,但以其诉诸人类的虚荣、畏惧和荣耀,可以正当地用以鼓励别人做出有利于我们自己或团体的行动方式。
几乎每个听过曼德维尔谈话的人,都斥责他是一个喜欢冷嘲热讽的唯物论者。然而,伏尔泰同意他关于奢侈有益的观点,而法国放任主义的重农主义者也赞扬他的观点,认为如果人类的贪婪听其自由发挥,工业的巨轮将嗡嗡转动。这位古怪的医生或许会承认,他那“个人的恶习是公共的利益”这一反论大体上是定义太过松散的文字游戏。像贪得无厌、好色、好斗、骄傲等“恶习”,在最初的生存斗争中一度是“美德”。它们只有在超出社会的利益下才会变成恶习,倘若通过教育、舆论、宗教和法律的控制,则可成为公众利益。
哈奇森跟这位恶名昭彰的医生截然不同。生在爱尔兰一位长老会牧师家中,他在都柏林开设了一所私立学院。在那里,意识到将无知的年轻人转变为公民这一职责,他写了一本《论道德的善恶》(Inquiry concerning Moral Good and Evil,1725年)。在文中,他认为一个好公民是促进公众利益的人,他形容公众利益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升为格拉斯哥大学伦理学教授后,由于维护个人的判断权利、快乐的合法性及“音乐、雕刻、绘画的创造性艺术,甚至男人的游戏”,而困扰了长老教会。他没有曼德维尔对人性的悲观论调。他承认人的错误和罪恶,他们狂热的情欲和暴烈的罪恶,“但他们生命最伟大的部分也应用在自然感情、友谊、天真的自爱或国家爱的职分之中”。他给历史学家增加了一个有益的警告:
人们往往将他们的想象力耗费在他们曾经听到过或在历史上读到过的抢劫、谋杀、剽窃、伪证、舞弊、大屠杀和刺杀事件上,因此断定所有的人类都很邪恶,就好像一个司法法庭是估量人类道德的适当场所,或是通过医院诊断一般趋势健全与否。他们难道不该想想任何国家中的诚实市民和农民的人数远超过各种罪犯的人数……与无辜或善良的行为相比,犯罪行为正因罕有,因而引起我们注意,并在历史中予以记载。那些多得不可胜数的诚实与慷慨的行为,只因其如此寻常,因而遭到疏忽。这如同在一个健康而安全的漫长生命中,一个大的危险或一个月的病痛将成为经常提到的故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