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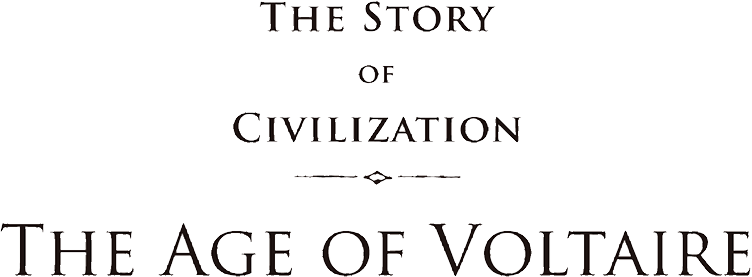
苏格兰的命运和爱尔兰的命运何以大不相同?
苏格兰从未被人征服过;相反,它曾给英格兰人一位苏格兰籍的国王。它的高地民族首领仍然未被征服,他们提供了一再领导苏格兰侵略英格兰的战斗部队。它的低地家系是盎格鲁—撒克逊族,基本上和英格兰人是同一个血统。它的土地仍然在勇敢的当地人民手中。它的宗教和英国国教一样,是宗教改革的产物,不是中世纪教会的遗产,同时它团结而非分化了整个民族。在合并法案(1707年)之后,苏格兰根据人口的比例分享目前不列颠——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国会的议席。它接受来自伦敦的统治,不过这只是在勒索商业让步使苏格兰人致富之后。苏格兰的每个教区都设法为其子弟设立一所学校,同时有4所大学提供当时不列颠群岛最好的高等教育。在18世纪,这种教育活动兴盛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Scotish Enlightenment)——休谟、哈奇森(Hutcheson)、里德(Reid)、罗伯逊、亚当·斯密——因而带动英国人的心灵向前迈进。
然而,辉煌的成就必须付出艰辛,在合并的果实成熟之前,已经度过了50年的光阴。1714年的苏格兰基本上仍是封建的,在城市之外,每个地区都由一位高高在上的贵族通过属下的地主治理,土地由忠心耿耿而目不识丁的佃农耕作。但现在和英格兰的政治合并迅速地破坏了那种结构。贵族支配着苏格兰的国会。当苏格兰国会解散时,不列颠国会的苏格兰籍议员发现他们置身在一个贸易、工业的影响力和土地的势力互争长短的环境中。他们采纳了英格兰的观念和技术。1750年,苏格兰的制造商和商人开始向阿盖尔、阿瑟、汉密尔顿和马尔诸家族的全国领导阶层挑战。1745年的拥护詹姆斯二世派事变是苏格兰封建势力闪出的最后一次火花,它失败后,苏格兰的经济与英格兰的经济合而为一,中产阶级的统治同时开始。这个合并使英格兰的殖民地开放给苏格兰人。1718年,第一艘苏格兰船只自格拉斯哥横渡大西洋。不久,苏格兰商人变得到处都是。农业技术和都市卫生有了改进。死亡率降低,人口由1700年的100万人增至18世纪结束时的165.2万人。拥有5万居民的爱丁堡,1751年成了大不列颠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伦敦和布里斯托。
长老教会(Presbyterian Kirk)仍然近乎狂热地效忠加尔文教派的神学。每个星期日,人们步行——有时两三英里路——到毫无装饰的教堂,聆听几个小时强调宿命论和地狱恐怖的讲道和祈祷。《圣经》是每个苏格兰家庭每天的精神食粮。1763年,休谟以戏谑夸张的口吻估计道,苏格兰境内每个男女老幼都有两本《圣经》。传教士的教育程度不高,但诚挚而虔敬感人,他们生活俭朴,他们的言传身教加强了苏格兰人特有的坚定和诚笃。每个教会的长老和牧师严格地监视教区民众的言行,他们分别对赌咒、诽谤、争吵、巫术、乱伦、通奸、任何不守安息日规定、任何违背他们严厉教规的行为加以处罚。牧师们谴责跳舞、婚宴和看戏。他们仍然对巫术举行审判,虽然由于巫术而处死的情形已越来越难得一见。1727年,一对母女就因为这样的罪名被判刑,女儿逃了,但母亲被烧死在柏油筒里。英国国会废除规定巫术处死的法律时(1736年),苏格兰的长老教会抨击这项行动违反《圣经》的昭然戒律。
同时,长老教会学校由教区维持,城镇学校由城镇维持,培育准备升大学的学生。各个阶层渴望求知的年轻人来到爱丁堡、阿伯丁、圣安德鲁和格拉斯哥。他们来自农村和工厂,也来自地主和贵族之家。一种求知的热诚激发他们,他们忍受了求知过程中任何的艰难。他们有许多人住在寒冷的阁楼里,以定期由父亲农庄运来的一袋燕麦片作为主食。教授们也都清心寡欲,年收入很少有超过60英镑的。在大学里神学是课程的核心,比教区学校几无不及,同时也教古典文学,还有一点科学的课程;苏格兰人的心灵接触到了欧洲的世俗思想。在格拉斯哥教伦理学(1729—1746年)的哈奇森,撇开教义的讨论不提,将他的伦理学建基于自然的基础上。一位苏格兰作者曾于1714年提道:“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在我们年轻的一代和学生中间大受欢迎。”少数陶醉于解放的年轻人组织了俱乐部——“硫黄社”“地狱火”“龙骑兵”——自豪地宣扬无神论,或许他们已和拥护詹姆斯二世派的不满分子混在一起。因为除了那些和英格兰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商人阶级外,苏格兰仍然对斯图亚特王朝的记忆激动不已,而且梦想詹姆斯三世或他的儿子再度领导苏格兰人越过边界,使苏格兰王朝坐上不列颠王位这一时刻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