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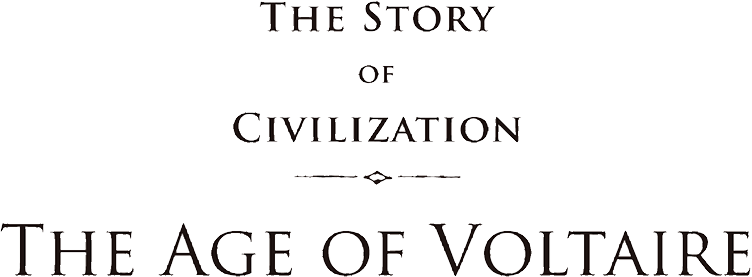
在历史上很少有像爱尔兰这样受到压制的民族。由于英格兰军队一再成功地镇压当地人民的叛乱,束缚爱尔兰人肉体和灵魂的一项法律制定了。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只有一小批天主教地主留有一部分土地,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在对待农工有如奴隶的新教徒手中。查斯特菲尔德说:“爱尔兰可怜的人民遭到他们主人奴役的情形比黑人还糟。”莱基(Lecky)说:“大地主们在寓所中有固定的监狱,用以立刻惩罚卑贱阶级的人,这在爱尔兰并非罕见的事。”许多地主居住在英格兰,并在那里花费掉(斯威夫特估计)爱尔兰佃户缴纳的2/3的地租。这些佃农——负担着交给地主的佃租,付给他们痛恨的英国国教的什一税和付给自己的传教士的费用——居住在屋顶漏雨的泥造小屋里,衣不蔽体,还经常处于饥饿的边缘。斯威夫特认为:“爱尔兰佃农的生活比英国的乞丐还凄惨。”那些停留在爱尔兰的地主和身在外地的地主代理人,以佳肴美酒的狂欢宴会、奢华的款待、争吵和决斗及豪赌来麻醉自己,而对周围的野蛮状态和敌意视若无睹。
全面控制爱尔兰之后,英国国会压制任何与英格兰竞争的爱尔兰企业。我们曾在别处看到一项1699年的法案如何禁止爱尔兰毛织品输往任何国家,以摧毁成长中的毛织品制造业。以同样的方式,爱尔兰在政治混乱和军事蹂躏期间保存下来的外国毛织品贸易,也被英国法律无情地扼杀了。爱尔兰的输出品须上交出口税,这一措施使它们除了英格兰外几乎断绝了所有的市场。许多爱尔兰人靠饲养家畜并将它们输往英格兰维生。1665年和1680年的法律禁止英格兰人进口爱尔兰的牛、羊或猪及牛肉、羊肉、咸肉和猪肉,乃至奶油或干酪。爱尔兰曾经将其产品输往英国的殖民地。1663年的一项法案规定,除了少数的例外,除非由配置英格兰船员的英格兰船只从英格兰载运,欧洲的货品不得输往英国殖民地。爱尔兰的商船队无法生存了。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受到英国为爱尔兰子民制定的法律的困扰。在一个有名的例子中,他们加入天主教徒推翻英国政府的运动。上交给身在外地的地主的租金不断外流,以致1722年造成爱尔兰硬币缺乏的情形。华尔波尔建议发行铜币以消弭这种情形。计划是合理的,但仍染上习见的贪污。肯德尔公爵夫人获得铸造这种新硬币的专利权,她以1万英镑的价格把专利权卖给制铁业者伍德。为了筹措这笔款项再加上他的利润,伍德建议铸造10.08万英镑的半便士或1/4便士的铜币。由于当时爱尔兰金属货币总额只有40万英镑,爱尔兰人提出了抗议,认为在付款和找换零钱上必须使用铜币,而外国的账目,包括身在外地地主的佃租,则以银币或纸币支付。不值钱的硬币将驱使良币囤积或外流,那时除了令人困扰的铜币外,爱尔兰人将别无他物作为货币。为了消除这些抱怨,英国政府同意将新币的发行数额减少到4万英镑,还提出铸币大师伊萨克·牛顿的一份报告:伍德的半便士硬币的金属成分和专利要求的一样好,而且比过去留传下来的硬币好得多。
这时,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主教斯威夫特以德拉皮耶(M.B.Drapier)为笔名发表一连串书简加入辩论的行列。他以热烈的精神和谩骂的手法,抨击新的货币是一项欺骗爱尔兰人的企图。他坚称送给伊萨克·牛顿检验的铜币是特别铸造的,伍德绝大多数的半便士硬币的价值远不及它们的面额。确实有些经济学家证实了他的说法,他们估计,照最初的计划发行这种硬币,爱尔兰将遭受60480镑的损失。在第四篇书简中,斯威夫特进一步强有力地指控英国在爱尔兰境内的一切统治,而且下了“所有未经被治者同意的政府就是奴隶制度”的定义。爱尔兰人,包括其中大多数的新教徒,热切地回应这个大胆的注释。街头唱出力促反抗英格兰的歌谣,几个世纪来蔑视整个民族的英国政府,现在发现它在一支秃笔面前退缩不前。它悬赏300英镑捉拿这位作者,虽然有几百个人晓得作者是当地那位郁闷的主教,却没有一个人敢对他采取行动,也没有任何一个爱尔兰人敢接受这种新硬币而面对人们的愤怒。华尔波尔承认失败,取消新币的发行,并付给伍德2.4万英镑,以赔偿他徒劳无功的开销和化为幻影的收获。
爱尔兰的政治结构使任何反抗英格兰统治的行动不可能实现,除非是群众的暴动或个人的暴力。除非皈依英国国教,没有人能够服膺公职,因此爱尔兰国会自1692年后,完全是由新教徒组成的,现在也已完全顺从了英国。1719年,英格兰国会重申其对爱尔兰立法至高无上的权利。在英国保障议会或个人自由的法律,像《人身保障法》(Habeas Corpus Act)和《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并不扩及爱尔兰,在英国享有的报业相对的自由也并不存在于爱尔兰。这两个议会只有在他们的选举人和议员的贪污腐败上彼此相似。英国国教主教在爱尔兰上院具有主宰力,这点却大不相同。
爱尔兰境内的英国国教,包括约占总人口1/7的信徒,国教靠取自农民的什一税维持,而农民几乎全是天主教徒。一小部分爱尔兰人信奉长老教会或其他非国教派,他们获得少许的宽容,但没有适任公职的资格。天主教徒不仅被摒弃于公职外,而且被排除于几乎一切需要学问的职业外,及几乎每个接受高等教育、获得财富或权势的机会之外。他们不得购买土地或以土地作为抵押投资,或持有任何长期或有价值的租约。除非是在找不到新教徒的地方,否则他们不能担任陪审员。他们也不能在学校教书,不能投票选举市政府或全国性的公职人员,或合法地与新教徒通婚。他们可以保有宗教信仰,但须由政府立案,而且做弃国宣誓(Oath of Abjuration),由不再效忠斯图亚特王朝的传教士主持仪式。其他的传教士动辄遭到监禁,但在1725年后,这项法令很少执行。1732年,爱尔兰国会一个委员会报告,爱尔兰境内有1445名传教士、229座天主教堂、549所天主教学校。1753年后,英国人的热情减弱了,爱尔兰境内天主教徒的处境获得改善。
宗教生活的杂乱、人民的穷困及社会进步的无望使爱尔兰人道德风气败坏。最能干和最勇敢的天主教徒——他们将会提高爱尔兰人能力、道德和知识的水准——纷纷迁往法国、西班牙或美洲。许多爱尔兰人为了免于饥饿而沦为乞丐或罪犯。盗匪集团藏匿在乡间,走私者和掠夺难船者潜伏在海岸附近,而有些拥有财产的人雇用多达80名的刺客干他们无法无天的勾当。数以千计的牛羊被流浪的游民宰杀,显然这是天主教徒报复信奉新教地主的行动。由于爱尔兰国会经常说占总人口3/4的天主教徒是“公敌”,人们实在难以尊重国会通过的法律。
爱尔兰人的生活也有较光明的一面。人们欢乐、逍遥自在、爱笑的性情历经一切艰难仍然存在。他们的迷信和传说使他们生活在神秘和诗意中,而没有导致像苏格兰和德国境内以巫术迫害为特征的暴动。爱尔兰境内的英国国教教士包括一些杰出的学者,及18世纪最初的25年中最伟大的英文作家,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主教斯威夫特。1731年创立的都柏林学会(Dublin Society)努力改进农业和工业的技术,刺激发明,并鼓励艺术。新教徒个人协助穷困的天主教徒,法官宽大处理触犯刑法中的严峻条文的囚徒,其例自不在少数。
但大致说来,爱尔兰的情况是历史上可耻的一页。可耻的穷困、无法无天、流浪的贫民、3.4万名乞丐、无数的窃贼、上层阶级生活在花天酒地之中而农民食不果腹、每一次作物歉收都带来广泛的饥荒——斯威夫特说:“年老和患病的人由于寒冷、饥馑、不洁和寄生虫而垂死、腐烂。”——这幕恐怖的景象必然在我们对人的概念中占有一席之地。在1739年长期的严寒之后,发生了1740年至1741年严重的饥荒。根据一项估计,有20%的人丧失了生命,从而留下许多荒无人烟的村庄。在克立郡,纳税人总数由1733年的14346人减到1744年的9372人。贝克莱估计:“爱尔兰可能无法在一个世纪内复原。”他的估计错了。妇女们耐心地生育子女以填补死去的人。随着教育的普及,新教徒的宗教热诚减退了,天主教徒的宗教虔诚则随着他们的宗教与这个民族争取自由的奋斗而加强。天主教赞成高的生育率,作为她对抗一切反对派的秘密武器,这迅速抵消了饥荒、时疫和战争对人口的掠夺。1750年,爱尔兰的人口由1700年将近200万的数目增加到约237万。到头来,被压迫者的信念和多产击败了征服者的武力和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