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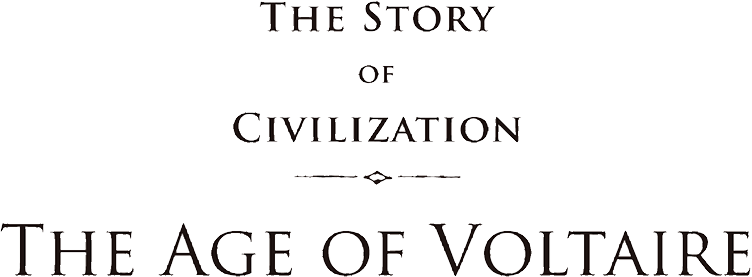
这个时期的英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初生婴儿的死亡率相当高。出生于伦敦的儿童中,59%在5岁以前夭折,64%在10岁以前夭折。许多婴儿出生后即遭遗弃,幸存的婴儿则依赖公款养活,然后被送往习艺所工作。助产妇和母亲的疏忽,造成大量儿童的身体残废。
出身贫穷家庭的儿童,可能无法接受任何学校教育。虽然有免费提供男女儿童初等教育的“慈善学校”,但1759年的在校总人数只有2.8万名,“慈善学校”不接收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仅很少的农家子弟和几近于零的都市贫民才有机会就读。一位英国权威人士说:“大部分英国人没有受过教育就走进坟墓。”就工匠阶层而言,学徒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中产阶级的儿童可以就读私立学校,这些私立学校是由“失败、破产或从其他行业溃败的人”主持的。还有“贵妇学校”,付得起学费的男女学生,在卑微的女教师教导下,学习读书、写字、算术,接受许多的宗教教育。以上的学校教育都强调教导学生满足各人所处的社会阶层,而且对较高的阶层表示顺从。
少数人在毕业后可以进入“文法学校”就读,那里的教师从适度收入中可以衡量出自己在社会上的卑微地位。学生除读书写字和算术外,还可学习一点拉丁文和希腊文。文法学校的管教相当严格,上课时间也长——上午6点至11点半,下午1点至5点半。比文法学校素质更高的是“大学预备学校”,主要的公立学校有伊顿、威斯敏斯特、温切斯特、士鲁兹伯利、哈罗、拉格比等。经过挑选的青年可以进入大学,每年大约需缴26镑,他们的前途即在此地注上阶级的标签。由于这些大学预备学校仅收容信奉英国国教的子弟,浸信会、长老会、独立教派、唯一神教、教友派、公理教派、遁道宗等异派宗教分别创设学院,以教育他们的青年。他们的教育不特别强调希腊罗马的文学,而更注意当代语言、数学、历史、地理和航海术的传授,以适合中产阶级的需要。
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不得接受大学教育。大部分大学生来自富裕的家庭,但也有穷人子弟利用慈善家或慈善机构捐赠的奖学金读完大学,还有一些“工读生”和“公费生”,如牛顿,在阶级意识浓厚的课堂上,靠工读接受完教育。这一时期的牛津与剑桥,不论在课程、方法和思想方面都趋于保守,呈现一片呆滞不前的气氛。剑桥大学比较愿意减少古典文学和神学的分量,以扩大科学方面的研究,但查斯特菲尔德批评剑桥“沦入最卑微隐晦的境地”。牛津大学墨守旧神学的研究和依附崩溃的斯图亚特王朝,拒绝粗鲁的汉诺威君主前往访问。1745年,身为牛津学生的亚当·斯密说道,他在牛津所学无几。1752年在牛津就学的爱德华·吉本,公然指责牛津的教职员是一群不学无术的酒徒,后悔他在牛津浪费的时光。许多家庭宁愿自己聘请私人的家庭教师。
女孩子在乡下和慈善学校接受启蒙教育——读书、写字、缝纫、编织、纺纱、些微的算术,大多是宗教。有些女孩由家庭教师教导,少数如玛丽·蒙塔古夫人一样,私下研究古典语言和文学。玛丽·蒙塔古说:“我辈女人通常不准研究此类学问,愚蠢通常被认为是我们的本分,我们稍过愚蠢比充装能读一点书抑或懂得些许道理,更能及早受人宽谅……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一个有学问的女人更容易受到普遍的嘲笑。”她推想男人不让女人获得学问的理由,是要使男人不耗力便可以勾引到女人。倘使我们从英王情妇们的丰厚收益来做判断,女人的确不需要有古典文学的修养,也不需要罗马诗人奥维德的教导启示,就可以操纵自如,在情场上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