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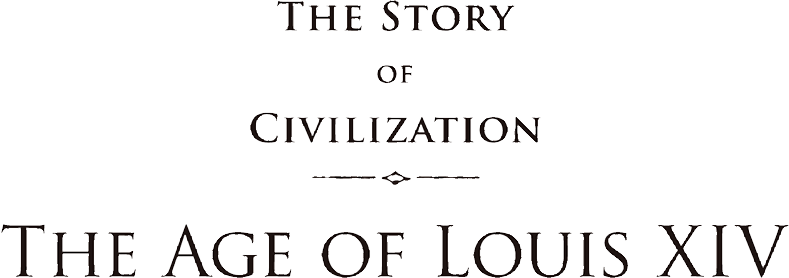
有一位沙普兰先生,在法兰西学院筹备时曾助过一臂之力。他被认为是那个时代(1595—1674年)最伟大的诗人。还有一位卢梭,他写的诗,人们都遗忘了,可是他写的刻薄的讽世警句,使他因人身诽谤罪,而被逐出法国(1712年)。差不多所有在政治上有地位的大人物,都写回忆录。我们提过雷斯、拉罗什富科的回忆录,以后还会提到圣西蒙的回忆录。除这三本以外,比较突出的回忆录是莫特维尔夫人写的三卷。她用令人着迷的平易语气,历述她在安妮王后的宫中服务22年的经过。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就是她赞同拉罗什富科的想法。“我曾经历过人们虚伪友谊带给我的许多痛苦,使我不得不相信,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正直’或‘一颗感恩的心’更加稀有。”她就是这种“稀有之物”之一。
拉布丁是比西地方的伯爵,写了一本《高卢民族爱情史》(Histoire Amoureuse des Gaules)。这是一本黑幕书,书中描写当时人物的丑闻,用古代高卢人物作掩饰。国王对他书中所写关于亨利埃塔夫人的双关语,十分愤怒,把他送到巴士底狱关了起来。一年后,将他放出,但前提是他必须退休,回到自己的领地。他在那里烦躁不安地度完了余年,也写了一本十分生动的《回忆录》。更不可采信的,是一本塔勒芒(Tallemant des Réaux)写的《逸事》(Historiettes),书中还画些恶意的小插图,画的是文艺界的名人或丑闻的主角。弗吕里(Claude Fleury)写了一本不昧良心的《教会历史》(Histoire Ecclésiastique,1691年)。蒂耶蒙(Sébastien de Tillemont)写了一本《皇家史》(Histoire des Empereurs,1690年后),还写了一本《公元六世纪前宗教史》(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des Six Premiers Siècle,1693年)。为写《宗教史》,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写得非常辛苦,但不知不觉地澄清了吉本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狂野、荒诞。
最后还有一位马克特(Charles de Marquetel),又叫圣埃夫勒蒙大公。他是态度最和蔼的“反灵魂不灭论者”(esprits forts)。他使天主教、胡格诺教派、耶稣会和詹森教派的人士都震惊了,因为他怀疑这四派最基本的信仰。他充满冒险的军旅生涯,使他几乎得到元帅的权杖。但他批评马扎然,又是富凯的好友,终于使他失去了宠信。知道自己上了被捕名单时,他逃到了荷兰,1662年,又到了英国。他的优美风度和怀疑论者的机智,使他成为伦敦奥尔唐斯·曼奇尼(Hortense Mancini)沙龙和查理二世宫中最受欢迎的人物。他和多克坎库尔(Maréchal d’Hocquincourt)一样,都是英王面前最令人愉快的聊天者之一。他最喜欢打仗,其次喜欢女人,第三才是哲学。他吸收了蒙田的轻松愉快,又和伽桑迪研究伊壁鸠鲁,他和那位邪恶的希腊哲学家同样下结论说:声色之娱是不错的,但求知的乐趣更好。不必考虑太多上帝的问题,因为上帝也不怎么关心人们。吃得好、写得妙,对于他来说是最合理的两件事。1666年,他又到荷兰,遇见了斯宾诺莎,对多神主义的犹太人过着虔诚的基督教生活有很深的印象。英国政府给他的资助金,加上他自己财产的剩余部分,他有余力写些不太著名的小品文,都是用飘逸自在的文笔写的。这种笔调,对伏尔泰的成名有一点影响。他写的《论阶级的不平等》,对孟德斯鸠有很大的帮助。他写给尼侬的书信,创造了法国人书信中特有的宁馨之气。58岁时,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意志不坚者:“如果没有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我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就是我研读这位名人作品得到的唯一益处。”他几乎和丰特内尔一样长寿,死于1703年,享年90岁。他还得到了法国人很难获得的特殊荣誉,即死后葬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
“9个世纪后,”腓特烈大帝写信给伏尔泰,“大家都会忙着翻译路易十四时代好作家的作品,就像我们现在翻译伯里克利和奥古斯都时代的作品一样。”早在路易十四去世前的好多年,很多法国人已经开始将他们那时的作品和古时最好的作品互相比较了。1687年,查理·佩罗在法兰西学院,念了一篇叫《路易十四的伟大世纪》(“Le Siècle de Louis le Grand”)的文章。在该文中,他认为他那个时代的一切,早已超过了希腊或罗马时代的成就。佩罗认为布瓦洛也是当时超过前期同行们的伟大作家之一,但那位老批评家马上站起来表示,古时的成就比较伟大。他还告诉学院中的人,听佩罗这种无聊的论调真是可耻。拉辛为了缓和二人的冲突,只好假设佩罗是在开玩笑。佩罗却认为,他是站在有利的一面。1688年,他重新奋斗,参加了“今古平等运动”(Parallèles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那是一段持续时间较长却有趣味的口头辩论。他认为当时的建筑、绘画、演说术——除了《埃涅阿斯纪》等叙事诗外——都比古代好。丰特内尔非常高兴地支持他的论点,但拉布吕耶尔、拉封丹、费奈隆和布瓦洛站在另一边。
这是一种健康的辩论,它结束了基督教及中古时期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理论,也否定了文艺复兴时期把古代的诗歌、哲学和艺术抬举得比什么都高的那种思想。一般来说,大家都赞成当时科学方面的成就,确实超过了希腊和罗马的任何时期,连布瓦洛也这么说。路易十四的宫廷中人,更迫不及待地承认,生活的艺术在马利或凡尔赛宫早已发展到史无前例的优美境地了。我们并不在这里假定可以代他们下结论,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等我们把同一时期全欧洲的情况完全了解了之后,再下结论也不迟。我们并不一定要相信高乃依比索福克勒斯好,拉辛在悲剧上的成就超过了欧里庇得斯,波舒哀的口才比德谟斯梯尼更动人,布瓦洛生动的文学连贺拉斯也自叹不如。我们更不敢把卢浮宫与万神殿互相比较,或把吉拉尔东和夸瑟沃克斯与菲狄亚斯和普拉克西特勒斯的雕刻术相比。但至少有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这种比较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而古人的成就并非是无人可以超越的。
伏尔泰称路易十四时代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开明的时代。他却没有想到,他的时代被人称为“启蒙时代”。我们必须修改一下他的颂文。那是一个反对开放、不容有异说的时代,由撤销民主的《南特诏书》一事便可看出。所谓“开明”只属少数不受朝廷欢迎或那些过度荒淫玩乐、为人不齿的人拥有的特权。那时,教育由教会控制,教的全是一些中古时代的教条。从没有人梦想过舆论自由,所谓自由只不过是一些有幕后人物保护的大胆言论。在黎塞留统治下的人,比路易十四时代的人更富于创造力和灵气,产生的天才人物更多。但路易十四时代,王室对文学和艺术方面的奖励、对文艺界人士的照顾,是之前任何时代或国家无法与之相比的。艺术和文学都达到最华美的地步,如卢浮宫的圆柱廊和拉辛的《安德洛玛刻》。但有时只是华而不实,凡尔赛宫的装潢和高乃依后来作品中的修辞学,都犯了这些毛病。而且,那时的悲剧和其他主要艺术,都有矫揉造作之感。他们太过于依赖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他们从那些古物中找材料,而不是从法国人的历史、信仰和特殊风俗中找题材。他们只表现出一些受过特殊教育的特殊社会阶级人士的状况,并不能代表一般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所以,在这么多光芒四射的显赫人物中,只有平民化的莫里哀和拉封丹在今天最受欢迎,因为他们忘记了希腊和罗马,只记得法国,在那个正统文学的时代,净化了语言,塑成了文学的模式,美化了谈话的内容,同时在推理中加入了感情,虽然也使法国和英国的诗变得冷淡乏味。
不管怎么说,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历史上,从没有一个统治者,以那么开明的态度对待科学、文学和艺术。路易十四迫害詹森教派信徒和新教徒,但在他统治下,帕斯卡写作,波舒哀证道,费奈隆教书。他把艺术当作政治手段和荣誉的一部分,在他的庇荫下,法国有了最伟大的建筑、雕刻和绘画。他帮助莫里哀对付一大堆反对他的人。他支持拉辛写完一个悲剧又一个悲剧。法国从未有过这么好的剧本、这么优美的书信和散文。国王的好风度、他的自我克制能力、他的耐心、他对女性的尊敬,使法国宫廷内外人士都养成彬彬有礼的优雅风度。这种风度流传到巴黎和全国,继而全欧洲。他错用了几个女人,但在他的统治之下,女性在文学和生活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因此使法国在文化上有一个可爱的特点,就是男女都有发展的机会,那是世界上别的国家所没有的。尽管那么多有才干人物被剥夺了风采以至才华没有充分发挥,我们还是可以和法国人一起宣布,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和伯里克利时的希腊、奥古斯都时的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伊丽莎白—詹姆士一世时代的英国一样,都达到了人类弧线上令人震颤的最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