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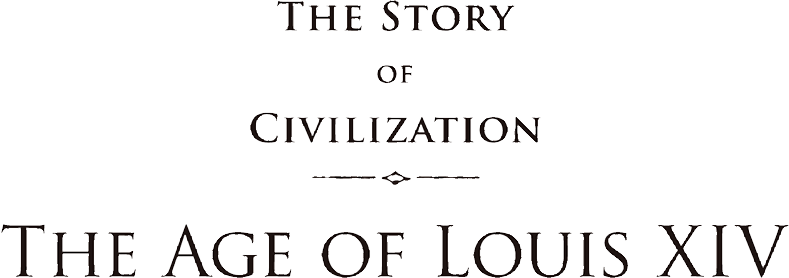
还有10卷作品,从那个时代一直流传到现在,也是由一位女士写的。玛丽·尚塔尔(Marie de Rabutin Chantal)女士,童年时代双亲就过世了,继承了很大的一笔遗产。法国人中头脑最好的几个联合起来,完成了她的教育。法国最高尚的几个家庭指导她学会了生活的艺术。18岁时,她嫁给塞维涅侯爵。但塞维涅先生是一位调情圣手,只爱她的钱,并不爱她,将她财产的一大部分浪费在他的情妇身上。有一次,为了某个情妇与人决斗,不幸失败身亡(1651年)。玛丽尝试着把他忘记,可是,她一直没有再嫁。她将全部心血花在养育她的一对儿女身上。也许,正如她那讨厌的表兄拉布丁(Bussy Rabutin)形容的,她是一个“冷酷的”女人。也许,她发觉到,如果母爱充分发挥了,性爱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她的每封信都充满了快乐与生趣,而且几乎都与母爱有关。
她热爱社会的程度与她不信任婚姻的程度一样深。作为一个拥有53万利维尔财产的富孀,她当然拥有不少追求者,蒂雷纳·罗昂、比西……她不认为应该从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做终身伴侣,而把其余的赶走。但终其一身,从无任何桃色新闻,或她与哪个男人有暧昧关系的谣言玷辱她的名声。朋友们用毫不猜疑的情感热爱着她。她的朋友有雷斯、拉罗什富科、拉法耶特夫人、富凯等人。前两人不得进入宫廷,因为他们参加了投石党。最后那个,因为有些来源不明的财富,也不许进宫。塞维涅夫人对他们四人忠实而友善,教会因此也不太欢迎她。《爱丝苔尔》一剧在圣西尔上演时,国王曾对她说了一些客气、赞美的话。除朝廷外,许多团体都欢迎她参加,因为她具有一切有教养的女性应有的风度与仪表。她的谈吐和她的文章一样生动有趣,这和我们平常夸奖人的方式有些不同,因为我们常听到的话是:某人会不顾一切把想要说的话写出来,谈话时却十分谨慎。
在她如今存留的1500多封信中,大多都是写给她女儿弗朗西丝·玛格丽特(Françoise Marguerite)的。她女儿于1669年嫁给格里南(Grignan)伯爵,随丈夫搬去普罗旺斯省居住,她丈夫担任副省长的职务。1671年至1690年,几乎每次邮差送信到她女儿家中时,都有一封母亲写给女儿的信,甚至一天有两封。她对女儿说:“我写给你的这些信,是我最大的财富,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乐趣。任何其他事情,和这事一比,都无足轻重了。”她把不能给予男人的爱,全部变成了对女儿的溺爱,连女儿自己都觉得不配。弗朗西丝是一位很保守的女士,她不懂得怎样用热情的言语来表达她心中的感情。她有丈夫和孩子们要照顾。她有时也会不耐烦,也有忧虑。可是,有25年之久,她每星期写两封信给母亲,除了生病之外,几乎从未间断过。这位快乐的母亲,有时会担心,写信是否浪费了女儿太多的时间。
这些信中最感人的一件事,是格里南伯爵夫人的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及后来被送进修女院与世隔绝的情形。为了使母亲便于照顾她,伯爵夫人到巴黎生产。孩子出生后,她马上向丈夫致歉,因为生了一个女儿,必须辛辛苦苦地教养成人,长大后还得花大笔金钱陪嫁,出嫁后,就失去了她。产后不久,她离开巴黎回到普罗旺斯去,暂时把女儿玛丽·布兰切留在兴奋的外祖母身边。塞维涅夫人写信给女婿说:“假使你想要个儿子,努力生一个吧!”她写信给那对不领情的父母,详细地告诉他们,那个他们不愿拥有的女儿,在成长过程中一切令人欣喜的细节:
你们的小女儿越来越可爱了……肌肤雪白,银铃般的笑声不绝于耳……她的相貌,她的嗓子,她身上的每一部分,都美妙极了。她懂得做100种小动作:牙牙学语,打人,画一个十字,请人原谅,鞠躬,亲自己的小手,耸肩,跳舞,拍马屁,摸人的下巴……我跟她在一起玩时,她可以给我好几个小时的欢乐。
外祖母必须把小胖外孙女送回普罗旺斯时,曾流了不少眼泪。后来,她的父母在她不到5岁大时,就把她送到一家修女院,塞维涅夫人更是伤心欲绝。这个孩子从未离开过修女院,15岁时正式宣誓成为修女,从此与世隔绝。
副省长是一个极度奢侈的人,喜爱宴游,经常入不敷出。他的太太隔一段时期就写信告诉母亲,他们快要破产了。母亲总是带着爱心责备他们,也必定接济他们一大笔钱。“一个拥有这么多金银珠宝、豪华家具的人,怎么居然会生活得像那些极端贫穷的人一样。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真是天晓得。”寄了这么多钱给女儿,为了维持自己的财富,塞维涅夫人只好辛辛苦苦地下乡到布列塔尼省的罗契村,那里有她的产业。她亲自察看那些财产是否被人好好地照顾保管。“产业出租的收入,除了一小部分被人吞没外,大多数都到达她手中。”她经常到乡下,使她在旷野里、森林中及布列塔尼地方的农民生活里,找到许许多多新的乐趣。她在信中对乡村生活的描述,也和对巴黎形形色色的描写一样生动有趣。这些事情,一周两次,像新闻简报一样送到她女儿那里。
她的儿子查理是另一个令她头痛的问题。她很喜欢他,因为他本性善良。她写道,他是“机智和幽默的源泉……他过去常念几段拉伯雷的幽默的短文给我们听,使我们笑痛了肚皮”。查理是一个模范儿子,只是他继承了父亲的习性,一个情妇又一个情妇,直到有一天——还是让我们看看夫人写给女儿的一封信,其中已非常明白地说出,当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告诉你一件有关你弟弟的事……昨天,他对我说,有一件可怕的意外发生在他身上。他和一个女人曾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可是到了紧要关头——就有点奇怪了。那个可怜的女孩,可能一生之中从未有过如此美好的经验。而我们的这位勇士,惨败而归,认为自己可能中了女巫的毒。更好玩的是,他说,他如不亲口把这事告诉我,他心中会感到十分不安。我取笑了他一番,并告诉他,以这种方式来惩罚他的恶行,真使我高兴极了……这真是给莫里哀编剧的一个好题材。
她儿子得了梅毒,她痛责他,但也细心地照料他。她曾试着灌输一些宗教思想给儿子,但她自己对这方面知道得太少,也没有什么可教给他的。她听了布尔达卢牧师的布道后,十分感动,心中也一度燃起圣灵的火花。可是,她看到宗教的游行行列经过住宅区时,受到那么热烈的欢迎,又觉得不值一笑。她常读阿诺德、尼科尔、帕斯卡等人的作品,她也同情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可是,她讨厌信教的人致力于使自己不受诅咒的那一套,因为她永远无法相信有地狱这种地方存在。一般来说,她避免想太严肃的事,因为那些不是一个女人该想的,又打扰了她平静安宁的生活。不过,她的阅读能力是最优秀的。她可以读维吉尔、塔西佗、圣奥古斯丁的拉丁文作品,蒙田的法文作品,她对高乃依和拉辛的剧本了如指掌。而她的幽默感比莫里哀更真诚、更令人愉悦。听听她讲的一个心不在焉的朋友的故事:
白仑卡有一天在街上走路,不小心掉到沟里去了。他十分安闲自在,对那些纷纷跑来援助他的人说:有什么事,需要我效劳吗?他的眼镜摔破了。如果不是他的运气比他的机智好一点的话,头也一样会破的。但发生的这一切都不能打断他的沉思默想。今天早上,我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他摔了一跤,而且几乎折断了脖子。我猜他大概是巴黎唯一不知道这事的人。
总而言之,这些信,在所有文学作品中,最能真实地表现出一个人的一切。塞维涅夫人毫不掩饰地,按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写出她犯的错误和她的美德。她是一个热爱子女的母亲,在巴黎的家中、在法国首府的沙龙中、在布列塔尼省的乡村,她写了一封又一封信给她女儿。她告诉女儿巴黎贵族社会中最新的闲言闲语,同时也告诉她“夜莺、杜鹃还有八哥儿已开始在春天的树林中歌唱了”。她有成百上千的朋友,老是打扰她完成2000页的作品,但她从不说他们一句坏话。她随时准备帮助别人,注意修饰自己的言谈,以便能适度地恭维别人,又不失礼。偶尔,她也会因为太高兴了而不知不觉地犯些小错。她同情不幸的人,也原谅她那个时代、那个阶层的人们不道德的行为。事实上,她自己的言行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她是一个神采飞扬的女人,不厌其烦地劝人为善,告诉大家“生存的乐趣”。她谦虚地说,自己不够资格出版一本书,可她是在法国文学巅峰时代里写出最优美法文作品的作家。
她有没有想到要出版她写的信呢?有时她也使自己沉湎在修辞学的梦里,好像嗅到了印刷机的油墨味。可是她的信中很多都写的是生活上的琐事,是过度亲昵的私人感情,有时也揭发了社会上某些有碍观瞻的事件。这些事,她都不太愿意公开让大家知道。她知道,她女儿把这些信件给友人们传阅,这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种风气。因为在那个时代,书信是住得距离较远的朋友们唯一交换消息的方式。她的另外一个外孙女保琳,她极力设法不让她和姐姐玛丽·布兰切一样进入修女院,继承并保留了她的那些信件。这些信件一直到1726年,即塞维涅夫人死后30年才出版。现在,这些信是法国古典文学中的瑰宝,犹如一大把艳丽的花束,其香味随着时间的逝去越来越浓郁。
她的生命快到尽头时,她对宗教问题想得比较多了。她承认她惧怕死亡和末日的审判。布列塔尼多雾,巴黎多雨,她患了风湿症,丧失了生命的乐趣,也终于发现,她是不可能长生不死的:
我来到这世上,并非出于自愿,如今又必须要离去。这种事简直叫我无法忍受。我如何离去?……我何时离去?……每天我都在想这些事。我终于发现,死亡真是太可怕了。我恨生命,是因为生命逐渐走向死亡,而并不是因为其中有太多的刺,刺得人痛彻心扉。你也许会说,我希望永远活下去。绝对不是!不过假使你真要问我的意见,那么,我情愿死在我护士的臂弯里。唯有如此,才能除去我精神上的一切痛苦。也唯有如此,才可以确定地、轻易地,把天堂赐给我。
她说她恨生命,因为生命导致死亡,这是不对的。正确地说,是她恨死亡,因为她几乎享受了77年无忧无虑的生活。她忍受着病痛,越过整个法国(约400英里),抵达格里南,希望死在女儿身边。死亡来临时,她以一种连自己都感到惊讶的勇气来面对,因为有临终圣餐及希望自己能青史留名这件事安慰她。事实上,她的愿望的确是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