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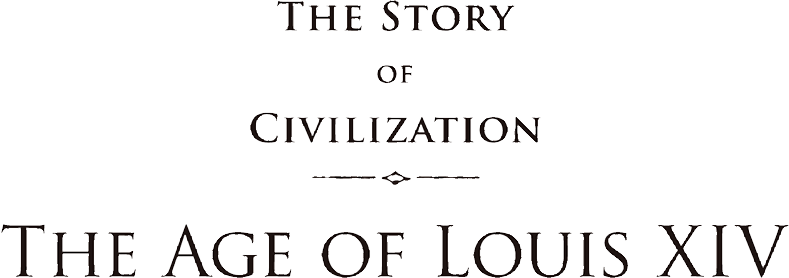
极端刺激的生活、肺痨、婚姻和亲人的丧亡,榨尽他生命的活力,莫里哀死时才50岁。米尼亚尔为他作的画像是在他的黄金时期:隆额、丰唇、喜剧性的昂眉,早现的额纹,沉思的眼神。他忙于剧务,周旋于跃跃欲试的贵妇群、活跃的妻子和敏感的国王中,眼看着三子有两子丧生——这不是走向乐观的坦途,而是病痛和早殇的大道。可以想象得到他变成了“自蚀的火山”,忧郁、躁急、率真地批评,但又富同情地宽容。他的剧团体谅他,对他忠心耿耿,明白他为剧团的生计和成就而鞠躬尽瘁。他的朋友随时准备为他卖命——尤其是布瓦洛和拉封丹,有时加上拉辛,和莫里哀四人为当时极有名的“四君子”。他们觉得他教养好、知识广、机敏但寡欢,在舞台上是一个明朗人物,私底下却比莎士比亚的耶克(Jaques)还抑郁。
经过四年半的分居,他与太太重聚(1671年)。他们重拾旧欢后所生的孩子,只活了一个月就夭折了。在欧特伊,他遵照医生嘱咐只喝牛奶,现在他恢复猛饮,为取悦太太常很晚进食。他无视日益严重的咳嗽,在最后一出戏《病态形象》(Le Malade Imaginaire)中,扮演主角阿甘(Argan,1673年2月10日)。
阿甘怀疑自己患上12种病,把半数资财都花在请医生和吃药上。他的兄弟巴拉尔(Béralde)嘲笑他:
阿甘: 我们病了该怎么办?
巴拉尔: 哥哥,什么事都别做……我们只要安静下来。天意,我们不打扰她时,自然会让她引起的骚动复归于常轨。都是我们的忘恩、急躁把一切都破坏了。何况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药石。
为了深一层嘲弄医生这一行,阿甘听说他自己在短期的安排下,可以成为大夫,可以轻易地通过考试,取得医生执照。该剧由此而写下了一段老少皆知的嬉闹式考试对白。
莫里哀的死几乎也是戏中的一部分。1673年2月17日,阿蒙蒂和一些朋友察觉到他的疲惫,求他歇业几天,以恢复元气。但他说:“我怎能那样做?这里的50位穷演员是按日计酬的,如果我们不演,他们怎么办?只要我还能演戏,而一日不给他们面包,我都会责备我的疏忽。”最后一幕,莫里哀,即剧中的阿甘(他两次装死),念到“我发誓”,正宣誓为医生,开始痉挛性地咳嗽。他装笑掩饰过去,把戏演完。他妻子和年轻的医生米歇尔·巴伦(Michel Baron)急速送他回家。他要一位牧师,但没人来。咳嗽越来越严重,最后血管破裂,血块哽住喉咙而死。
巴黎主教尚瓦隆下令,莫里哀没做临终忏悔,未得赦罪,不得埋于教地。阿蒙蒂纵使欺骗莫里哀时,也始终爱他,她到凡尔赛国王御前,虽不聪明,鲁莽,然而真诚地说:“如果我丈夫是罪人,他的罪也是陛下亲自认可的。”路易给主教下了一道密令,主教妥协了。灵柩不能移进教堂行基督教仪式,但允许在黄昏日落安静地埋在蒙马特大道的圣约瑟墓园的角隅。
一般人都认为,莫里哀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却不是由于戏剧技巧的完美,也非诗句的华丽。几乎所有戏中的情节都是引用别人的故事,结局也都造作牵强、离奇不经;所有的角色都个人化,有些像阿巴贡,夸张几近于滑稽的地步;他的喜剧又常常沦为闹剧。但我们都知道,朝廷和大众都喜欢他的闹剧,不能接受他对一般毛病的尖厉的讽刺。如非为了维持他的剧团,他很可能会省去闹剧。
就如莎士比亚悼念的,他必须身为大众的丑角。莫里哀写道:“在一般艺术中,对牛弹琴,听任蠢人的评判是一件苦刑。”他烦透了要时时让观众笑口常开,为此,他借剧中一个角色说:“……这是一桩古怪的事业。”他有雄心撰写悲剧,虽没达到预期目标,但他使他最伟大的喜剧渗入悲剧的意义和深度。
这是他剧中的哲学,人情味和锐利的讽刺使每一位识字的法国人都读他的作品。它主要是理性派的哲学,这使18世纪的哲学家大为开心。“莫里哀没有丝毫超自然的基督教义”,《伪君子》剧中“宗教的发言人的解释‘可能被伏尔泰认可’”。他从不妄评基督教的信条,他承认宗教在无数的生活中有裨益,他尊敬虔诚的信仰,但他严责在日常自私上加上一层礼拜日仪式的表面虔诚。
他的道德哲学在意义上是异端的,享乐合法,无罪恶感。那是更具伊壁鸠鲁和塞涅卡的风味,而少圣保罗和奥古斯丁的格调;更适于国王的放纵,而无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大胆。他驳斥德行的过分,赞美通达人情之辈,他们在荒谬的世界上睿智稳健地走他们的路,并使自己不受染于浊世。
莫里哀自己没达到中庸境界,身负喜剧作家的职业,迫使他冷嘲热讽,还时常夸大其词。对有学问的女人他太苛责了,对医生的攻击又太盲目了,即使对灌肠器他都来得客气些。但过分夸张是讽刺剧中应流的血液,对戏剧来说必不可少。莫里哀也许能更伟大,如果他能寻着一条讽刺当政腐化、军事野心及路易十四毁灭性的暴君主义的手法。然而,这位优雅的君王保护他对抗仇人,使他能够与偏执做对。然而他又很幸运,死在这位主人成为最具破坏性的偏执自大者之前。
法国人爱莫里哀、演他的戏,如同英国人爱莎士比亚、演他的戏。我们不能像某些狂热的法国人,拿他来与莎翁并列。他只是莎士比亚的一部分,其他部分是拉辛和蒙田。我们也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把他列在法国文林之首。我们也不敢肯定,布瓦洛禀告路易说莫里哀是当朝最伟大的诗人时,他是对的。布瓦洛说这话时,拉辛还没写出他的巨著《菲德尔》(Phèdre)和《阿达莉》(Athalie)。但在莫里哀说来,他不仅仅是法国历史上的作家,他还是这么一个人:受困扰却尽责的经理,受骗而宽宥的丈夫,以笑声掩盖悲戚的剧作家,挣扎到死都与迂阔、偏执、迷信和虚伪作战的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