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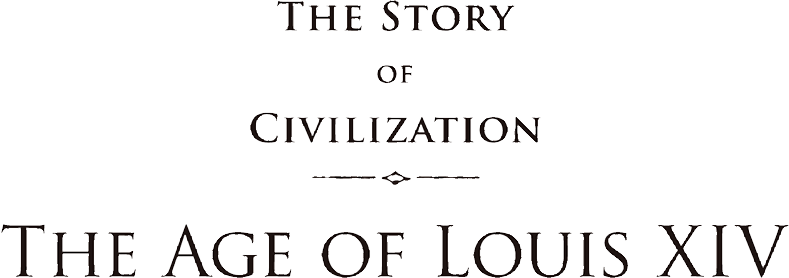
就当时来说,法国教会是胜利的,正处于其权威与尊严的顶峰。虽然教会的精神不宽容,手段残酷,但无可否认地拥有全欧知识层次最高的团体,残酷之士不少,圣徒也不少。有数位主教是人道主义者,诚心地尽心公益,其中有两位主教像帕斯卡一样才华横溢,而且当时的名声比帕斯卡还高:在法国的宗教史上,确实少有人比得上波舒哀的威望与费奈隆的盛名。
波舒哀于1627年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他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律师,也是第戎议会的议员。他的父母希望他成为教士,8岁时便让他受洗,13岁时他在梅斯(Metz)大教堂中成为一名修士。15岁时,他进入巴黎的那瓦尔学院(Collège de Navarre)就读,到16岁时已颇有才名,因而朗布耶厅中的才女们说服他在沙龙中发表布道词。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到梅斯,接受了圣职,不久进修神学博士的学位。他惊骇地发现在梅斯的3万生灵中有1万人是上帝诅咒的新教徒,从此他与一位胡格诺教派领袖费里(Poul Ferry)的关系处于一种有礼貌的对立状态中。他承认天主教中有某些罪恶,但他认为教会分裂则是更大的罪恶。他与费里在信仰的对立中维持友善达12年,此后他与莱布尼茨合作,设法使基督教世界重新联合。国王的母后安妮听了他在梅斯的讲道,认为这样一个人才不应放在如此偏远的地方,说服路易邀请他到巴黎。他于1659年迁往巴黎。
最初,他在圣拉扎尔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t.Lazare)向普通听众布道。1660年,他在皇家广场附近的米尼姆教堂(Church of Les Minimes)向一群时髦的会众讲道。路易听说这位年轻的讲道者不但口才好,信仰纯正,而且有坚强的个性,于是邀他到卢浮宫发表严斋期讲道(Lenten sermons,1662年)。路易以令人注目的虔敬参加这些布道会,除了一个星期日他赶到一个修道院中去寻找露易丝·拉瓦利埃。在国王的气质风度熏染下,波舒哀逐渐改变了省区的粗俗、学者的迂腐及辩证式的论争等各种气质,宫廷中的优雅与礼节也传染了这位高级教士。波舒哀的布道向高一层的境界发展,从而使布道进入一个雄辩时代。他布道的雄辩,足以比拟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与西塞罗的法庭式辩论。此后8年,波舒哀成为宫廷教堂中最受欢迎的布道家。他成为许多名门贵妇,如亨利埃塔公爵夫人、朗格维尔夫人、蒙庞西埃小姐等人的宗教指导者。有时他在讲道中直接向国王说话,通常是夸大的奉承之辞,有一次热诚地召唤路易放弃他的情妇回到自己妻子身边。因而国王有段时间对他大为不满,但当波舒哀感化蒂雷纳悔改后,再度得到国王的宠信。1667年,路易请他在安妮王后的葬礼上发表葬礼演说,两年后他又在亨利埃塔·玛丽亚的葬礼上发表演说。1670年,他又心情沉重地为年轻的亨利埃塔·安妮发表葬礼演说,她是他心爱的赎罪者,以青春盛年死在他的怀中。
这两篇为英国查理二世的母亲与姐妹发表的讲道是法国文学中最著名的演说——也许更著名的应该是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欧洲组织第一次十字军的演说(1095年),但那篇演说虽在法国发表,却是以拉丁文写成的。波舒哀第一篇演说开始于一个勇敢而令人喜欢的主题:一个国君应从历史的教训中学习,如果他不用他的权力为人民造福,神的惩罚将会降在他身上。但他看不出英国查理一世应该受到这种惩罚,除了过分宽厚,他找不出英王的错来,而他在英王忠心的妻子身上更找不到过错。他称呼过世的王后为一个圣人,因为她努力使她丈夫与英国转向天主教。他的语锋最后转向一个他喜欢的题目:各种名目繁多的新教主义,由信仰的混乱而产生的道德的混乱,在英国发生的大动乱是上帝对其背叛脱离罗马教廷的惩罚。但查理一世被处决后,他的王后表现的行为如此令人可敬!她承受她的悲哀,视为一种祝福。她感谢上帝的所为,在谦逊而耐心的祈祷中生活了11年。最后她得到了报偿:儿子加冕复位,而身为母后的她现在可以再住回宫中。但是她情愿住在法国一个修道院中,除了广施善行外,她从不动用她的财富。
更令人感动的、在历史上更为人熟悉的是第二篇演说,是波舒哀在十个月后为亨利埃塔·安妮之死而发表的。那时他刚被任命为法国西南部康敦(Condom)的主教,为这篇演讲他特地赶到巴黎圣丹尼斯教堂,摆出全副主教排场,头戴法冠,前有使者为前导,亨利埃塔公主生前给他的大翡翠戒指在手指上闪耀。通常,在这一类的演说中,演说者的感情总是节制的,以一般的语气谈到死亡。然而现在这位死者,她昨天还是国王的欢乐与宫廷的荣耀。他说到如此实在而痛苦的打击使整个法国陷入悲哀、困惑于上帝如此做的理由时,这位威严的主教忍不住掉下泪来。他没有以冷静客观的语句描述亨利埃塔,代之以热烈的偏爱——永远是甜蜜的、安静的、慷慨的、宽和的,而他仅仅简短地暗示到,她的快乐比不上她受的苦难。有一刻这位谨慎的主教,正统的支柱与护卫者,甚至敢于询问上帝为什么世界上有如许多的罪恶与不平。最后他回忆到亨利埃塔临死的虔诚,临终的圣礼净化了她所有在尘世的牵绊。他向自己与会众宣布,一个如此温柔纯洁的灵魂值得救赎,更值得进入天国乐园。
一向善于判断的路易,被他的辩才感动,做了一个少有的错误决定,任命波舒哀为其子多芬的教师(1670年),信任他去训练这个迟钝的孩子,以使多芬在知识与性格上足以在将来统治法国。波舒哀忠实地接受这项工作,他辞去了主教职务,以接近宫廷与他的监护人。他又为年轻的太子写了许多热心的著作,包括世界史、逻辑、基督教信仰、政府、国王的责任,殷切期待着把这个孩子训练成完美的君主。
在这些文章中,有一篇《从圣经经句中引出的政治学》(1679年、1709年),波舒哀维护绝对王权与君权神授的理论,较贝拉尔米内红衣主教维护教皇至上论更为热切。在《旧约》中说道:“上帝给每一个人民以统治者。”在《新约》中,保罗权威地说道:“那权力是上帝授予的。”使徒保罗又说:“因此,不论何人抗拒这个权力,便是抗拒上帝的委托,那抗拒的人将受到永恒的诅咒。”很明显,任何接受《圣经》为上帝圣道的人须尊奉国王为上帝的代理人,或如以赛亚称居鲁士为“上帝所圣化的”。因此,国王是神圣的,王权神授是绝对的,国王只须对上帝负责。但这个责任给予他严格的义务,他必须在言语与行为上都服从上帝的律法。对于路易来说,幸运的是上帝在《圣经》中对多妻制并无甚恶意。
波舒哀也在1679年为多芬写下了那本名著《世界史论》。他对笛卡儿的理论——以为上帝只是推动的第一因,此后客观世界的所有事件均可依自然的律令机械地加以解释——感到愤怒。相反,波舒哀认为历史上的主要事件都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是全能的神领导其子民经过基督的牺牲、基督教的发展,最后进入天国的过程。波舒哀再度引用《圣经》,他将历史集中在《旧约》中的犹太人与接受基督教的国家上。他说:“上帝利用亚述人与巴比伦人来惩罚神的选民,用波斯人以复其国,以亚历山大保护他们,以安提奥卡斯(Antiochus)试探他们,以罗马人保护犹太人的自由来对抗叙利亚国王。”如果这种理论看起来很愚蠢,我们须记得这同样是《圣经》作者的理论,而波舒哀相信《圣经》是其作者在上帝启示下而写的。因此,他以对《旧约》历史的节要作为开始,以一贯的秩序、扼要、谨严与雄辩的笔法写出这一段。《圣经》纪年是采用厄谢尔大主教(Archbishop Ussher)的编年,定创世的日期为公元前4004年。对于在《圣经》范围以外的国家,波舒哀仅一笔带过,但在这些大略的叙述中却见出他有卓越独特的洞见与了解。在帝国的兴盛与衰亡中,他看出某些进步的原则。在他及其他一些当时作家维护现代与古代的对立之中,进步的观念逐渐成形,并为日后杜尔哥(Turgot)与孔多塞(Condorcet)的理论铺路。这本书尽管有许多错误,但它是第一本现代的历史哲学,波舒哀的成就也可谓不小了。
但波舒哀的这位皇室学生并不能赏识这些为教导他而写的伟大著作,而且波舒哀的性格过于严肃、严格,不能做一个讨人喜欢的老师。将露易丝·拉瓦利埃自通奸的生活引向修道院,倒是更适合他做的事。露易丝宣誓时,是由他发表讲道的。1675年,他再度责备国王在情感上的放浪。路易对他很不耐烦,将他派到莫城做主教(Meaux,1681年),与凡尔赛宫相距不远,使他仍得以接近宫廷的繁华。此后一代之间他是法国教士的权威代表与领导人物,是他拟定4项条款确定法国教会的自由传统以对抗教皇的控制。因此,波舒哀虽得不到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但他在实际上成了法国的教皇。
他并不是很差的教皇。他坚持教会的尊严与仪式,但和蔼且富于人道,一视同仁地对待天主教信仰各个不同的派别。他不原谅《省区书简》中的热情与轻蔑,但他同意谴责良心裁决论的滥用,1700年他说服教士会议通过弃绝耶稣会良心裁决论中的127条见解。他一直与阿诺德及其他詹森教派人士保持友好关系。他对忏悔者很宽大,也反对一般的教徒实行苦修,但他对阿蒙·郎塞的禁欲理论表示赞同。他经常在特拉普圣母修道院静修,希望在修道院的静室中会得到和平,但宫廷豪华生活的吸引胜过对圣洁的向往,使他的神学沾上了政治野心的色彩。有一次他要求莫城女修道院教长说:“为我祈祷,使我不致爱这个现世。”晚年他变得更为严格。我们须原谅他谴责戏剧与莫里哀《喜剧的格言》的剧本(1694年),因为莫里哀的作品仅显示了宗教在清教徒与伪君子的一方面,对樊尚·保罗这种人是不公正的。
波舒哀在行动上较他在理论上更为宽容。他认为,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不管他如何聪明,自以为可以在他的一生中获得足够的知识与智慧裁决其家庭、社会、国家与教会的传统与信仰是荒谬的。社会的“集体意识”(Sens Commun)较个人的推理更值得信赖,这并不是指一般民众的“普通常识”(Common sense),而是指许多年代的集体知识,得自多少世纪以来的经验,而表现于人类的信仰与习俗之中。人如何能说他比这许多人更知道人类灵魂的需要,去回答那些仅凭知识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因此,人心需要一个权威给予他和平,而自由思想则足以摧毁和平。人类社会需要一个权威给予其道德,自由思想由于探究道德律是否起始于神,从而造成整个道德秩序的瓦解。因此,异端邪说是背叛其社会、国家与教会的,“认为一个国君不应在宗教事件上使用武力……是大不敬之罪”。波舒哀倾向于使用劝服而非武力使异端信仰者悔改,但也赞同武力强制是最后的办法。他赞扬《南特诏书》的撤销,认为它是“一项虔信的诏令,将给予异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他自己的教区中他执行诏令极其宽大,以致省区的钦差大臣报告说:“在莫城教区什么也没做到,主教的软弱是令教徒悔改的一大阻碍。”在那个地区,大多数胡格诺派教徒仍维持他们的信仰。
他甚至希望他的论证可以感召荷兰、德国与英国返而信仰天主教,他与莱布尼茨商讨多年,提出一个重新团结分裂的基督徒哲学家计划。1688年,他写成杰作《新教诸派史》。巴克尔(Buckle)说这本书可能是所有直接攻击新教的最可怕的作品。这部四册的巨著是一部辛苦的学术作品,每一页都附上了参考资料,这种负责的态度当时正开始成形。作者在书中也力求公平。他承认路德反叛的教权滥用。他肯定路德的性格有许多可尊敬的地方,但他不能接受路德身上那种轻率的粗俗混合着爱国者的勇气与男子气的虔信。他把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hthon)描写成一个可爱的人。但是,借显示这些宗教改革者的个人弱点及他们在神学上的争论,他希望离间那些追随者对这些大师的崇敬。他嘲笑每个人均可以自由解释《圣经》及借一本著作建立一个宗教的想法。任何熟识人类天性的人都可预见,如果此举不加反对,其结果是将基督教割裂成无数的派别,形成一个个人主义的道德。在这种状况下,人性的本能只能在不断加强的警察力量下才得以控制。从路德到加尔文到苏塞纳斯(Faustus Socinus),从拒绝教皇到拒领圣餐礼到拒绝基督本人,然后从唯一神论到无神论,这是一步步对信仰的分解。从宗教叛乱到社会叛乱,从路德的论文到农民战争,从加尔文到克伦威尔到平等主义者(Leveller)到弑君,这是一步步趋向社会秩序与和平的解体。只有一个权威的宗教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道德与稳定,才能给予人类心灵在面对困惑、离乱与死亡时以力量。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论证,展示了丰富的知识与辩才,其文采在当时的法国散文中除帕斯卡外无人可以匹敌。如果书中诉诸理性的论据不牵涉进《南特诏书》的撤销期间野蛮愚蠢的武力迫害,其效果可能更为成功。在新教国家出现许多驳斥文字,痛诋作者诉诸理性的伪装,因为他竟然以强掠、驱逐、没收财产与苦工船劳役为天主教辩护的论据。而且,难道天主教中没有派别吗?哪一个世纪中没有天主教会的分裂——罗马天主教、希腊天主教、亚美尼亚天主教?难道当时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的詹森教派不正和他们耶稣会的天主教弟兄开战吗?难道法国的国教派教士不是由波舒哀本人领导,与教皇全权论派发生严重的争执,几乎与罗马教会分裂?难道波舒哀没有与费奈隆争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