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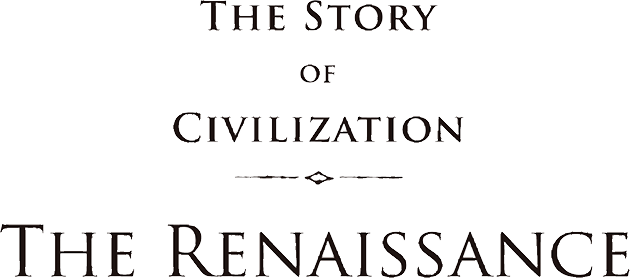
在意大利,14世纪,绘画高于雕刻;15世纪,雕刻高于绘画;16世纪,绘画又居于领导地位。也许14世纪的乔托、15世纪的多纳泰洛和16世纪的达·芬奇、拉斐尔和提香等人的天才在这个转变中占了重要的地位,但是天才是时代精神的结果而不是它的成因。也许在乔托时代,古典雕刻的发现和启示并不像它们对吉贝尔蒂和多纳泰洛一样,发生很大的刺激和指导作用。但是那种刺激在16世纪达到巅峰,为什么没有使伊库甫·圣索维诺(Iacopo Sansovinos)、切利尼(Cellinis)和米开朗基罗的雕刻位居当时的画家之上?为什么米开朗基罗本来是雕刻家,却一步步闯入绘画的领域?
是因为文艺复兴艺术还有比雕刻更广、更深的工作和需要?艺术,在贤明、富有的赞助人的支持下,希望占据整个描述和装饰的领域。用雕像达到这个目标要费太多时间、劳力和金钱,使人不敢问津。在一个匆忙而繁荣的时代,绘画可以更轻易地表达基督教和异教思想的双重范围。哪一个雕刻家能像乔托一样迅速、杰出地描绘圣方济各的生活?而且,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大多数人的情感和思想仍是中古式的,甚至被解放的少数也依恋古神学的回声和记忆,回想它的希望、恐惧和神秘观点,它的热诚、温和与弥漫的精灵音响。这些就像希腊、罗马雕刻所表达的美和理想一样,已在意大利艺术中找到出口和形式。以绘画表达如果不比雕刻更忠实、更微妙,至少也方便得多。雕刻长久地、热爱地研究人体,因此灵魂的表现并不擅长,虽然哥特式雕刻家偶尔也做精灵的石像。文艺复兴艺术必须同时描绘身体和灵魂、面孔和情感,它必须十分敏感,足以表达所有虔诚、挚爱、热情、苦难、怀疑论、感觉论、自负和权力的全部范围和气氛,还要使人感动。只有努力的天才才能用大理石、青铜或泥土达到这样的成就。当吉贝尔蒂和多纳泰洛尝试的时候,他们必须将方法、透视学和绘画的色调差异带入雕刻之中,并为生动的表达而牺牲黄金时代希腊艺术所要求的理想形式和沉着平静。最后一点,画家使用吸引注意的色彩,或叙述大家喜爱的故事,使人们更容易了解。教会发现绘画比冰冷的大理石雕刻或端庄的青铜铸像更容易感人、更亲切地触动人们的心灵。随着文艺复兴的进行,艺术拓宽了范围和目标,雕刻降为背景,绘画的地位提高了。以往雕刻是希腊人最高的艺术表达方式,如今绘画领域加宽了,形式变化了,技巧改进了,已成为至高的、有特性的艺术,成为文艺复兴的面孔和灵魂。
这段时期绘画仍处在摸索与不成熟阶段,鲍罗·乌切洛研究透视学,后来简直没有其他东西使他感兴趣。弗拉·安杰利科在生活和艺术方面都是中古理想的实现。只有在马萨乔的画中才可感觉到即将征服波提切利、达·芬奇和拉斐尔的新精神。
某些次要的天才曾转变了艺术的技巧和传统,乔托教过加多·加第(Gaddo Gaddi),加多再教塔第奥·加第,塔第奥又教安哥洛·加第(Agnolo Gaddi),而安哥洛在1380年仍用乔托形式的壁画装饰克罗齐教堂。安哥洛·加第的学生西尼尼(Cennino Cennini)将当时绘画、构图、嵌饰、颜料、油彩、上光等画家工作所积存的知识汇成《艺术之书》(Libro dell’arte)。第一页写道:“这是《艺术之书》的开始,用以表示对上帝和圣母的尊敬,也对所有圣人们……还有乔托、塔第奥·加第和安哥洛·加第示敬。”艺术成为一种宗教。安哥洛·加第最伟大的学生洛伦佐·摩纳科(Lorenzo Monaco)是一个同志会僧侣。在华丽的祭坛画《圣母的加冕》中——洛伦佐为他那“属于天使”的寺院所画(1413年),洋溢着一种全新的观念和活力,面孔个别化了,颜色灿烂而强烈。但是在三联画上并没有透视学,后面的形象比前景中的还要高。就像从舞台上向下望见的观众头颅一般。谁能让意大利画家领会到透视学的奥秘呢?
布鲁尼里斯哥、吉贝尔蒂、多纳泰洛曾接近它。乌切洛几乎为这个问题贡献一生。他每夜都在沉思,使他太太极为愤怒。“透视学是多么迷人的东西!”他告诉她,“啊!如果我能让你了解其中的快乐多好!”对于乌切洛而言,最美的莫过于图画上平行田畦的稳定接近和远景混合。他在一位佛罗伦萨数学家安东尼奥·曼尼提(Antonio Manetti)的协助下,决心确立透视法则。他研究如何正确表达圆顶的后倾弧度,物体进入前景时的粗劣扩大,曲形廊柱的特殊变形,等等。最后他感到自己已将这种神秘化成规则,由这些规则,一个维度可传达出三维度的幻觉,绘画可以显出空间和深度。这对于乌切洛而言似乎是艺术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他以自己的画证明他的原理,并且用壁画装饰圣诺维拉教堂的回廊。他的画在当时引起轰动,却经不起时间的磨蚀。他仍存的作品是大教堂墙上约翰·霍克伍德的画像(1436年),这位骄傲的贵人曾一度从攻击转而保护佛罗伦萨,现在正加入学者和圣人的行列。
安东尼奥·韦内齐亚诺(Antonio Veneziano)是乔托的门徒,斯塔尼亚(Gherardo Stamina)是韦内齐亚诺的学生,斯塔尔尼亚传授马索里诺(Masolino da Panicale),马索里诺又教马萨乔。马索里诺和马萨乔也研究他们自己的透视学。马索里诺是最初画裸体的意大利人之一。马萨乔最先应用透视学原理得到成功,使当代人大开眼界,也开创了绘画的新纪元。
他的真名是乔万尼(Tommaso Guidi di San Giovanni)。马萨乔是他的绰号,意思是“大汤姆”,正如马索里诺意思是“小汤姆”一般。意大利人喜欢为人取这种有鉴别性的名字。他很小就开始拿画笔,非常热爱绘画,对其他东西都不在意——他的衣服、他的外表、他的收入、他的债务。他曾和吉贝尔蒂一起工作,也许曾在那所学校中学到了解剖的精确性,那是他作品的特征之一。他研究马索里诺在圣玛利亚教堂的布兰卡奇(Brancacci)礼拜堂所画的壁画,也特别高兴注意到其中的透视和远缩试验。在巴迪亚寺院教堂的一根柱石上,他用从下往上看的远缩法画了布列塔尼的圣伊沃(St.Ivo)像,观者都不肯相信圣人会有这样的大脚。在圣诺维拉教堂的《三位一体》壁画上,他画了一个筒状拱环,渐缩的透视非常完美,使眼睛似乎看到画上的天花板正沉入教堂的墙壁中。
使他成为三代之师的划时代的杰作,是他继承马索里诺为布兰卡奇礼拜堂所画的有关圣彼得生平的壁画(1423年)。这个纳税的小故事由这位有新观念、真实线条的青年艺术家描绘出来:基督显得坚决高贵,彼得愤怒庄严,税吏带着罗马运动家的柔软骨架,每一个使徒的面貌,衣服和姿势都不同。建筑物和背景的山丘证明了初兴的透视学。而马萨乔自己,对着镜子摆姿态,也将自己画成群众中一个带胡须的使徒。当他绘制这一系列图画的时候,人们正用游行仪式供奉礼拜堂。马萨乔以敏锐的记忆眼光观察仪式,然后在回廊的壁画中描绘出来,布鲁尼里斯哥、多纳泰洛、马索里诺、乔万尼·美第奇和教堂负责人布兰卡奇都曾参加供奉,现在发现他们都在画里。
1425年,马萨乔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放下他未完成的工作,去了罗马。我们再也没有听过他的消息,只能猜测他也许遭到意外或病亡了。布兰卡奇那些壁画虽然未完成,却立刻被公认为绘画上的一大进步。在那些大胆的裸体、优雅的衣褶、惊人的透视学、写实的远缩法和精确的解剖细节中,在光影的微妙层次深度中,大家都感到一种新的起程,那就是瓦萨里所谓的“现代”形式。凡是佛罗伦萨行程范围可及内有野心的画家都来研究这一系列图画:包括安德烈亚、利比、卡斯塔吉诺、韦罗基奥、吉兰达约、佩鲁吉诺、彼罗·弗朗切斯卡、达·芬奇、巴托罗米奥修道士、安德烈亚·萨尔托、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没有一个已死去的人有过这么多显赫的学生。自乔托以来没有一个艺术家曾经不自觉地有过这样大的影响力。达·芬奇说:“马萨乔以完美的作品显示,凡是不以自然——至高的女主人——为向导的人,都会在徒劳的苦工里耗尽生命。”
在这些刺激的新奇事物中,弗拉·安杰利科静静地走着他自己的中古路线。他生在一个托斯卡纳村庄,本名彼得罗,年轻时就来到佛罗伦萨学画,可能是向洛伦佐·摩纳科学习的。他的天才成熟极快,而他也有希望在世俗领域建立一定的地位,但对和平的热爱、对拯救的渴望使他加入了多米尼克教团。他在各城见习修行,改名为弗拉·乔万尼,然后定居在费舍尔的圣多米尼克修院(1418年)。他在快乐、默默无名的状态下画书稿插图,为教堂和宗教团体画图。1436年,圣多米尼克的教士们转入圣马可新修院,那是由科西莫出钱、任命米开罗佐所建的。以后的9年中,乔万尼在寺院教堂、僧会礼堂、宿舍、餐厅、招待所、廊柱和小室等处的墙上画了50多幅壁画。同时他以十分谦和、十分诚挚的态度修行,修士伙伴们便称呼他为安杰利科弟兄(Angelic Brother)、弗拉·安杰利科。没有人看见过他生气,也没有人能激怒他。凯皮斯(Thomas Kempis)发现他完全“模仿基督”,只有一个微小的差错:在《最后的审判》中,这位天使般的僧侣竟忍不住将几个圣方济各教派修士放入地狱。
对于弗拉·乔万尼而言,绘画是宗教的习题,也是美学上的解脱与喜悦。他绘画的格调很像他的祈祷,而他一定先祈祷才作画。他远离了生命中的严酷竞争,觉得生命是神圣补偿和爱的颂歌。他的题材永远是宗教——圣母和基督的生活、天堂中受保佑的人、圣人的生活、僧侣团的团长们,等等。他的目的与其说是创造美,不如说是激励虔诚。在僧会礼堂中,他画了一张副主教认为应该常存教士心中的图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是一张强有力的绘图,显示出他对裸体的研究和包容一切的基督教本质,在十字架的底部,与圣多米尼克一起的是敌对教团的建立者——圣奥古斯丁、圣本笃、圣伯纳德、圣方济各、古伯托(John Gualberto)、同志会的阿尔伯特。在接待旅人的接待所入口天窗里,安吉利科描绘了有关基督化身香客的故事,因此每一个香客都应该被当作基督化身来招待。招待所内部如今聚集了不少安吉利科为各教堂和公会所画的题材:麻布公会的《圣母像》(Madonna of the Linaioli),其中天使唱诗班的团员都有女性化的柔软外形和天真孩童的微笑面孔;一幅《基督下十字架》(Descent from the Cross),美而柔和,可媲美文艺复兴艺术中描述同一场面的成千作品中任何一幅;一幅《最后的审判》,有一点儿太对称了,而且充满了可怖、不讨人喜欢的幻想,仿佛原谅是人道的,憎恨却是神圣的。在通向小室的楼梯顶部立着安吉利科的杰作《圣召》:一个非常优雅的天使已经对未来的耶稣之母表示敬意,而玛利亚正谦逊地、怀疑地鞠躬,用手画“十”字。在近50间小室中,这个有爱心的教士在他的教士学生的协助下,抽出时间来为每一间画一张壁画,使人回忆起一些激励的福音场面——《基督变容》、《使徒的共融》、《抹大拉的玛利亚以香膏涂基督的脚》等。在科西莫修行的双间小室中,安吉利科画了一幅《耶稣钉上十字架图》,还有《众王的崇拜》,其中众王都穿着富丽的东方服饰,也许就像这位艺术家在佛罗伦萨会议上所见的一般。在他自己的小室中,他画了《圣母的加冕》,那是他曾一再画过的最喜爱的题材。沃夫兹画廊有一幅,佛罗伦萨有一幅,卢浮宫有一幅,最好的是安杰利科为圣马可修道院所画的,其中基督和玛利亚是艺术史上最美好的形体之一。
这些虔敬作品的声名为乔万尼带来数以千计的订单。他对那些慕名而来的人说,他们必须先求得副主教的同意。有了副主教的同意,他不会拒绝他们。尼古拉五世召请他去罗马,他便离开佛罗伦萨的小室,前去为教皇布置礼堂,他选用的情景是有关圣斯蒂芬和圣劳伦斯的生平,这些画至今仍是梵蒂冈最愉悦的画面之一。尼古拉十分仰慕这位画家,建议他做佛罗伦萨大主教,安杰利科借故推辞,推荐他最敬爱的副主教。尼古拉接受了这个建议,而弗拉·安托尼诺即使在大主教长袍之下也仍是一个圣人。
除了艾尔·格里科(El Greco),没有人会像安杰利科一样创造如此统一、如此独特的风格,即使生手也能认出他的手笔。恢复乔托风格的单纯线条和形式;狭隘却清幽的颜色组合——金色、朱红、猩红、蓝、绿——反映出光辉的精神和快乐的信仰;形体也许太简单了,几乎没有解剖观念;面孔很美、很温和,但是苍白得不像活人,僧侣、天使、圣人都相似得近乎单调,就像天堂中的花朵一般;一切都加上温柔奉献的理想精神,气氛和思想的纯洁使人想起中古最好的时刻,不再被文艺复兴所掳。这是中古精神在艺术上的最后呼声。
弗拉·乔万尼在罗马工作了一年,一度曾在奥维托住过,曾在费舍尔的多米尼克修院当过3年的副主教;又被召回罗马,68岁那年死于该地。也许是洛伦佐·瓦拉的古典笔调写出了他的墓志铭:
基督!但愿你将赞美归于我,不因我是你所称呼的另一个人,而是因我曾将一切利益奉献于你。
有的事业是在世上,有的在天上。伊城的花将我若望举起。
基督,不要向你最忠心的信徒,我,称赞我是另一个阿佩莱斯,称赞我已贡献了一切吧;因为有些作品是为尘世,有些是为天堂。我弗拉·乔万尼,是佛罗伦萨城邦的托斯卡纳市民。
艺术从温和的弗拉·安杰利科,经过热情的马萨乔,然后到了一个喜欢生命甚于来世永生的艺术家手中。弗拉·菲利皮诺·利比,屠夫托马索·利比之子,生于佛罗伦萨同志会修院后面的穷巷里。他两岁便成了孤儿,由一个婶母勉强抚养,到了8岁婶母便把他送入同志会教团,摆脱了他。他不喜欢读指定的书,却在书页边缘上画满了漫画。副主教注意到那些画的不凡,让他学马萨乔在同志会教堂所画的壁画。不久这个少年便在同一教堂里画自己的壁画了。那些画现已不存,但是瓦萨里认为不次于马萨乔的作品。他在26岁(1432年)离开寺院,仍旧自称为“教士”(Fra),却活在“世界”里,而且以他的艺术为生。瓦萨里说了一段已被传统所接受的故事——虽然我们无法确知其真实性:
利比据说非常好色,当他看见一个中意的女人,便愿意献出一切财产以占有她。如果不能成功,便画她的画像以平息爱火。这种欲望完全占据了他的心灵,只要有这样的心情存在,他就不再注意他的工作。因此,有一次科西莫雇用他时,把他关在房中,以免外出浪费时间。这样过了两天,他又被色情和原始的欲望所征服,用剪刀剪下床单,从窗户攀下房外,花费很多天的时间尽情玩乐。科西莫找不到他,特别来一次搜寻,最后利比又自行回来工作。从此以后,科西莫让他自由来去,后悔把他关起来……因为,他说:“天才是天上的形体,不是捆扎的驴子。”……后来他努力以情感的束缚绊住利比,因此得到他更情愿的服务。
1439年,利比教士在写给彼罗·美第奇的信中形容自己是佛罗伦萨最穷的教士,有6个侄女与他同住,供养不易,而且她们都急于出嫁。他的作品销路甚佳,但是收入显然不敷侄女们的愿望。他的道德还不至于声名狼藉,因为他还曾经受聘为许多女修院作画。在普拉托的圣玛格丽特(Santa Margherita)修院中,他爱上了卢克雷齐娅·布蒂(Lucrezia Buti),也许是一个修女,也许是修女的监护人。他说服女院长让卢克雷齐娅·布蒂做圣母的模特。不久他们就私奔了。虽然她的父亲责备她,她还是和这位艺术家一起,做他的情妇和模特,让他画出许多圣母像,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成名的小利比。普拉托教堂的监护们并没有为这件事而反对他,1456年,他们聘请他在唱诗班席位上画壁画,描述“施洗者”圣约翰和圣斯蒂芬的生平。这些壁画现在已大大损坏,当时被公认为杰作,构图完美,色彩丰富,充满戏剧性——一端以莎乐美(Salome)的舞蹈,一端以石掷斯蒂芬达到高潮。利比生性好动,觉得这件工作太沉闷,曾两度逃离。1461年,科西莫说服庇护二世(PiusⅡ),让这位艺术家解除僧侣誓言。利比似乎觉得自己也脱离了对卢克雷齐娅的忠心——她现在已不能做圣母的模特了。普拉托的监护们想尽一切办法劝他回去完成壁画。最后,距开始动笔10年之后,他才在科西莫的私生子卡洛·美第奇——现任使徒书记的劝诱下将壁画加以完成。在斯蒂芬葬礼的一幕中,利比竭力去实现的是——建筑背景的透视错觉,环绕尸体而各有特性的形体,科西莫私生子为死者宣读礼文时的强壮体型和平静圆满的面孔,等等。
虽然他在性行为方面很不规矩,可能也正因为他对女人可爱的温柔很敏感,利比最好的作品全是圣母像。它们缺乏安杰利科圣母像中的非俗世精神,但是却表达了深度的柔软人体美和不尽的温柔。在利比教士的画中,圣父一家变成了一个意大利家庭,被家庭偶发事件所包围,而圣母玛利亚的肉体美更预报了异教文艺复兴的来临。除了女性魅力之外,利比在他的圣母像中又加上轻灵的优雅,这种特色后来传给了他的徒弟波提切利。
1466年,斯波莱托城邀请他在教堂东面半圆室内再度描绘圣母的故事。他谨慎地工作,热情冷静下来,但是力量也随着热情消逝,他再也无法重现普拉托壁画的杰出成就了。他在这次工作中死去(1469年),瓦萨里认为是被他所诱惑的一个女子的亲戚毒死的。这一点不太可能,因为他被葬于斯波莱托大教堂中。而且几年以后,他的儿子还应洛伦佐·美第奇之聘为他的父亲建立了富丽的大理石墓。
每一个创造美的人都值得纪念,但是我们这里只能匆匆跳过多米尼克·韦内齐亚诺(Domenico Veneziano)和谋杀他的嫌犯卡斯塔吉诺。多米尼克从佩鲁贾(1439年)应召到圣玛利亚教堂画壁画,他的助手是一位来自伯戈城(Borgo San Sepolcro)的有为青年彼罗·弗朗切斯卡。他在这些作品中——现已失散——第一次做了佛罗伦萨油画实验。他只留给我们一张杰作——《妇人画像》(Portrait of a Woman,现存柏林):上梳的头发,慧黠的双眼,突出的鼻子和丰满的胸。根据瓦萨里的记载,多米尼克把这个新技巧教给了当时也在圣玛利亚教堂作壁画的卡斯塔吉诺,也许竞争破坏了他们的友谊,而卡斯塔吉诺又是一个冷酷、冲动的人。瓦萨里叙述了他谋杀多米尼克的经过,但是其他记录显示多米尼克比卡斯塔吉诺多活了4年。卡斯塔吉诺以克罗齐教堂的基督受难图闻名,其中的透视技巧连同行都大感惊奇。在佛罗伦萨的圣阿波罗寺院中藏有他虚构的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乌波提(Farinata degli Uberti)画像,还有虚张声势的《皮博·斯帕纳像》和《最后的晚餐》(1450年)。《最后的晚餐》似乎画得很差,毫无生命力,但是可能对达·芬奇多多少少提供了一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