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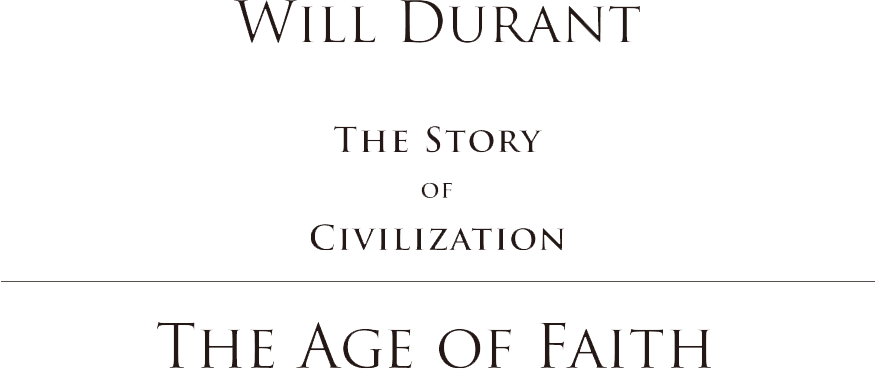
沙普尔、卡瓦德、库斯鲁诸朝都富甲天下,成就卓著,然而留传至今的只有萨珊的艺术品。不过,光是这些艺术品,就足以让我们震惊于从大流士大帝到沙·阿巴斯(Shah Abbas)大帝,从波斯波利斯城到伊斯法罕城(Isfahan),波斯艺术持久的生命力和强大的适应力。
萨珊流传至今的建筑多为世俗建筑,火庙已消失不见,只留下一座座皇宫。而这些废墟仅是“巨型骨架而已”,外面装饰用的灰泥早已剥落。现存最古老的废墟是设拉子(Shiraz)东南菲鲁扎巴德(Firuzabad)城阿尔达希尔一世的皇宫,建成年代不详,有的说是公元前340年,也有的说是公元460年。经过15个世纪的风雨侵蚀、窃盗及战火的破坏,它的圆顶依旧覆盖着一个高达100英尺、宽55英尺的大厅。一座89英尺高、42英尺宽的大拱门把长达170英尺的正面分为两半,这个正面到我们这一代才彻底坍塌,内拱角的拱门从这个长方形的中央大厅向上延伸到圆形的圆拱上。所谓“内拱角”,就是置于多角形建筑物的上部与该建筑物上边圆形或椭圆形圆顶间的对角拱门,克雷斯维尔(Creswell)认为这种方法是由波斯人发明的。一种不常见而又极有趣的设计,使这个圆顶的压力由双层的中空墙壁来承受,这面墙的内部和外部的支架上跨设一个桶状穹隆,再以重量极大的石块做成的半露方柱所形成的外扶墙来加强外墙对内壁的支撑。这种建筑方式和波斯波利斯城的那种古典廊柱建筑大不相同——粗糙笨拙,不过它所使用的形式后来被查士丁尼所建的圣索菲亚教堂采用,并使之达到完美的境地。
离菲鲁扎巴德不远的萨尔维斯坦(Sarvistan)城也留下一个兴建年代不详的同类型废墟:废墟的正面有三个拱门,一个中央大厅,两旁另有厢房,上面有卵形圆顶、桶状穹隆当作扶墙的半圆顶;哥特的飞行式或骨架式的扶墙可能就是从这些半圆顶中除去其他部分,只留下支撑用的骨架演变而来。苏萨西北的另一处王宫废墟——伊万·伊·哈尔卡(Ivan-i-Kharka)有着已知的最古老横亘式穹隆,是以斜弯梁组成的。不过,萨珊遗迹中最感人的——征服波斯的阿拉伯人为其庞大所慑服——是泰西封的皇宫,阿拉伯人称之为“塔克·伊·基斯拉”(Taq-i-Kisra),也就是库斯鲁(一世)拱门。这可能就是638年一位希腊历史学家描写过的那栋建筑。这位历史学家说查士丁尼如何来“为科斯洛埃斯提供希腊大理石以及工匠,为他建了一个罗马式的王宫,其位置离泰西封不远”。这个皇宫的北翼于1888年倒塌,圆顶已不见,三堵巨大无朋的墙高达105英尺,其正面有5层无窗拱廊。极高的中央拱门——已知椭圆形拱门中最高(85英尺)、最宽(72英尺)者——开设在一个长115英尺、宽72英尺的大厅墙壁上。这是历代萨珊国王最喜爱的一个房间。这些毁坏了的建筑正面模仿了马塞努斯剧场(Theater of Marcellus)等较不雅致的罗马前门正面图。这些建筑物给人的印象是大而无当,不过,我们不能光凭遗迹判断过去的美。
萨珊遗迹中最吸引人的并不是那些已被劫掠一空、饱经风雨、仍旧处在倒塌中的皇宫,而是波斯山间那些岩石浮雕。这些巨型雕像是阿契美尼德悬崖浮雕的直系亲属,有些还和它们并列,仿佛是在强调波斯权力的延续,及萨珊诸王和阿契美尼德诸王地位平等。萨珊雕刻中最古老的一个表现阿尔达希尔脚踩倒下去的敌人。较出色的则在波斯波利斯附近的纳克什·伊·鲁斯塔姆(Naqsh-i-Rustam),纪念的是阿尔达希尔、沙普尔一世和巴赫拉姆二世。这些国王当然自觉居于主体地位,但是跟大多数的国王和一般人一样,人物雕像难以跟动物在优雅、对称方面一比高下。纳克什·伊·雷德叶布(Naqsh-i-Redjeb)和沙普尔的同类浮雕表现沙普尔一世和巴赫拉姆一世、巴赫拉姆二世强有力的像。在克尔曼沙阿(Kermanshah)附近“花园拱门”(Taq-i-Bustan)有两个由廊柱支撑着的拱门深深嵌入悬崖中,这两个拱门内外的浮雕表现的是沙普尔二世和库斯鲁·帕维兹狩猎的情形,刻着肥象和野猪,栩栩如生。此外,花形饰物刻工极细,廊柱的柱头也都刻得很好看。这些雕刻丝毫看不到希腊那种动态优美,线条圆滑的特点,没有强烈的个性刻画,没有透视的意味,更缺乏形式设计。不过,在尊严和高贵、表现男性活力与权力等方面,它们足可与帝国式的罗马的大部分拱门抗衡。
这些雕刻作品显然是彩色的,宫廷中的许多雕像也是如此,不过也只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而已。然而,当时的文学作品反映萨珊时期的绘画极为发达。据说先知摩尼还创办了一所绘画学校,斐尔杜西还提到过,波斯的达官显贵常以伊朗英雄的形象来装饰他们的居所。诗人阿尔·布赫图里(Al-Buhturi)也描写过泰西封王宫里的壁画。当萨珊国王逝世时,宫廷召集当时最优秀的画家来为他画像,以便与皇室传家宝一起保存。
绘画、雕刻、陶器及其他装饰都大量使用萨珊纺织艺术的图案。丝、刺绣、织锦、花缎、绣帷、椅罩、床罩、帐篷、地毯等,都以极大的耐心、极工的技巧织成,然后放在温热的黄、蓝、绿等染料中浸染。除了农夫和传教士之外,每一个波斯人都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像上层阶级。礼物常是华丽的衣饰。亚述以来,大幅的彩色地毯就已成为东方财富的合法外快。劫后幸存的利牙的那两打纺织品现已成为目前最珍贵的萨珊纺织品。萨珊纺织品甚至当时就成为自埃及至日本各国艳羡与模仿的对象,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这些来自异教的艺术品还被选为覆盖基督教圣哲遗迹的布料。赫勒克留占领库斯鲁·帕维兹设在达斯塔格德的皇宫时,细致的刺绣和那一望无垠的地毯是最受他珍爱的战利品之一。最有名的是库斯鲁·阿努舍文(Khosru Anushirvan)的“冬天的地毯”,地毯上那些春、夏景色让他忘却了严冬:地毯上还有红宝石织成的花、果,钻石镶在黄金铺成的地面上,银的人行道,珍珠做成的小溪。哈伦(Harun-al-Rashid)还以那块厚厚地钉上珠宝的宽大萨珊地毯为荣。波斯人更以其地毯为题,大写情诗。
除了实用的陶器之外,萨珊陶器很少留传至今。阿契美尼德王朝制陶艺术极为发达,在萨珊领导下继续下去,这一技艺才能在伊斯兰教的伊朗达到这么完美的地步。热心的费内洛萨(Fenellosa)还认为波斯可能是传播搪瓷艺术到远东地区的中心。艺术历史学家争论有光泽的陶瓷器和景泰蓝瓷器到底是渊源于波斯、叙利亚,还是拜占庭。所谓陶瓷器的光泽就是银、铜、锰等上釉,置于密闭的窑内加热,以免直接与火接触,并促使金或银熔入陶器或玻璃上。萨珊的金属工人制作的大口水罐、细颈壶、碗、杯仿佛是为巨人族特制的。先在陶轮上旋转,制成胚胎然后用雕刻刀或凿刀将之切开,或从正面的敲花细工中锤出图案,从雄鸡到雄狮的各种动物像被制成把手或壶嘴。现今存放在巴黎国家博物院(Bibliothèque Nationale)的玻璃库斯鲁之杯就有好多镶入金板中的奖牌形水晶饰物。据推测,这是当年哈伦送给查理曼大帝的礼物之一。哥特人可能向波斯人学来这种镶嵌技术,再把它向西传播。
银匠制造昂贵的盘子,并协助金匠,拿珠宝为地主、淑女和平民制作饰物。一些萨珊时期的银盘留传下来——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列宁格勒收藏所、俄罗斯国家博物馆及地中海艺术博物馆里——所描绘的国王或贵族打猎的场景,对动物的刻画总比对人的刻画成功。萨珊时期的硬币有时铸得跟罗马的一样漂亮,例如沙普尔一世发行的。连萨珊的书本都可以当作艺术品来观赏。有一个传说还讲述摩尼的书被拿去公开焚毁时,金和银不断从书中滴流下来的情形。萨珊家具也用极珍贵的材料。库斯鲁一世就有一张镶宝石的金桌子、库斯鲁二世也送过他的救命恩人莫里斯皇帝一张直径5英尺的琥珀桌子,桌脚是金的,上面镶满宝石。
总之,萨珊艺术在帕蒂安时期式微4个世纪之后,重新焕发活力。要是遗留之物足以作为我们判断的依据,那么它在高贵和伟大方面远不及阿契美尼德,其创意、细致与格调也不如伊斯兰教的波斯,但是在其浮雕上却保存着古老的雄浑,为其后装饰体材的丰盛铺路。它欢迎新观念与新形式,库斯鲁更是一方面打败希腊将领,一方面又好心起用希腊艺术师与工程师。作为偿债的手段,萨珊艺术把它的形式和动机向东输往印度、土耳其和中国,向西输往叙利亚、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巴尔干半岛、埃及及西班牙诸地。或许它的影响使得希腊艺术强调的重点由古典的表现转向拜占庭式的装饰,也使拉丁基督教艺术从木制天花板转为使用砖制或石制的穹隆、圆顶以及带扶墙的墙壁。萨珊建筑的正门和圆屋顶传下来成为伊斯兰教的寺院和蒙古人的王宫和神龛。在历史上不会有失落的东西:每一种具有创意的观念总会有表现、发展的机会,将其艳丽的色彩投注到人类文明的火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