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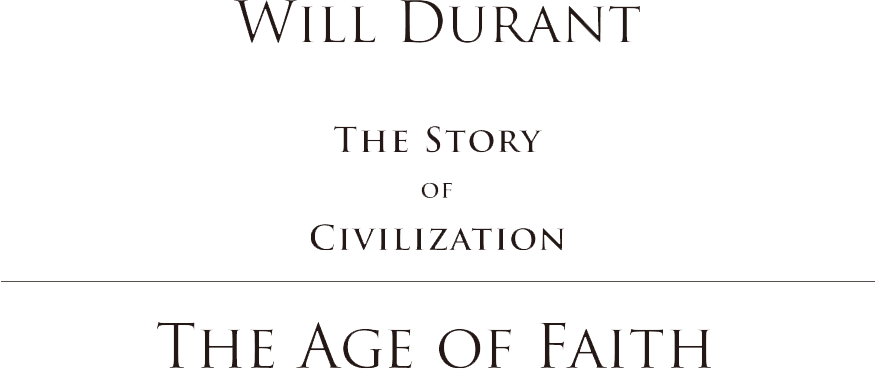
425年,狄奥多西二世或其摄政改组君士坦丁堡的高等教育,并正式成立一个拥有31位教授的大学:一位讲授哲学课程,两位讲授法律课程,其余28位讲授拉丁和希腊文法与修辞,这28位教授还负责拉丁文学和希腊文学的讲授。教授人数之多,使我们联想到学生们对文学的浓厚兴趣。这些教授中有一位叫普里西安(Priscian),他在约526年写了关于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巨著《文法》( Grammar ),该书成为中古时代最著名的教科书之一。东方教会在这段时期似乎不反对抄录异教的名著,虽有少数圣徒进行抗议,君士坦丁堡大学仍然忠实地把古代的名著保存至拜占庭帝国的末期。虽然羊皮纸的价格日渐上涨,书籍的流通仍然甚广。约450年,穆萨欧斯(Musaeus)这位不知来自何处的诗人写成他著名的诗作《希洛与利安得》( Hero and Leander ),诗中描写利安得如何在拜伦之前游过达达尼尔海峡到他钟爱的希洛身旁去,他如何在这次尝试中丧生及希洛在看到他的尸体被冲到她住的塔底下时,她如何
从峻峭的危岩倒栽葱跃下,
陪着死去的情郎随波逐流。
根据异教神明的故事,以古典方式写了最后一批优美情诗并被收入《希腊诗集》( Greek Anthology )的,就是拜占庭宫廷中的基督徒绅士们。以下抄录一首启发了英国诗人本·琼生(Ben Jonson),并以同题材诗歌成为名篇的,阿加提阿斯(Agathias)(约550年)写的一首情诗:
我不爱酒;不过如果你能使
忧愁的人快乐,只要你啜饮一口
递给我时,我一定接过酒。
如果你的樱唇沾上酒杯,为了你,
我就不再严肃,不再坚持,
或是回避那浓香馥郁酒壶。
酒杯把你的香吻递给了我,
告诉了我你赐给它的欢愉。
这段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是历史学家写的。萨狄斯城(Sardis)的欧纳匹乌斯写了从270年到400年的《世界史》( Universal History )。该书现已不存,书中的主角是查士丁尼,此外是23个饶舌的晚期诡辩学者与新柏拉图派学者的传记。君士坦丁堡正统基督徒苏格拉底写了309年至439年的《教会史》( History of the Church ),如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希帕提亚的情形一样,这部历史书极为准确,而且大致说来极为客观。不过这个苏格拉底也在叙述史实时,加上许多迷信、传说、奇迹,并且时常在书中谈到他自己,仿佛他无法分辨他自己和宇宙似的。他在最后还提出了一个新奇的、劝导各宗派和平相处的呼吁:他认为,和平到来的时候历史学家便没有写作的资料,而那一帮可怜的悲剧贩子一定会绝种。索佐门的那本《教会史》( Ecclesiastical History )绝大部分抄袭苏格拉底之作。索佐门是生于巴勒斯坦的基督徒,跟他崇敬的苏格拉底一样,也是首府的律师,法律方面的熏陶显然并未消除他的迷信观念。君士坦丁堡的佐西姆斯在约475年写了《罗马帝国史》(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他虽然是个异教徒,可是在吹牛和无聊方面却不逊于与他竞争的基督徒。525年,狄奥尼西乌斯(Dionysius Exiguus)——“矮子”丹尼斯(Dennis“the Short”)——提出一种记载事件年代的新方法,就是以一般人认为耶稣降生的那一年为基准。这一提议在10世纪之前一直未为拉丁教会接受,而拜占庭的人们始终以世界初创的时间为准来算他们的年代。说来令人灰心,不知道有多少我们早期文明原已知晓的事,我们这一代却一无所知。
这一时期有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普罗科匹乌斯。他生于巴勒斯坦的恺撒里亚(490年),学过法律,到君士坦丁堡后被任命为贝利沙鲁斯的秘书和法律顾问。叙利亚、非洲、意大利诸战他也曾与这位大将军同行,并一同返回君士坦丁堡。550年,他出版了《战争纪事》( Books of the Wars ),由于他亲身体会过这位将军的优点和那个统治者的小气,他故意把贝利沙鲁斯描写成一位显赫的英雄,而使查士丁尼黯然无光。普罗科匹乌斯马上又动笔写《逸事》、又称《秘史》的著作。由于他保密措施极为成功,故一直未出版发行,查士丁尼还于554年任命他撰写自己在位期间新建建筑的记事。普罗科匹乌斯于560年发表了《论建筑》( De Aedifias ),由于书中极力赞美皇帝,查士丁尼不禁怀疑他用心不良或存心讽刺。那一本《秘史》在查士丁尼——也许普罗科匹乌斯——死了以后才公开。这是一本颇富吸引力的书,使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不过就文学而言,对已经无法辩解的人进行人身攻击,是一件令人不悦的事。所以说,滥用笔杆来证实某论点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歪曲事实的真相。
普罗科匹乌斯对自己未经历的事情偶尔记载欠确实,他有时抄袭希罗多德的方法和哲学,有时抄袭修昔底德的演说词和围城事记,他也有着当时一般人的迷信,这使他的著作因征兆、预言、奇迹和梦兆而失色不少。不过对他亲眼看见的事物的记载,则又每一桩都经得起考验。他勇于负责,对资料的处理极合逻辑,他的叙述也很引人入胜,希腊文清晰明了,而且极为典雅。
他是不是基督徒?外表上看他是基督徒,不过有时他也随声附和异教的观点、斯多葛学派的宿命论及学院派的怀疑主义。他谈到“命运”——
邪恶的本质与不可理解的意愿。不过,我认为这些事物从未被人类了解过,将来也一样不会为人了解。对这种题材的谈论一向很多,而且众说纷纭……因为我们人人都想为自己的无知寻求慰藉……我认为想要探寻上帝的本质的人是发了疯的傻瓜……对于这些问题,我想谨慎地三缄吾口,唯一的目的就是不让这些古老、受崇敬的信仰被人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