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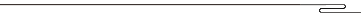
由以上讨论可知:“后谢灵运时代”两位诗人鲍照和谢朓书写大自然的全新美感话语,是在偶有中、低山地丘陵的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经验中产生的。二人登游山岭的作品则继承了大谢“游览”闽浙山地丘陵的风格。
郭熙曰:“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须远而观之,方见得一障山川之形势气象。”
 山水对中国诗、画而言,本质上是眺望中的“远景”,这一点与欧洲文艺复兴后形成的“地景”(landscape)概念并无不同。
山水对中国诗、画而言,本质上是眺望中的“远景”,这一点与欧洲文艺复兴后形成的“地景”(landscape)概念并无不同。
 鲍、谢二人在长江中下游的江矶或数十米的矮丘之上,取代大谢的肢体移动,以望眼揽取更具深度的远景。于是,据山而“望”不再如以往诗人那样,仅为一种生命姿态和超越经验视野的展示,
鲍、谢二人在长江中下游的江矶或数十米的矮丘之上,取代大谢的肢体移动,以望眼揽取更具深度的远景。于是,据山而“望”不再如以往诗人那样,仅为一种生命姿态和超越经验视野的展示,
 而是让视知觉为光所引领,更自由地“游览”世界。这样的美感体验,需要概括为一新的语词。“风景”一词并不苟然地在此时出现了。
而是让视知觉为光所引领,更自由地“游览”世界。这样的美感体验,需要概括为一新的语词。“风景”一词并不苟然地在此时出现了。
“风景”是“空气和日光”以转喻方式实现的词义扩大,因其指向种种气象,确能概括明远和玄晖为中古山水美感话语树新添的枝杈。它精致化了“山水”的书写,因为自然山水映现于望眼之中的样貌,皆取决于当下气象中的光照和空气的纯净度。从“山水”到“风景”,恰如宋人韩纯全论画山水,首论山,次论水,再次论林木与石,复又论“云霞烟霭岚光风雨雪雾”,以为“夫通山川之气,以云为总也”
 。从“山水”复有“云霞烟霭岚光风雨雪雾”,这也是画史本身的逻辑体现:大量以烟霭处理山水,乃是山水被确立为绘画中心主题两个世纪以后的事。在此,诗人的认知和表现显然走在了画家之前。为彰显日光、气流的“风景”,明远将眼前山水风物置于天-地之中,以更广阔的构架书写山水。诗人在谢灵运的“山水”中增添了“氛雾”、“星辰”、“青冥”、“星汉”这些天象,并且关注长江中下游湿气象中的渺漭景色。大谢基元构架下的山/水与色彩的对比被景物间的明暗关系和通贯所替代。
。从“山水”复有“云霞烟霭岚光风雨雪雾”,这也是画史本身的逻辑体现:大量以烟霭处理山水,乃是山水被确立为绘画中心主题两个世纪以后的事。在此,诗人的认知和表现显然走在了画家之前。为彰显日光、气流的“风景”,明远将眼前山水风物置于天-地之中,以更广阔的构架书写山水。诗人在谢灵运的“山水”中增添了“氛雾”、“星辰”、“青冥”、“星汉”这些天象,并且关注长江中下游湿气象中的渺漭景色。大谢基元构架下的山/水与色彩的对比被景物间的明暗关系和通贯所替代。
鲍照诗赋中的天-地框架,绍复了宋玉铺写巫山的云气变幻的天空的传统。其意义超越了文学,成为中国艺术家景观意识的根本。程抱一说:中国画家是负载于地,而将其灵魂转向天。
 其实比之画家,中国诗人并非只是单纯地去望天,而是更习惯自天而俯瞰大地山川。
其实比之画家,中国诗人并非只是单纯地去望天,而是更习惯自天而俯瞰大地山川。
 与西方风景画设置“地平线”以强调画家“从主体的立场出发所观察到的大地之极限”
与西方风景画设置“地平线”以强调画家“从主体的立场出发所观察到的大地之极限”
 ,彰显有限与无限的界限的意识
,彰显有限与无限的界限的意识
 不同,中国诗、画的天-地框架消泯了有限与无限的界限。无论从词源和意义考虑,通常译为“风景”的西方语文中的landscape或paysage,都应译为“地景”
不同,中国诗、画的天-地框架消泯了有限与无限的界限。无论从词源和意义考虑,通常译为“风景”的西方语文中的landscape或paysage,都应译为“地景”
 才更妥当,因为landscape本是画家身处地上某一点的经验视野。而中国诗、画中的山水则是一种“天-地之景”。“天-地”令有限与无限交融于“风”和“景”之中,烟云雨雾皆由“天地相合”以出。
才更妥当,因为landscape本是画家身处地上某一点的经验视野。而中国诗、画中的山水则是一种“天-地之景”。“天-地”令有限与无限交融于“风”和“景”之中,烟云雨雾皆由“天地相合”以出。
 如此的“天-地之景”不再可能仅仅是一个静态的视觉对象,人一旦“仰尽兮天经,俯穷兮地络”,就不再坚持距离感,而落在了无处不在的动态“风景”之中。于此甚至可能藉接连宇宙之气以作“神”之“游”。
如此的“天-地之景”不再可能仅仅是一个静态的视觉对象,人一旦“仰尽兮天经,俯穷兮地络”,就不再坚持距离感,而落在了无处不在的动态“风景”之中。于此甚至可能藉接连宇宙之气以作“神”之“游”。
 一位研究中国山水画的俄国学者说:“天和地自如地奏出了(中国)绘画的‘主旋律’。”
一位研究中国山水画的俄国学者说:“天和地自如地奏出了(中国)绘画的‘主旋律’。”
 宋人郭熙论画谓:“凡经营下笔,必合天地。何谓天地?谓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间方立意定景。”
宋人郭熙论画谓:“凡经营下笔,必合天地。何谓天地?谓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间方立意定景。”
 明人石涛曰:“山川,天地之形势也。……正踞千里,邪睨万重,统归于天之权、地之衡也。天有是权,能变山川之精灵;地有是衡,能运山川之气脉;我有是一画,能贯山川之形神。”
明人石涛曰:“山川,天地之形势也。……正踞千里,邪睨万重,统归于天之权、地之衡也。天有是权,能变山川之精灵;地有是衡,能运山川之气脉;我有是一画,能贯山川之形神。”
 天与地这一阳一阴之间,“天”更具创生而“地”更具呈法的意味,由此展开了中国诗画以滃渤之“气”——云、雾、雨、露——为基本要素的物质想象,灏灏之气令山水缥缈幽窅,如梦如幻【图十、十一】。诗人在开启云空这一特别维度的同时,也因之往往展开超自然的想象。
天与地这一阳一阴之间,“天”更具创生而“地”更具呈法的意味,由此展开了中国诗画以滃渤之“气”——云、雾、雨、露——为基本要素的物质想象,灏灏之气令山水缥缈幽窅,如梦如幻【图十、十一】。诗人在开启云空这一特别维度的同时,也因之往往展开超自然的想象。

图十 三清山云海

图十一 李士达《山亭坐望图》
不无吊诡的是,居停以望“风景”又是切割大自然而“取景”的开端。有学者根据《释名》中诠“景”为“境也,明所照处有境限也”引申出“景”为一“边际化了的光亮”的义涵。
 户牖本为取光之用,且具框限的功能。当谢眺透过轩窗眺望之时,他关注的已不仅是哪处山水,而是变化于光照、温度与气流中的这一刻这一视角中的山水,已藉轩窗自其身体此刻的在世存有对存有界的湍流进行了切割和镶嵌,已从空间和时间上片段化了流而不滞的水色山光、云影天风。这不妨看作是“景”观念的萌起,因为“景”即意味着以画意为追求的切割和片段化。
户牖本为取光之用,且具框限的功能。当谢眺透过轩窗眺望之时,他关注的已不仅是哪处山水,而是变化于光照、温度与气流中的这一刻这一视角中的山水,已藉轩窗自其身体此刻的在世存有对存有界的湍流进行了切割和镶嵌,已从空间和时间上片段化了流而不滞的水色山光、云影天风。这不妨看作是“景”观念的萌起,因为“景”即意味着以画意为追求的切割和片段化。
 这种切割令诗对风景的书写前所未有地出现颇具中国传统绘画画意的平远构图,令诗人藉由方位词、动词的巧用以凸显景物之间迷幻的空间关系,以及浑涵和清晰的穿插变换。然而,“风景”又同时意味着一切皆笼罩于天地之中,意味着诗人处身于“风景”的氛围之中。故而,所谓画意构图,绝不意味着诗人面对着隔绝在主体之外的对象,而是“身即山川而取之”
这种切割令诗对风景的书写前所未有地出现颇具中国传统绘画画意的平远构图,令诗人藉由方位词、动词的巧用以凸显景物之间迷幻的空间关系,以及浑涵和清晰的穿插变换。然而,“风景”又同时意味着一切皆笼罩于天地之中,意味着诗人处身于“风景”的氛围之中。故而,所谓画意构图,绝不意味着诗人面对着隔绝在主体之外的对象,而是“身即山川而取之”
 ,即诗人自由地与山水风景往还,游目于其中;山水风景亦同时拥入诗人的视野。
,即诗人自由地与山水风景往还,游目于其中;山水风景亦同时拥入诗人的视野。
对诗歌而言,明远、玄晖对风景与情感之间新关系的开拓更为重要。谢灵运的山水诗多依诗人的“游览”过程而展开,铺陈山水美之余,必须不无生硬地解说经此而发的理悟或感叹。情与景、心与物故而由外在的逻辑所连贯。鲍照对景与情关系的开拓,主要见于其宦游和去离题材的作品。诗人于自然现象的结构或基调之中发现了与其情感类似的结构或基调,其中江天湿气象的淼茫景象特别成为漂泊旅人迷茫、阴沉心境的象征。在此,鲍照开拓的新情景关系藉用和符应着其铺写风景的天-地框架。
玄晖对情与景关系的开拓亦自其以轩牖吸纳两间景物的框架中生发。由此,诗人当然不会再叙写其肢体进入山水的过程,而只敏感于眼前比山水更广阔亦更不恒定的“风景”氛围中或乍然倏尔之间、或悄然浸润之中的动态变化,而其心灵的微澜则因之油然而起。此处再无游览和理辩的区隔和逻辑联系,因为心境的变化亦几乎与“风景”同步。后人所谓“入兴贵闲”、“兴隐而比显,兴婉而比直,兴广而比狭”云云,当以此类诗作的经验为基础。而且,玄晖写此种种荒忽变化之笔致,竟如此轻灵摇曳;发此种种情意之语调,竟如此从容儒缓,在在符应眼前“清远绵渺”之风景,和心中缕缕之清愁。玄晖亦如明远,着笔于江南湿气象中的山水,然与明远不同,玄晖情景交融的世界仍不乏优美之致。谢朓故而是真正的“淡墨轻岚”的诗中董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