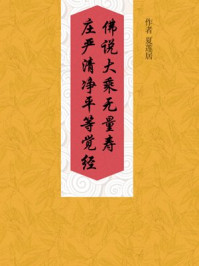少林寺的达摩被禅宗奉为东土初祖,他把禅学奥旨又传给了一个中国高僧慧可,是为二祖;慧可传给僧璨,为三祖;僧璨传给道信,为四祖;道信传给弘忍,为五祖。弘忍有两个得意弟子: 神秀(606—706年)和慧能(638—713年)。据《坛经》记载,慧能二十四岁往蕲州黄梅(今属湖北省)东山寺参拜弘忍。弘忍先令慧能在寺内随众作劳役,于碓房踏碓舂米。弘忍将传法衣,上座弟子神秀先写了一个得法偈书于廊壁上,其偈说: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然而这一偈未得弘忍心许。慧能虽不识字,也请人于壁上代书一偈,其偈说: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慧能这一偈,把菩提树、明镜台都看成虚无的,自然要比神秀对“空”的理解彻底得多,因而得到弘忍的赏识,密授以法衣(袈裟)。于是慧能成为禅宗六祖。他得到法衣后,立即南下到岭南,后于曹溪(今广东省曲江县)宝林寺弘扬佛法,提倡顿悟自性,开创禅宗之南宗。神秀在荆州玉泉寺说法,后来被武则天召至长安,倡渐修之说,称为禅宗之北宗。于是禅宗有所谓南顿北渐之分。
《坛经》记载的传衣故事不可尽信,事实上,敦煌抄本《楞伽师资记》卷一就是把神秀当作弘忍的接班人的。而且,据神秀和弘忍禅法之间的关系来看,《楞伽师资记》的说法更为可信。弘忍的“东山法门”,主张“背境观心,息灭妄念”,而神秀的北宗则要求人们“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荷泽神会禅师语录》)。所以,神秀当年寻师访道,遇五祖弘忍以坐禅为务,乃叹伏曰:“此真吾师也。”(《五灯会元》卷二)可见他们的禅法都接近于达摩的壁观禅。
神秀的中心理论是:心如明镜,本自清净,只因为心不净才产生善恶差别,所以须“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也就是说,必须通过长期修习才能逐步领悟佛理而成佛,禅定工夫必须持之以恒,莫使心灵受外界尘埃的污染。他的偈语,完整地浓缩了佛教“戒(防非止恶)—定(息虑静缘)—慧(破惑证真)”三阶段方式,形象而又通俗地表明了佛教对于世界的理解以及对解脱方式的理解。
然而,在慧能看来,这种时时拂拭、天天坐禅实在太麻烦。既然众生都有佛性,佛即在自性中,又何必向外去求,成佛只在一念之悟、刹那之间,顿悟自性,便可成佛,“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坛经》)。这是一种何等简捷的功夫!既然成佛在于“一念”,在于刹那顿悟,那么传统佛教所主张的读经、明律、念佛、坐禅等一系列修行功夫,也就失去了重要意义。慧能对坐禅的理解也不同于神秀,他只管坐禅的实质和功能,而不在乎其静坐的形式,“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坛经 · 坐禅品》)。从此,行住坐卧皆是禅,再不必像达摩那样面壁九年。当然,慧能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渐修,他认为佛法无顿、渐之分,但人有利(聪明)、钝(愚笨)之分,有迷、悟之分,对于愚迷之人,还是要先通过渐劝手段,才能最后达到顿悟。
我们这里且不谈慧能这次宗教革新的意义,只是想说明“渐修”和“顿悟”两种修行方式对中国古代诗论的启示。慧能的弟子神会曾对顿悟说有过一段详尽完整的解释:
自心从本已来空寂者,是顿悟;即心无所得者,为顿悟;即心是道,为顿悟;即心无所住,为顿悟;存法悟心,心无所得,是顿悟;知一切法是一切法,为顿悟;闻说空,不着空,即不取不空,是顿悟;闻说我不着,即不取无我,是顿悟;不舍生死而入涅槃,是顿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
这里所说的“即心是道”、“存法悟心”、“知一切法是一切法”、“不舍生死”等,都悟到诸法“如实”的存在,具有肯定现实的方面。正因如此,顿悟的结果,不是指向彼岸世界,而是指向现实人生,这就与表现现实人生的诗歌有了携手的可能。从盛唐孟浩然的“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来 黎新亭作》)的悟道,到晚唐齐己的“禅关悟后宁疑物,诗格玄来不傍人”(《道林寺居寄岳麓禅师二首》)的禅悟诗玄的对举,再到北宋吴可的“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藏海诗话》)的诗禅相通说,可见随着晚唐两宋时期禅宗影响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自觉地将禅之悟与诗之悟沟通起来了。
禅悟是东方思维中的一种特有表现方式,它关系哲学心理学中常说的直觉、体验、灵感、想象、独创等,但却非其中每一概念所能涵盖,它与艺术思维能力有共通性。“禅则一悟之后,万法皆空,棒喝怒呵,无非至理。诗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先生说:“禅如果没有悟,就像太阳没有光和热一样,禅可以失去它所有的文献、所有的寺庙以及所有的行头,但是,只要其中有悟,就会永远存在。”(《禅与生活》第四章)同样,诗的思维也离不开悟性,没有悟性的诗人,就像没有翅膀的鸟。悟使人心花开放,茅塞顿开,左右逢源,纵横自在,悟使诗人获得自己本心的创造能力,这种创造力正如禅家所谓的“般若智”一样,本来就潜藏在他心中。所以宋人严羽的《沧浪诗话》说:“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过去学术界往往把诗之妙悟等同于禅之顿悟,其实妙悟应当包括“渐修”和“顿悟”两个阶段。一个不识字的和尚,可能不暇修持,灵心一动,即可悟道。然而,一个没有丝毫艺术修养的人,却不可能灵心一动,而写出优美的诗来。因为,禅不需用语言,诗却离不开语言。禅可以一念悟众生即佛,一念迷佛即众生(照《坛经》的说法),而诗却“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文心雕龙 · 神思》)。所以,严羽尽管声称他的学诗方法“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沧浪诗话》),但实际上,他开的一长串须熟参的诗人的名单,以及“朝夕讽咏”的熟读方法,何尝不是“时时勤拂拭”的渐修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的妙悟是一种渐悟,在长期艺术实践的基础上,掌握写诗的精微规律。这一精微规律如禅家的正法眼藏,必须在熟读前人大量作品的基础上,通过直觉、经验领悟到它,这就需要渐修的功夫。因此,唐宋以降以禅喻诗的诗人们常把学诗过程比作由渐修而至于顿悟的过程:
虽然,方外之学,有为道日损之说,又有学至于无学之说,诗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非技进于道者能之乎!(元好问《陶然集诗序》,《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七)
然偈不在工,取其顿悟而已。诗则一字不可不工。悟而工,以渐不以顿。(方回《清渭滨上人诗集序》,《桐江续集》卷三十三)
盖积之不厚,则其发之也浅;发之不秾,则其感之也薄。彼禅者或面壁九年,雪立齐腰,后之学诗者,其工夫能尔耶?(刘将孙《如禅集序》,《养吾斋集》卷十)
所谓技进于道,厚积工夫,都是禅家的渐修法门。吴可的一首《学诗诗》写得最为形象:
学诗浑似学参禅,
竹榻蒲团不计年。
直待自家都了得,
等闲拈出便超然。
没有“竹榻蒲团”的渐修,哪来“自家了得”的顿悟,这就是诗人们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