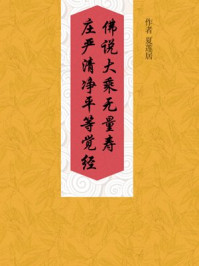通过对禅宗公案史的匆匆巡礼,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禅宗的哲学其实就是一种诗化哲学,至少在它的方法论、认识论、行为论方面是如此。用李泽厚先生的话来说:“中国哲学思想的道路不是由认识、道德到宗教,而是由它们到审美。”(《漫述庄禅》,上海人民出版社《关于思维科学》)这是就形而上而言。从形而下来看,禅宗宗师们在示法、开悟、颂古方面,动辄吟诗引句,为传授教法之用。虽然禅宗认为第一义不可言说,但是到启悟后学之时还是须勉强去说。每遇此际,大师们就拈出各种象征方式,如棒喝,如机锋,借模拟动作,引人入悟。诗因其象征性极大,所以禅宗诸师常常爱借用作得鱼之筌、示月之指。而且又因诗的形式易于使人记诵,所以诸师常以诗偈表示自身开悟或向别人示法。这样,禅宗公案里的语言可以说绝大部分由诗的语言组成。随便举一则公案就可略知一斑:
上堂:“瘦竹长松滴翠香,流风疏月度炎凉。不知谁住原西寺,每日钟声送夕阳。”上堂:“声色头上睡眠,虎狼群里安禅。荆棘林内翻身,雪刃丛中游戏。竹影扫阶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上堂:“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衲僧失却鼻孔。是风动,是幡动,分明是个漆桶。两段不同,眼暗耳聋。涧水如蓝碧,山花似火红。”(《五灯会元》卷十六《云峰志璿禅师》)
三次上堂(指为演说佛法上法堂)垂语示众,都用的诗句韵语。第一次是音韵谐和、意境清新的绝句,第二次是几句对仗工整、平仄协调的偶句,第三次是句式多变、风格诙谐的韵文。可见出禅师们示法相当讲究语言的修饰。
袁行霈先生认为:“诗和禅的沟通,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双向的,其实主要是禅对诗的单向渗透,诗赋予禅的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诗与禅》,《文史知识》1986年第10期)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难道诗仅仅是为禅客“添花锦”而已?让我们来看看偈颂的演变过程,再想想这种演变中是否还包含着除形式以外的因素。
偈颂是佛教经典中的一种文体,梵文作伽陀,是佛经中的赞颂词。伽陀是古印度的诗歌,本来在梵文里,偈颂的体制很严密,讲究音节格律,但在汉译佛典时,译场师为了便于读诵与理解,不惜削足适履,把它们通通依照中国诗的传统形式(主要是五言,也有四言、六言、七言)翻译出来。由于既要借用中国诗的形式,又受原典内容与形式的限制,因此传译的偈颂不得不放弃梵文的辞藻与韵律,形成一种非文非诗的体裁。所以在佛典三藏(经藏、论藏、律藏)中,偈颂一般是拙朴粗糙的,仅做到了每句的字数整齐一致,连节奏与押韵都无暇顾及。如反映原始佛教教义的《杂阿含经》中的一些偈颂:
法无有吾我,亦复无我所。
我既非当有,我所何由生。
比丘解脱此,则断下分结。
(卷三)
佛者是世间,超渡之胜者。
为是父母制,名之为佛耶?
(卷四)
除了五言的整齐形式外,再没有任何可称为诗的因素。这一方面受到译者文化水平与翻译文体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因佛经主要是对大众宣讲的,必须采用一种通俗朴实的接近口语的语言。这时的偈颂,不过是佛经散文(长行)的分行排列形式,说理叙事,基本上与中国传统的诗歌无关。
六祖慧能开宗以后,偈颂开始盛行,并成为押韵的精炼的诗偈。禅宗所谓不立文字,很大程度上是排斥概念化的、说教式的佛经中的文字,而非象征性的、非逻辑性的诗的文字。所以,从禅宗出现时起,诸大师就以诗偈作为传心示法的主要工具。不过,在早期的禅宗祖师中间,除了前面所举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和慧能的“菩提本无树”两首示法偈算是较生动形象的说理诗外,其余诸大师的偈却是相当枯燥乏味的。例如,南岳怀让的示法偈:
心地含诸种,遇泽悉皆荫。
三昧华无相,何坏复何成!
(《五灯会元》卷三)
又如马袓道一的示法偈:
心地随时说,菩提亦只宁。
事理俱无碍,当生即不生。
《五灯会元》卷三
完全是在阐述佛教哲理,没有丝毫诗意可言。这种情况在中唐开始出现转折,偈颂的诗意开始越来越浓。如马祖道一的法嗣明州大梅山法常禅师的偈:
摧残枯木倚寒林,
几度逢春不变心。
樵客遇之犹不顾,
郢人那得苦追寻?
一池荷叶衣无尽,
数树松花食有余。
刚被世人知住处,
又移茅舍入深居。
(《五灯会元》卷三)
又如灵云志勤禅师因见桃花而悟道所写的诗偈:
三十年来寻剑客,
几逢落叶几抽枝。
自从一见桃花后,
直至如今更不疑。
(《景德传灯录》卷十一)
平仄音韵完全符合近体诗格律,而且运用比兴手法,虽也是说理之作,但比起初期的偈颂来,已经非常像诗了。就是比起王梵志、寒山、拾得等诗僧那些直白浅显的诗来,也毫不逊色,甚而更有诗味。
从诗偈的体制来看,中晚唐后也变化更多,逐渐出现五律和七律这样格律精严、对仗工整的诗体。著名的如法眼宗的创立者清凉文益的一则故事:
宋太祖将问罪江南,李后主用谋臣计,欲拒王师。法眼禅师观牡丹于大内,因作偈讽之曰:“拥毳对芳丛,由来趣不同。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后主不省,王师旋渡江。(《冷斋夜话》卷一)
文益的这首偈简直就是一首咏牡丹的咏物诗,他采用的是五律的格式,全用譬喻和象征来说理,意在言外,余味无穷。
学术界一般都只注意到偈颂文体对诗坛的影响,如带来诗风的通俗化、哲理化等(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七章再作论述),却忽视了诗对偈颂的反馈作用,以及在此后面蕴藏着的诗的审美特质对禅的渗透。在我看来,这些反馈或渗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佛经中的偈颂或早期禅宗的诗偈由于着意要用某种类比来表述意蕴,常常因陷入概念化而变为论理诗、说教诗,这恰好违反了禅宗的本旨。聪明的禅师发现,不少唐代诗人的作品实际上比许多偈颂更真正接近于禅,所以在各种语录、灯录里,著名诗人的佳句被大量用来说法,如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韦应物的“野渡无人舟自横”(《滁州西涧》)、齐己的“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早梅》)等,就分别被雪窦重显、开先善暹、翠岩可真等禅师所引用(见《续传灯录》卷二、卷七),来暗示禅所追求的意蕴和“道体”,或是神秘的悟道体验。甚至禅家有时就直接把诗人的名句嵌到自己的诗偈里,如《人天眼目》卷四所载法眼宗的“三界惟心”颂:
三界惟心万法澄,
盘环钗钏一同金。
映阶碧草自春色,
隔叶黄鹂空好音。
后两句就完全是生吞活剥杜甫《蜀相》诗的颔联。这种大量的引用、点化或摹仿的结果,无疑使诗的审美趣味不知不觉渗透到禅中来。
其次,不少禅师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比如清凉文益“好为文笔,特慕支、汤(指六朝诗僧支遁、汤惠休)之体,时作偈颂真赞,别形纂录”(《宋高僧传》卷十三),曹洞宗开山祖师曹山本寂“素修举业”,“文辞遒丽”,“注《对寒山子诗》,流行寓(宇)内”(《宋高僧传》卷十三)。唐以诗赋取士,本寂所修举业,即指诗赋。像这样富有文学修养的大师加盟禅宗,并开宗立派,必然带来禅风的变化,前面所举文益的那首诗偈就是一个例子。从晚唐到北宋,所谓禅宗由无字禅越来越发展为文字禅,并不是重新回到佛典的繁琐教义中去,回到思辨推理的文字中去,而毋宁说是发展为一种指向审美的诗禅。
其三,诗歌体制与风格的演变直接导致偈颂风格的演变。近体格律诗奠基于初唐,定型于盛唐,因而早期的偈颂,多为五古或不入律的五绝,盛中唐以后,禅偈始为律句,我怀疑《坛经》中达摩、神秀、慧能的偈(均见前)都出自盛唐后禅和子的伪造。最早以五律为禅偈的是庞蕴居士那首“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的示法偈。最早以七律为禅偈的是裴休(唐宣宗大中年间宰相)呈示黄檗希运禅师的那首:
自从大士传心印,
额有圆珠七尺身。
挂锡十年栖蜀水,
浮杯今日渡漳滨。
一千龙象随高步,
万里香花结胜因。
拟欲事师为弟子,
不知将法付何人。
这当然算不上好诗,但可看出禅门外的人对偈颂形式的贡献。另外,五代北宋偈颂,有近艳体诗者;南宋诗偈,又多类江西诗派,如南宋诗人曾几就称秀峰空和尚的偈得“江西句法”,从“派(江西诗派)中来”(见《罗湖野录》卷三)。可见诗风的变化直接影响偈颂风格的变化。
那么,以上这几方面的渗透是否仅仅是诗赋予禅的一种形式而已呢?我看并不是这样。既然人们都承认禅宗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那也就是承认禅宗渗透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中国文化中有一重要特色,就是尊重文学的空气很浓,而中国文学的最大特点,一是取材于日常经验的诗文为文学的主流;二是文学的修辞性极强,例证之一就是律诗;三是对典范的尊崇(见其《中国文学史》第一章“中国文学的特色”,岩波书店1975年版)。中国诗对偈颂的影响,其实就是中国文学这三大特点对偈颂的渗透过程,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文化精神对禅的改造过程。
先说第一大特点,取材于日常经验的诗歌对禅宗的世俗化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早期的偈颂偏重于直接阐述教义,宗教意味很强。后期的诗偈偏重于用日常生活经验来作象征譬喻,直接取材于日常生活,带着世俗人的各种复杂感情。比如有两首关于楼子和尚听唱“你若无心我也休”一句曲而悟道的偈颂:
因过花街卖酒楼,
忽闻语唱惹离愁。
利刀剪断红丝线,
你若无心我也休。
唱歌楼上语风流,
你既无心我也休。
打着奴奴心里事,
平生恩爱冷啾啾。
(《禅宗颂古联珠通集》卷四十)
离愁别恨,情韵深婉,哪里还有半点宗教的影子。这显然是诗坛流行的艳体诗影响的结果。
再说第二大特点,修辞性极强的诗歌对禅宗日益演变为文字禅起了很大作用。大约从晚唐五代开始,禅师们就已非常自觉地提倡语言修饰,反对缺乏诗意、不讲修辞的野谈俗语,文益禅师《宗门十规论》里的观点就集中代表了这种倾向:
稍睹诸方宗匠,参学上流,以歌颂为等闲,将制作为末事。任情直吐,多类于野谈;率意便成,绝肖于俗语。自谓不拘粗犷,匪择秽孱,拟他出俗之辞,标归第一之义。识者览之嗤笑,愚者信之流传。使名理而寝消,累教门之愈薄。不见华严万偈,祖颂千篇,俱烂漫而有文,悉精纯而靡染,岂同猥俗,兼糅戏谐。在后世以作经,在群口而为实,亦须稽古,乃要合宜。
所谓“烂漫有文,精纯靡染”,完全是遵循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心雕龙 · 原道》)的古训,把美的感动作为伦理的、宗教的感动的前提。与此同时,就是用一种文学的语言去代替任情直吐的口语白话。
最后说说第三大特点,尊崇典范的诗歌对禅宗颂古拈古之风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诗歌对典范的尊崇表现为仿拟大作家、点化前人诗句及用典故成语等,这种现象在宋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西昆体仿李商隐,江西诗派学杜甫,永嘉四灵效贾岛、姚合等。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禅师的诗偈用典的风气也相当浓厚,如惠洪觉范禅师的一首偈:
天下心知不可藏,
纷纷嗅迹但寻香。
端能百尺竿头步,
始见林梢挂角羊。
(《林间录》卷上)
“百尺竿头”语出《景德传灯录》卷十,“挂角羊”出自《景德传灯录》卷十六雪峰义存的一个著名比喻。更值得注意的是,禅家的颂古、拈古也开始出现于宋初,并蔚成风气,愈演愈烈。所谓颂古,是举一则古德(佛教徒对先辈的尊称)的公案,为作韵语,发明其意;拈古,是拈起古德公案作批评。前面说过,禅门在中晚唐曾掀起过一股离经慢教、呵佛骂祖之风,似与此相矛盾。但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的那样:“它打倒了佛教经典的权威,但是,代之而起的是禅宗祖师们的语录的权威。”(见《论禅宗》,《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这可以从“看话禅”那里得到证明,从颂古与拈古中更能确定这一点。当我们注意欣赏颂古拈古那些优美诗句之时,是否想到过诗人尊崇典范的文化心理也随之渗入禅门之中,使那些曾一度呵佛骂祖的禅宗门徒,也逐渐跪倒在古德公案脚下,到古德的话头中去讨灵丹妙药。
世俗化、文学化、典范化,这就是诗在赋予偈颂形式的同时赋予禅的精神内容。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偈颂的诗化过程,也就是禅宗的中国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