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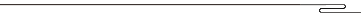
以赛亚·伯林讨论问题的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格,是他往往喜欢通过对一系列“那不是什么”的阐述,来界定自己有关“那是什么”的核心观念。但是我们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在迫不得已要从他的诸多“那不是什么”的外围论辩中去抽绎出伯林心目中对“那是什么”的真正见解。
陈来这篇论文所从事的,正是这样一项很不容易的工作。它力图围绕着对“归属”的渴望与“创伤”导致要求被承认的情绪因发炎而强烈反弹这两个主题,对伯林观念中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或者也可以分别把它们视为“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加以区分。陈来指出,特别是在追溯民族意识为什么会“发炎红肿”的根源时,伯林“显然表达了对民族主义较多的同情理解”。
我们都知道,伯林十分肯定地把自己称为“自由的理性主义者”,一个“相信民主、人权和自由国家的人”。正如陈来所说,恰恰由于自由主义对个人所抱持的那种相当不同的理解,伯林以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身份对民族主义的同情与肯定,成为人们之所以对他的见解倍加关注的内在原因。由此便引发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用“自由民族主义”这样一个概念,来概括伯林对待民族主义问题的基本立场吗?
在这里,陈来所进行的细致分辨大概包含如下三个要点。首先,民族主义作为“三种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国家意识形态”之一,必须分别被另外的那两者,也就是被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家建制所直面、接纳、妥协和结合。在此种意义上,伯林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遗产,对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也具有非常积极的参考价值。其次,对伯林所持有的这一立场,无须采用“自由民族主义”这个他本人从未使用过的概念予以阐释。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伯林思想中的共存,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就是政治自由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共存。因而站在伯林的立场上看问题,他也许更愿意接受的,是一种类似丹尼尔·贝尔提出的多元结构模式。最后,我们虽然不能将自由民族主义直接指归于伯林,但它确实可以被看作伯林的学生和研究者对伯林思想的积极而并不过度的诠释和发展。
对上述第二、第三点之间的分疏和辨析是完全必要的。陈来明确指出:一方面,伯林对民族主义的警觉和提防,针对的主要是政治民族主义,而不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主张和实践;另一方面,伯林自己不仅很少“把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关联在一起讨论”,甚至“政治自决的民族主义”在伯林论民族主义的文字中也“很少涉及”。那么除此之外,二者之间是否还存在更进一步的内在理路上的联系呢?
我以为,在伯林本人思想深处,或许确实存在着可以将上述两点联系在一起的过渡环节。为此,很有必要像此前的伯林研究者已经做过的那样,将他强调过的“家园”意识在刺激民族主义情感方面的重大作用引入讨论,无论这种“家园”意识应当被看作与“归属”及“创伤”并列的催发民族主义的三种重要情感,还是可以将它当作“归属”情感中一项意义异乎寻常的内容。
伯林在提到以色列国家的缔造者和它的第一任总统魏茨曼时这样赞扬道:“他本能地看出,人们(此指犹太人——引用者)只有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在那里,人们可以不必时刻担心别人如何看待自己,自己又该如何对待别人,自己的行为会不会让人讨厌,或者自己的行为会不会引起别人过分注意——才能自由地发展,才不会老是担惊受怕——‘这样做对吗’?‘他们会接受吗’?赫尔德早已表述过这样的看法;不过,据我所知,魏茨曼并不知道。”他曾在另一处这样转述“魏茨曼并不知道”的赫尔德的见解:“一个人的创造力要想得到充分发挥,只能是在他自己的出生地,跟那些与他在身体上、精神上类似的人生活在一起,那些人跟他讲着同样的语言,让他感觉像回到家一样自在,跟他们在一起,让他有归属感。唯有如此,真正的文化才能产生出来,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特的,都对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特殊的贡献……而这些文化却只有在他们自己的土壤中,扎下自己的根系,并且可以远溯到某种共有的过往经历,才会枝繁叶茂。”伯林肯定,犹太人对“作为一个共同体自由发展”的希望、他们“追求一种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是符合赫尔德的思想的。而对犹太人来说,实现这种追求和希望最首要的前提,是获得一片可以作为家园的土地。伯林征引同时身为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赫斯曾一再重复的话说:没有土地,就没有民族生活;“只要它依然是个没有家园的民族,即使街头恶少也会把羞辱它当成自己的义务”。因此,问题的核心正在于犹太人的无家可归。“利用他们自己的自然资源,在自己的土地上”,在他看来,至少是与“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等等同样重要的民族文化得以发展的条件。所以他坚持认为:“犹太人活下来了,但只有迁移到他们的故土,他们才能作为一个民族重新振兴。”在这个意义上,他毫不犹豫地宣称:“我当然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我们自然有充分的必要从“那不是什么”的角度去界定伯林所抱持的犹太复国主义。最重要的,它肯定不是一种“整体论意义上的犹太复国主义”(Integralist Zionism)。犹太民族必须有一个安全的、民族自决的家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有权利强制性地要求聚拢所有的犹太人。对那些已安于在世界各地作为少数族群而生活的犹太人,乃至自愿放弃自己族裔身份的犹太人个体及家庭,他们应当具有自主地做出这些选择的全部自由。另外,即使在被犹太人当作自己家园来建设的以色列,仍然需要保证位于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圣地的治外法权,以及在以色列领土内的众多巴勒斯坦人的政治及宗教信仰等权利,并必须在实现与巴勒斯坦的永久性领土分割后与它保持克制、友好、和平的睦邻关系。但是,纵然在枚举出更多的“那不是什么”的限制之后,他的犹太复国主义立场依然被不止个别的学者满怀犹疑地看作与他对消极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及宽容等等的强烈主张之间毋庸回避的、“真实的紧张”,看作他灵魂中“不同层面”的反映,甚或看作有点违背他的其他许多更连贯一致的见解的“例外”。
伯林对犹太人必须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的强调,无疑和他对自己犹太身份的敏感体验有密切的关系。但与其说它反映的只是一种绝对的特殊性,还不如说正因为有那种独特的敏感体验,伯林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和意识到某种在许多互不相同的个别的、具体的场合都可能表现出来的特殊归属情怀。事实上,在最早揭示这种家园感的重要性的赫尔德那里,他谈论的对象根本就不是犹太人。
争取一个能实现内部自决或自治的家园的权利,当然不能够被看作只是一种文化的权利,而只能是用来保障独特的民族文化赖以保存和发展的政治权力。从这一角度看问题,把伯林赞同的民族主义的基本性格理解为主要是文化民族主义,可能就不太周全了。因此我觉得还是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见解更加使人信服。他说,伯林既拒绝放弃特殊的归属情怀,又拒绝放弃普遍的善的意愿。像这样的双重拒绝,只能驱使他滑向一种可以叫作“自由民族主义”的立场。
自由民族主义不是一个从逻辑上可以自恰的、严密的思想理论体系,但它反而更加彰显出伯林特色的“狐狸”的智慧。他不但用消极自由观念来对抗启蒙运动以理性名义推行另一类甚至更带窒息性、更残酷严厉的专制的危险倾向,而且也采纳被他认为是由反抗18世纪理性主义的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所建构的民族主义思想养料,用来为正在遭遇“受唯一的普遍标准支配的统一领域”压制和扼杀的不同文明,以及同一文明的不同阶段所蕴含的最为宝贵的人类文化多样性进行有力辩护。他是一种示范,提醒现代人应当同样地珍视和继承18及19世纪的西方留下来的两种几乎针锋相对的思想传统。这两种传统已经如此深刻地以互相夹缠的形式渗透到现代思想里,只要看一看民族主义怎样从体现着启蒙立场的主权在民原则中起步,在浪漫主义的塑造下转身成为族裔民族主义,同时却仍旧保持着启蒙运动的极端姿态,就不难体会了。因此,像伯林那样的观念史梳理,像伯林那样针对每一个具体的、个别的场景,在互相冲突的原则之间勉力去寻求某种很可能带着脆弱平衡性格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奢望获得一种根本性的、一劳永逸的解救,尤其显示出对我们的重要性。
鉴于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以赛亚·伯林与中国”,所以我还想在最后简要地谈一谈,他关于家园感的见解对我们思考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所可能产生的启发。
一个民族或族裔群体是否拥有一片可以被认为是属于他们自己家园的土地,对这个民族或族群的每一个成员,无论他们当下是否或者是否打算在未来生活在那块土地上,都同样会是最被珍爱的精神资源。你可能经常甚至长期不在家,但有家的感觉依然使你不孤独。我们不难认识到,当今世界上的大部分现代民族国家,其实都是多民族国家。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像康诺尔(Walker Connor)所从事过的分析那样,在多民族国家中再分辨出“只有一个拥有家园的民族的多民族国家”(unihomeland multination state)、“有诸多个拥有家园的民族的多民族国家”(multihomeland multination state),以及“没有拥有家园的民族的多民族国家”(non-homeland multination state),等等。仅仅停留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识上,我们还不能看出,中国与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到底有没有区别?如果有,这个区别究竟在哪里?它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又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康诺尔对多民族国家的分类,凸显出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即它的版图覆盖着多达数十个久远以来即分别属于各庞大的少数民族或大规模边缘人群的生存活动地区。在当今大部分现代民族国家经由着从过去帝国(包括殖民帝国)统治中分裂出来的道路而诞生时,中国却几乎完整地把它在帝国时代的疆域纳入了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边界之内。当代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全部特殊性,归根结底就是从这里产生的。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对中国长期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非但不存在任何可以怀疑动摇的理由,并且只能在不断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平台上对它更全面和坚决地予以进一步落实。倘若我们真的愿意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地爱护和捍卫国家的统一,我们就必须针对这个至关重要的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特殊性问题,不断地展开更敞开心胸的、深思熟虑的探索。
如果伯林还活着,如果他也关注到中国民族问题的现实与前景,那么,他又会向我们发表什么样的评论呢?
(原载刘东、徐向东主编:《以赛亚·伯林与当代中国:自由与多元之间》,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