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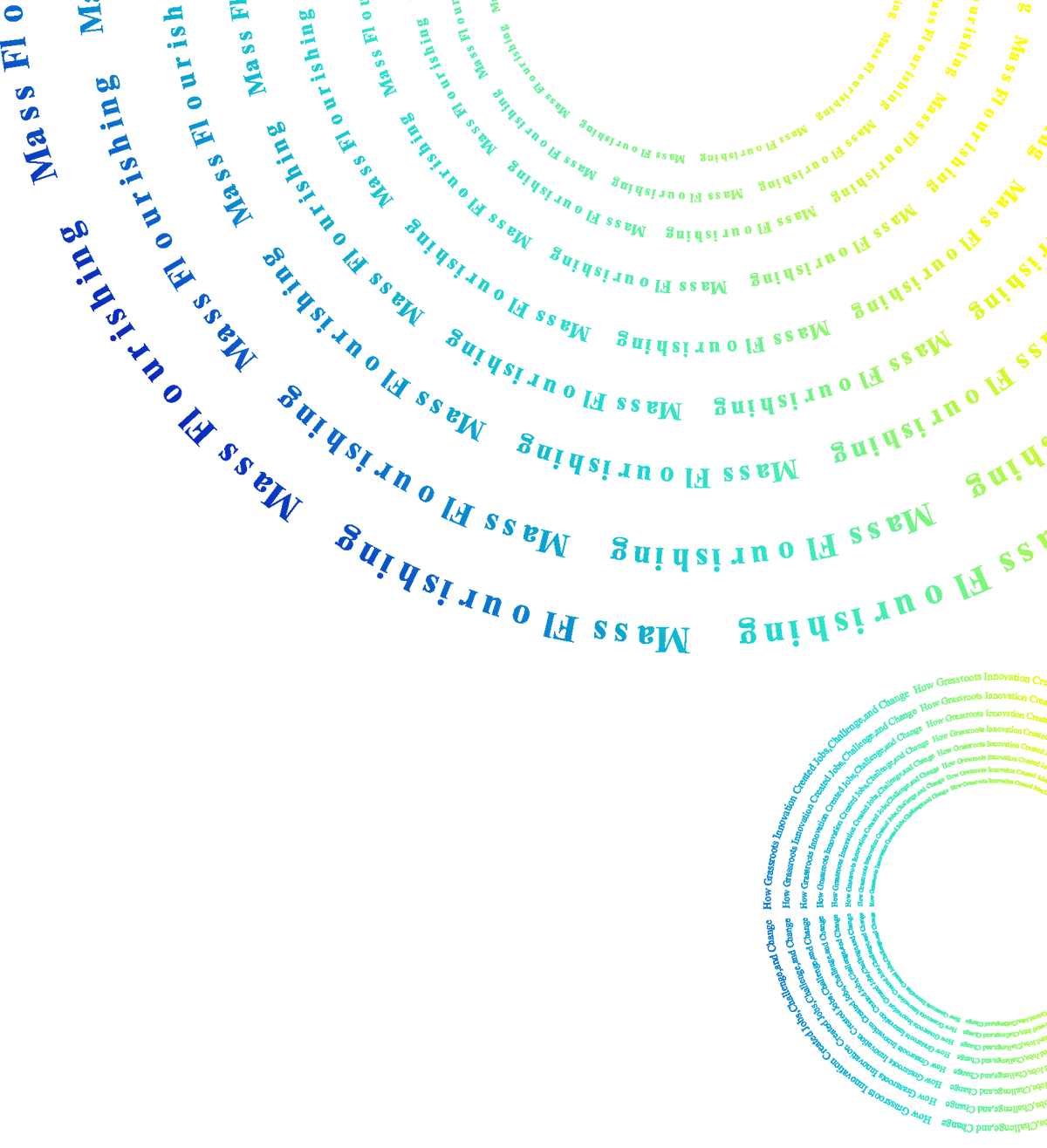
古巴比伦有空中花园,古埃及有金字塔,雅典有卫城,罗马有大竞技场,布鲁克林有大桥。
——1883年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开通仪式上的标语
我们在前一章里通过结构剖析确定了经济的不同类型,而这些经济类型的真正意义在于其影响。现代经济的到来使几个国家的生产率水平从19世纪开始持续增长,并且产生了划时代的结果。卡尔·马克思虽然反对自己身边的经济制度,但丝毫没有忽视这种持续增长的重要意义。1848年,在现代经济体还没有达到最快成长速度之前,马克思就已经注意到了生产率问题,提出了现代经济体的“进步性”。
 如第一章所述,生产率的增长具有全球意义,因为新工艺和新产品可以被其他经济体接受和采用,甚至包括很多较为原始的经济体。我们看到,某些国家起步较早的现代经济在20世纪之后出现现代性的退化,例如法国,可以说到“二战”后的某个时期已丧失了大部分经济活力。还有些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转变为非现代或反现代性质,例如德国。不过,也有些国家的经济变得更为现代了,例如加拿大和韩国。因此总的来说,现代经济生存了下来,而且至少在大多数市场环境中,某些现代经济体保持着大范围的创新活力并由此取得了成功。
如第一章所述,生产率的增长具有全球意义,因为新工艺和新产品可以被其他经济体接受和采用,甚至包括很多较为原始的经济体。我们看到,某些国家起步较早的现代经济在20世纪之后出现现代性的退化,例如法国,可以说到“二战”后的某个时期已丧失了大部分经济活力。还有些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转变为非现代或反现代性质,例如德国。不过,也有些国家的经济变得更为现代了,例如加拿大和韩国。因此总的来说,现代经济生存了下来,而且至少在大多数市场环境中,某些现代经济体保持着大范围的创新活力并由此取得了成功。
本章的目标是让读者了解运转良好的现代经济的活力和影响。我们可能无法准确解释很多奇迹出现的原因,但奇迹般的现代经济是在特殊时刻出现的,当时并没有其他大事发生,因此我们可以将19世纪与18世纪的生活状态的巨大差异归结为现代经济诞生的影响。对现代经济产生的这些影响的检测非常接近于实验室里的工作。当然我们首先需要注意,不关心水平的提高,只关心最终达到的高水平是没有意义的。就像电影业从业者爱说的:“你的表现只不过和上部片子齐平。”同时,如果处于很低的绝对水平,只谈增长也没什么意义。
最后,我们感兴趣的是现代经济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更确切地说是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影响。人均产出和平均工资这样的数据不具有说服力,它们并不能充分反映现代经济体中的实际生活:在那几十年里,这样的产出和实际工资能买到什么,获得这样的产出和工资的经历又能带来什么收获?我们希望了解现代经济体如何改变了工作与生活,最好是真实而广泛地调查参与者的各种付出和收益。
本章和下一章将指出,现代经济体及其背后的现代性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大部分是正面的。本章将分析现代经济体的有形的影响,即物质带来的愉悦和关怀;下一章主要分析无形的影响,它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意义。
现代经济体带来了人均产出(劳动生产率或简称生产率)的持续攀升,并且延续至今。从定性的角度看,进入现代经济的国家(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被卷入全球经济的国家)从静止状态跃升到爆炸式的无尽增长状态。如果每年的生产率增幅只有0.5%或更低,很多人可能根本注意不到变化,因为以这样的速度,需要144年才能使人均产出翻番。现代经济不但带来了没有止境的增长,还带来了真正快速的增长。
人均产出在那个所谓的漫长世纪(到“一战”为止)的增幅之大令人激动。到1870年,西欧的人均产出比1820年提高了63%;到1913年,又比1870年提高了76%。在英国,该指标在这两个阶段分别提高了87%和65%。在美国,分别是95%和117%。对熟知中国在1980—2010年增长奇迹的当代读者来说,上述增幅或许不算什么,但中国可以从海外借鉴大量的生产经验,而当年的欧洲和美国却只能自己摸索。
从起飞阶段到1913年的累计增幅使英国和美国的人均产出分别增长到原来的3倍和4倍,给普通人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18世纪的人们不可想象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革命性的直接影响,之后的章节还将详述,另外还有间接影响:随着经济体的总产出和总收入不断增长,家庭财富与收入的比例将发生变化。在过去的静止状态下缺乏储蓄的人们开始增加储蓄,收入越来越多,储蓄也越来越多,这使财富存量的增速不至于过分落后于收入的增速。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将看到现代经济中的劳动参与率远远高于商业经济时代,只是苦于没有数据可以验证这一猜想。
工资(而非生产率)是最重要的反映物质收益的指标,尤其是对那些没有太多继承财富的普通人而言。足够高的工资是通向重要福利的大门,至今依然如此。尤其在19世纪,普通人能赚取的工资是他所能负担的必需品的决定性因素,包括住房、医疗等。工资还能满足所有人内心都渴望的非物质需求,例如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拥有家庭、参与社区生活的权利。
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总能实现工资的提高,反之,在生产率没有提高时,工资也有可能提高。本书曾提到,极负盛名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发现,虽然16世纪的伟大探险家和殖民者给国王带回了大量白银,但这些收入却没有推动工资的提高。
 尽管人均工资与人均产出之间存在相关性(有人曾说经济学中的任何指标之间都至少通过两种渠道相互作用),但从生产率到工资的影响渠道可能受到其他特殊因素的影响。但不必担心,现代经济体的确使劳动者的工资得到了大幅提高,实现了天量的白银没有达到的成就。
尽管人均工资与人均产出之间存在相关性(有人曾说经济学中的任何指标之间都至少通过两种渠道相互作用),但从生产率到工资的影响渠道可能受到其他特殊因素的影响。但不必担心,现代经济体的确使劳动者的工资得到了大幅提高,实现了天量的白银没有达到的成就。
有关工资的讨论曾谈到,现代经济体的出现打破了布罗代尔观察到的悲观发展模式。我曾指出,在现代经济体出现前的16世纪、18世纪以及1750—1810年,工资水平在下降——至少有数据表明英国属于此种悲惨情况。但是从1820年左右开始,英国手工业者的人均工资(如果用真实水平或者购买力计算)持续提高,与人均产出的起飞基本同步。在比利时,工资从1850年左右开始增长。法国的工资水平随后起飞,一直紧随英国,直至1914年。在德国各城市,工资水平像坐上了过山车,从19世纪20年代早期到整个40年代一直在下降,由此引发了1848年的暴动,1860年后又开始持续增长(另一项资料显示是从1870年开始)。可惜美国没有那么早的数据。总之,现代经济体中的建筑工人、工厂工人和农场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都伴随着生产率的起飞而高涨。
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工资是否表现出了与人均产出同样显著的增速?如果劳动在产出增量中所占的收入份额下降,工资增速或许会落后于生产率。实际上,普通的城市非熟练男性工人的名义日工资(以当地货币计算)不但能跟上人均产出的货币价值的增速,甚至还更快。1830—1848年(又是那个糟糕的年份),英国的工资—生产率比略有下降,到19世纪60年代终于赶上并超出了以前的水平,70年代再度下降,此后到90年代再度超出,直至1913年。法国的这个比值反映出了类似的变化趋势。在德国,工资—生产率比在1870—1885年保持稳定,到19世纪90年代有所恶化,但到20世纪前10年时已提到很高的水平,直至“一战”爆发。此外,这些数据并未反映出这么一个事实,即各国工人的收入并不都用来购买国内产品:由于供应量增加、运输成本下降,他们实际上购买了大量价格更低的进口消费品。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在长期停滞后,实际工资水平在1820—1850年几乎翻番。”
 因此,现代经济中工资收入相对于非工资收入的份额下降的观点并不成立。当然,弱势群体、下层社会民众的工资水平在这些经济体中的变化趋势可能有所不同。
因此,现代经济中工资收入相对于非工资收入的份额下降的观点并不成立。当然,弱势群体、下层社会民众的工资水平在这些经济体中的变化趋势可能有所不同。
在公众看来,对那些不得不在工厂、矿山和家政行业中谋职的底层工人来说,19世纪兴起的新经济制度简直是人间地狱。有人认为,这种社会状况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没有改善,直到社会主义思潮席卷欧洲、美国兴起新政之后才发生变化。有的文学作品可能会给人这样的印象,但描写的年代并不吻合。例如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 Les Misérables )主要描述了1815—1832年的路易·菲利普王朝的社会紧张状况,而不是反映几十年之后出现于法国的现代经济的阴暗面。当然,19世纪中叶的许多作品也很出名。狄更斯在1839年出版的小说《雾都孤儿》( Oliver Twist )中细致地描述了伦敦的贫困现象,奥诺雷·杜米埃的画作生动地刻画了持续到1870年的巴黎工人抗争运动。它们给人的印象是,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大量劳动适龄人口因为工资水平下降而受苦,或至少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陷入悲惨、失业和空虚的状态。这种说法需要得到验证。
验证办法之一是,在现代经济开始确立并发挥效力时,测算所谓的工人阶级(手工劳动者或其他体力劳动者)的蓝领工资水平是否停滞或下降。那么实际情况是这样吗?人们的普遍印象是,由于机械化水平提高,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在19世纪有所下降,至少是相对于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而言。
但事实上这又是一个错觉。根据之前提到的英国的研究,在1815—1850年,平均工资水平的增幅比蓝领工资水平的增幅多出了20%,但这主要是由于农业中的体力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停滞,而农业的困境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现代产业的影响。另一项资料估计,在那一时期,英国非农业部门的所有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的增幅仅比非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的增幅多出7%。
 克拉克在2005年整理的关于英国手工业者和建筑业帮工的日工资数据显示:18世纪40年代之后,两者的相对工资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从19世纪第一个10年开始,帮工的工资涨幅不及工匠;但从19世纪中叶起趋势发生改变,到19世纪90年代,已回到之前的相对水平,在之后的10年里帮工的工资增速依然更快。那个时代的人也提到过这样的印象。例如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就看到各类工资收入者缴纳的税收均快速增长,他在下议院评论说:
克拉克在2005年整理的关于英国手工业者和建筑业帮工的日工资数据显示:18世纪40年代之后,两者的相对工资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从19世纪第一个10年开始,帮工的工资涨幅不及工匠;但从19世纪中叶起趋势发生改变,到19世纪90年代,已回到之前的相对水平,在之后的10年里帮工的工资增速依然更快。那个时代的人也提到过这样的印象。例如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就看到各类工资收入者缴纳的税收均快速增长,他在下议院评论说:
如果像我原本认为的那样,这样不同寻常的税收增长只来自处境优越的阶层,那我会感到有些难过,但比较容易理解……然而……看到富人在变得更为富有的同时,穷人的情况也有所改善,则给人莫大的安慰……我们可以看看英国劳动者的普遍状况,不管是农民、矿工、操作工还是技工,各种无可争议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在过去20年里他们的生存条件都得到了巨大的改善。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宣布,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

在当时的英国,现代经济并没有拉大工资收入的差距,至少没有系统性和持续性地拉大差距。
所谓劳动者在19世纪的整体收入的增长速度慢于资本的说法,也和其他误解一样缺乏根据。最近得到的数据显示了单位雇员的日工资与国家人均产出的比值。在英国,这一比值呈上升而非下降趋势,从1830年的191升至1910年的230。在法国,该比值从1850年的202提高到1910年的213。德国则从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199提高到20世纪初的208。
 1887年,英国记者(兼政府首席统计师)罗伯特·吉芬对此进行了规范的记述,他收集了1843年英国开征所得税之后的个人收入数据,表明在其后的40年里“富人”的总收入翻番,但其人数也翻番,体力劳动者的总收入增幅超过一倍,而其人数增加有限。
1887年,英国记者(兼政府首席统计师)罗伯特·吉芬对此进行了规范的记述,他收集了1843年英国开征所得税之后的个人收入数据,表明在其后的40年里“富人”的总收入翻番,但其人数也翻番,体力劳动者的总收入增幅超过一倍,而其人数增加有限。
富人的人数多了,但平均来说,每个人的富裕程度并未提高;穷人的平均收入几乎是50年前的两倍。因此,过去50年来巨大的物质进步的好处几乎全部落到了穷人的头上。

尽管在19世纪的几十年里,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依然较低,但实际工资水平的上升趋势仍然可以带来两方面的好处,具有明显的社会价值。好处之一是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解放了人们,使那些工资水平较低的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非熟练工人)能够从以前不得不从事的工作转移到更合心意的工作。例如,在“家政经济”中做家庭主妇或者在别人家做帮工的人可以转移到不那么孤独的职业中去;在地下经济中工作的人可以到合法的经济部门谋取职位,获得更多的尊重,减轻人身依附;有的人可以离开原来的岗位,寻求回报更多的机会,如能发挥更多主动性、能承担更多职责和需要更多交流的岗位。通过这些机制,工资的提高会使我们常说的经济包容性增强,使更多的人参与社会的核心项目,并获得相应的回报。对经济包容性的描述和肯定将在下一章里详细讨论,此处暂不展开。
工资的提高还有其他社会意义,例如减少贫困现象。当时的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观察得出结论,19世纪的所有现代经济体的贫困现象都显著减少,至少有数据记录的经济体是如此。1887年,在讨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变化趋势时,吉芬注意到赤贫者(免于偿还债务的个人)的数量持续下降,从19世纪70年代上半叶的4.2%降至1888年的2.8%,这还是在人口增速创纪录的情况下实现的。吉芬同时发现,在现代经济来得更晚的爱尔兰,“赤贫人数增加,同时总人口数量下降”。戴维·威尔斯在19世纪90年代分析美国的情况时,在讨论赤贫现象的两页文字中提道:“穷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通常在下降,尽管核查赤贫现象存在很多困难,尤其是在美国这样每年都从欧洲国家接纳大量贫困人口的国家。”
 对于现代经济损害了民众利益的说法,还有一种验证办法,即核查传染病、营养状况及死亡率方面的数据。结果与上面的情况相似,并不是简单的直线改善。数据表明,这些指标自18世纪开始发生变化,到19世纪改善尤为显著。令人惊讶的是,主要造成幼儿死亡的天花导致的死亡数量从17世纪到18世纪中叶的商业经济全盛期一直在上升,导致2/3的儿童在5岁前夭折。天花流行的原因不能归咎于现代经济(因为现代经济在当时还几乎没有充分运转),而是由于国际贸易的增加:随着全球贸易量的增长,各国进口了更多被感染的动物品种。此后,天花导致的死亡率开始下降,到19世纪的第二个25年,儿童死亡率下降了2/3。促成这个改善的原因似乎更像是19世纪前10年起步的现代经济,而非18世纪70年代爆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如前所述,那场工业革命仅限于单一的产业部门,时间也较短。
对于现代经济损害了民众利益的说法,还有一种验证办法,即核查传染病、营养状况及死亡率方面的数据。结果与上面的情况相似,并不是简单的直线改善。数据表明,这些指标自18世纪开始发生变化,到19世纪改善尤为显著。令人惊讶的是,主要造成幼儿死亡的天花导致的死亡数量从17世纪到18世纪中叶的商业经济全盛期一直在上升,导致2/3的儿童在5岁前夭折。天花流行的原因不能归咎于现代经济(因为现代经济在当时还几乎没有充分运转),而是由于国际贸易的增加:随着全球贸易量的增长,各国进口了更多被感染的动物品种。此后,天花导致的死亡率开始下降,到19世纪的第二个25年,儿童死亡率下降了2/3。促成这个改善的原因似乎更像是19世纪前10年起步的现代经济,而非18世纪70年代爆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如前所述,那场工业革命仅限于单一的产业部门,时间也较短。
 随着现代经济体在19世纪的增强,天花导致的死亡率加速下降。威尔斯在报告中说:“在1795—1800年,伦敦的年均天花死亡人数是10 180人,到1875—1880年已下降到1 408人。”
随着现代经济体在19世纪的增强,天花导致的死亡率加速下降。威尔斯在报告中说:“在1795—1800年,伦敦的年均天花死亡人数是10 180人,到1875—1880年已下降到1 408人。”

主要影响成人而非儿童的传染病的危害在19世纪也迅速降低。威尔斯提道:“鼠疫和麻风病在英国和美国几乎消失了。斑疹伤寒曾经是伦敦的痼疾,如今据说已从这个城市完全消失。”死亡率因此大幅下降。“伦敦在19世纪60年代的平均死亡率为24.4‰,1888年已降至18.5‰。维也纳的死亡率从41‰降至21‰。在欧洲其他国家,死亡率降幅约为1/4~1/3。美国的死亡率降至1880年的17‰~18‰。”

这些是否应该归功于科学?专家们的看法并非如此。拉泽尔和斯宾塞指出,伦敦市的各种传染病的危害全面降低,包括天花、热病(斑疹伤寒和伤寒)和抽搐病(痢疾和肠胃病),应该是收入提高所带来的公共卫生和健康措施改善的结果:
这些疾病中的大部分都是卫生状况不佳引起的。死亡率的降低程度在富裕人群和非富裕人群中几乎相同……有可能是环境的改变对疾病发生率产生了影响……用亚麻和棉织品替代了羊毛衣物,出现了更好的洗涤方法,包括将衣物煮沸,这些可能是逐步消灭斑疹伤寒和虱子的原因。

威尔斯还指出,高收入促进了饮食的改善:
虽然卫生知识和监管措施的改进也有作用,但食品供应的丰富和廉价才是主要原因,这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和分配方式的改善……美国人的身高和体重明显增加,如果大众的生活水平下降,这种情形是不可能出现的。

通过这些途径,现代经济帮助降低了发病率和死亡率。经济生活的生产率提高给家庭和社区提供了以日常的私人和公共卫生手段对抗疾病的必要条件。医院条件的改善,例如防腐剂的使用,有助于控制传染病的传播。此外,现代医院是现代经济的组成部分,医院中得到的新观察和新知识及其在整个医疗卫生产业的传播,是现代经济所产生的知识爆炸中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
随着现代经济体的发展和生产率提高扩散到其他国家,世界进入了良性循环。死亡率降低使年轻人口数量增加,也就有了更多可以发明、开发和尝试新创意的人,从而可以推动新一轮的工资提高和死亡率下降。
现代社会中工资的增长令读者感到吃惊,他们或许会想,现代经济体的兴起对就业或失业的影响的传统看法是否也需要纠正。就在2009年,英国记者马耶夫·肯尼迪在看到大英图书馆刚放到网上的记录百年历史的英国报纸时评论说:“被今天的政治丑闻、战争、金融灾难、高失业率和儿童酗酒现象困扰的人都可以到19世纪去找借口,去看看那时的战争、金融灾难、政治丑闻、高失业率和醉酒的儿童。”然而,大规模失业源于造就了第一批大城市的18世纪的商业经济。此前,大多数人都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偶尔会加入间歇性的雇佣劳动或者说“工薪阶层”,在那种生活状态下不存在失业问题。商业时代来临后,很多人移民到城市,失去雇佣岗位意味着几乎没有其他办法获取生存条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尽量储蓄,以应对失业的风险。在无能为力时,需要互助会(行会)向手工业者提供帮助,很多人还求助于亲朋好友。政府负责的失业保险项目直到1905年和1911年才分别在法国和英国出现。
现代经济体在19世纪的兴起大大增加了城市的数量,也使失业人数剧增。一个国家的城市数量及失业人数快速增加,同时就业不足的农村出现萎缩,此时全国的总失业人数难免会有所增加。但这并不绝对都是坏事。对城市居民而言,的确存在失业的风险,但也存在获得某些利益的机遇,这才会吸引人们涌入城市。许多人加入城乡移民的队伍,他们在权衡利弊后认为值得这样做。
我们目前没有数据判断,现代经济是否使老城市的平均失业率高于一个世纪之前的平均值。但已有数据显示,19世纪劳动力参与率有所提高(女性),而失业率并没有超过今天的水平(例如自1975年后的平均失业率)。最近,法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趋势变化最早出现于19世纪50年代,60年代之后得以持续,尽管劳动适龄人口的增长突然停滞,就业人数的增长仍在加速。”
 有证据表明,是现代经济在法国的出现将更多的劳动适龄人口吸引到了非农业岗位上,而不是说农业部门存在排斥他们的因素。在英国,A.W.菲利普斯的经典研究追溯了1861年以来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数据显示,在现代经济制度及其带来的知识创造和变革力量的几十年发展期内,并没有出现失业率上升的趋势。在菲利普斯的数据系列早期阶段(1861—1910年),失业率没有明显上升,相比之下,1971—2010年的情况却很糟糕:在这个时间段,英国已不是知识和创新方面的领跑国家。我们由此得到的启发是,快速的知识增长以及生产率和工资的提高通过多种渠道控制住了失业水平,而今天的英国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创造力下降,已很难做到。无数的补贴项目和政府机构成功地减轻了低收入群体的失业现象,但未能扭转这一趋势。
有证据表明,是现代经济在法国的出现将更多的劳动适龄人口吸引到了非农业岗位上,而不是说农业部门存在排斥他们的因素。在英国,A.W.菲利普斯的经典研究追溯了1861年以来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的关系,数据显示,在现代经济制度及其带来的知识创造和变革力量的几十年发展期内,并没有出现失业率上升的趋势。在菲利普斯的数据系列早期阶段(1861—1910年),失业率没有明显上升,相比之下,1971—2010年的情况却很糟糕:在这个时间段,英国已不是知识和创新方面的领跑国家。我们由此得到的启发是,快速的知识增长以及生产率和工资的提高通过多种渠道控制住了失业水平,而今天的英国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创造力下降,已很难做到。无数的补贴项目和政府机构成功地减轻了低收入群体的失业现象,但未能扭转这一趋势。
那么,为什么现代经济体一直被糟糕的声誉所困扰——包括19世纪和之后出现的现代经济体?它们都被贴上了威廉·布莱克的“黑暗的撒旦磨坊”的标签。他创作这一作品的时间是1804年,正处于工厂出现前的那个10年。过程艰辛、待遇微薄的农业劳动大多数会被各种工厂中常见的枯燥、脏乱和喧闹的场景取代。查理·卓别林在1937年的电影《摩登时代》( Modern Times )中展现的生产线,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愚笨无知,而非极具压迫性。无论如何,工厂并不是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经济体的特有现象,某些缺乏现代性的经济体也出现了类似的甚至更糟糕的工厂景象,如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而且,工厂的兴起并非任何阶段的现代经济的必然产物,未来走向现代社会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跨越工厂阶段,直接进入办公室和网络经济阶段。
可能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对我们而言,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可能对19世纪兴起的现代经济体快速蔓延的城市肮脏和令人窒息的污染状况感到吃惊。但我们可能忘了,这对于那些刚刚摆脱中世纪的微薄报酬,收入水平提高了两三倍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就是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大多数人在19世纪切切实实获得的收益。收入水平虽然是一个非常抽象、毫无生机的数字,但更高的收入降低了贫困发生的概率。
对那些成功建立现代经济的国家而言,它们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随着收入的提高,更多人获得了自立的尊严,他们得以解放出来,加入社会生活,开辟了与乡村不同的城市生活的选项。随着收入的提高,生活水平在很多基本方面得到改善,疾病造成的早亡风险降低,使人们可以有更长的寿命享受新生活。新的中产阶级大量涌现,他们可以外出用餐,去体育馆或剧院休闲,让子女接触艺术活动。有人说,每个美国家庭的客厅似乎都有一架钢琴。
如今看来,这种“持续增长”似乎已不再重要。与消费和健康状况很差的当年相比,对现代人来说,更高的收入水平已没有那么重要,例如,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的工作日和工作周的数量大幅减少。本书的主题之一是,对现代经济体中数量不断增加的人群而言,工资的持续增长已不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10年之前开展的一项有关“幸福”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家庭调查数据显示,在达到某个数量后,收入更高的人并没有报告更高的“幸福指数”,就像佛教徒不再需要更多的消费和休闲一样。此外,收入的提高往往伴随着更重大的责任。当然也有后续研究者从类似的数据中得出上述观点并不准确的结论。但不管上述结论准确与否,我们都知道“金钱买不来幸福”。幸福与收入没有必然联系,获取高收入是获取满足的手段,这种满足不属于“幸福”。相反,人们的收入不足会对实现很多重要目标构成障碍,如实现个人发展和获得满意的生活。现代经济体的巨大成功就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使因为收入短缺而不能实现非物质目标的人越来越少。
当然,如果现代经济没有在西方兴起,依然由巴洛克时代的商业经济主导,随着可能出现的科技进步(不管具体是哪些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外生影响,工资水平和收入同样可以提高,但工资和收入的提高速度绝不可能那么快。如果外生的科技因素是19世纪少数西方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那这样的科技进步应该能产生水涨船高的普遍推动作用,会同时抬升荷兰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这两个国家在刚进入19世纪时相对来说具有生产率优势。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在1820年左右都处于类似的起跑位置,但后来少数国家的物质进步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这个事实反映了现代经济体取得的杰出成就。
总之,本章不但定量分析了现代经济的出现给少数国家带来的快速增长,还通过证据表明,现代经济扎根以后,通过永不停歇的新经济知识的创造,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现代经济体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它们的体制结构能够很好地推动和实现大众参与的创新。
 大众参与的创新自下而上渗透至整个国家。与这种创新的草根性质一致,收入等方面的收益也较为平等地被很多弱势群体分享,健康和长寿等其他收益也更多地流向弱势群体。正如最近出版的反映这段发展历程的美国历史书所言,这是一场经济“革命”,“在很多方面是之前从未降临到美国普通民众身上的最大福祉”。
大众参与的创新自下而上渗透至整个国家。与这种创新的草根性质一致,收入等方面的收益也较为平等地被很多弱势群体分享,健康和长寿等其他收益也更多地流向弱势群体。正如最近出版的反映这段发展历程的美国历史书所言,这是一场经济“革命”,“在很多方面是之前从未降临到美国普通民众身上的最大福祉”。

物质方面的进步并非现代经济的唯一成就,它在非物质的、无形的方面带来的改变(包括体验、理想、精神和想象力)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同样翻天覆地。这些将是下一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