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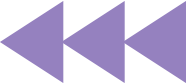
时间到了第四天早上。
“咦,耳朵里怎么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劳拉一边想,一边掀开被子一角,向外偷偷张望,却发现床上到处都是调皮的雪花。接着传来了火炉盖轻轻碰撞的声音,以及火焰燃烧时噼噼啪啪的声音。这时她才恍然大悟,难怪耳朵里空荡荡的,原来是暴风雪停了!
“快醒醒,玛丽!”她一边兴奋地大喊,一边用手肘碰了碰玛丽,“暴风雪停了!”
劳拉一下子跳下温暖的床,屋里的空气比寒冰更冷。炉火虽然烧得很旺,却似乎一点儿热气也没有。水桶里的雪水几乎冻成了硬邦邦的冰块。挂着霜花的窗户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
“屋里屋外一样冷。”走进屋时爸说道。他弯下腰,让火炉的热度融化胡子上的冰凌。冰凌落在炉子上,嘶嘶直响,转眼就化成了袅袅上升的水蒸气。
爸擦了擦胡子,继续说:“钉在屋顶上的沥青纸被风撕开了一个大口子,难怪屋顶又漏雨又飘雪。”
“反正暴风雪结束了。”劳拉愉快地说。她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看着洒落在玻璃上那金灿灿的阳光,心情大好。
“我们还会迎来温暖的天气的。”妈的语气中充满了肯定,“这场暴风雪来得太早了,不可能这么早就进冬天的。”
“我也从不知道冬天会来得如此之早,”爸附和道,“不过有些事总让我觉得不对劲。”
“什么事,查尔斯?”妈好奇地问。
具体是什么事,爸也说不上来,只是含糊地说:“干草堆旁有几头迷路的牛。”
“它们把干草堆弄垮了吗?”妈赶忙问道。
“没有。”
“既然它们没有搞破坏,那有什么好烦恼的呢?”妈有些不解。
“我猜它们是被暴风雪弄得筋疲力尽,”爸说,“于是把干草堆当作避难所。我原打算让它们休息休息,吃点东西,再把它们赶走。可万一它们把干草堆弄垮了,那就糟糕了。不过只要它们不捣乱,吃些干草是可以的,可谁知道它们什么也没有吃。”
“出了什么事吗?”妈又问了一句。
“没事,”爸回答,“它们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妈说。
“没错。”爸喝完茶,继续说,“我得把它们赶走。”
他穿上外套,戴上帽子和手套,推门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妈说道:“劳拉,你去看看,你爸可能需要帮手,你去帮他赶赶牛。”
劳拉飞快地用妈的大披肩裹住头,将别针牢牢地别在下巴下面。羊毛披肩把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双手也藏在披肩下,只剩下一张小脸蛋露在外面。
屋外强烈的光线一时间刺得眼睛生疼,她深深地吸了一口冷空气,眯着眼左右张望。辽阔的天空蔚蓝无边,地上则是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直吹的狂风没有把雪花刮起来,只是让它们低低地掠过大草原。
寒冷的空气刺痛了劳拉的脸颊,又钻进她的鼻子,弄疼了胸膛,最后化作一团雾气,被呼了出来。她拿起披肩一角捂住嘴,呼出来的气立刻在披肩上结成了霜。
走到马厩转角处,劳拉一眼就看见了爸和牛群。于是她停住脚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眼前的景象。
阳光下,干草堆的阴影里站着一群牛,颜色各异,有红色的、棕色的、斑点的,还有一头瘦弱的黑牛。所有牛一动不动地站着,头低垂在地上,毛茸茸的红色脖子与棕色脖子下是巨大的、肿胀的白色脑袋。这些牛一个个瘦骨嶙峋的。
“爸!”劳拉大声喊道。爸示意她待在原地,自己继续在雪地中迈着艰难的步伐,慢慢地向牛群靠近。
这群牛看上去不像真牛,像是被施了定身术,纹丝不动,连最细微的动作也没有。它们只是在呼吸的时候,肋骨之间毛茸茸的肚子才会一鼓一缩的。臀骨和肩胛骨尖尖地凸起,四条腿僵硬地、一动不动地支撑着身体。再瞧瞧那肿胀的白色大脑袋,似乎在纷飞的大雪中被牢牢地冻在地面上。
劳拉感到头皮发麻,脊梁骨发凉,恐惧感爬上后背。刺眼的阳光和呼啸的冷风刺得她流泪,冰凉的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爸迎着风,继续慢慢地向牛群走去。牛群依然静静地站在原地,仿佛没有生命的雕塑。
爸先停下来观察一番,接着弯腰飞快地做了什么。劳拉只听见一声吼叫,一头红色小公牛弓着背跳了起来,一边摇摇晃晃地走着,一边大叫,正常的牛头上长着眼睛、鼻子,张开的嘴吐出团团白气。
另一头牛也跟着号叫起来,跌跌撞撞地跑了一小段路。接着又有一头牛叫喊着奔跑起来。爸依次对每头牛做了同样的事。牛群的吼叫声响彻云霄,久久回荡在冰冷的天空中。

最后,所有牛一同静悄悄地走进了深及膝盖的雪地,渐行渐远。
爸向劳拉挥挥手,示意她赶快回屋,自己留下来检查干草堆。
“你怎么在外面待了这么久,劳拉?”妈问道,“那群牛钻进干草堆了吗?”
“没有,妈,”劳拉回答,“它们的头……我猜它们的头被冻在地上了,所以动弹不得。”
“这怎么可能!”妈惊呼。
“肯定是劳拉在胡思乱想。”玛丽坐在火炉旁的椅子上,忙着做针线活儿,头也不抬地说,“你倒说说看,牛的脑袋怎么可能被冻在地上呢?劳拉,有些事被你一说真叫人担心哪。”
“你们不信问爸好了!”劳拉毫不客气地说道。她无法告诉妈和玛丽自己的感受。不知道怎么回事,她隐隐觉得,在这个狂乱的暴风雪之夜,在大草原各种纷杂的声音之下,有一种死寂的力量牢牢地控制住了这群牛。
爸回来后,妈问:“牛群出了什么事,查尔斯?”
“它们的头和冰雪冻在一起了,”爸说,“呼出来的气体遇冷结冰,冻住了眼睛和鼻子,它们既看不见,也无法呼吸。”
听到这里,正在扫地的劳拉停了下来,惊恐地说:“爸!它们差点被自己的呼吸害死了。”
爸理解她的感受,说道:“现在它们没事了,劳拉。我把它们头上的冰块打碎,它们又能顺畅呼吸了,我猜牛群会找到地方躲避风雪的。”
卡瑞和玛丽听得目瞪口呆,连妈也是一脸害怕的神色。她随即简明地说:“快扫地,劳拉。我的天呀,查尔斯,你怎么不把外套脱掉烤烤火?”
“我有东西要给你们看。”说着,爸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口袋,“快瞧,孩子们,看看我在干草堆里发现了什么。”
说话间爸慢慢地张开了手。天啊,手套里竟然站着一只小鸟。爸轻轻地把小鸟放进玛丽的手中。
“天呀,这小家伙站得多么笔直呀!”玛丽难以置信地叫了起来,用指尖轻轻地碰了碰小鸟。
这种鸟大家还是第一次看见。虽然个头小小的,但看上去和爸那本绿皮大书《动物世界奇观》里的海雀的图画一模一样。
瞧,它长着同样白色的胸脯、黑色的背和翅膀,同样短小的腿,同样有蹼的大脚。小短腿支撑着整个身体的重量,直直地站立,活像一个穿着黑外套、黑裤子、白衬衣的小人儿,一对黑色的小翅膀好似两只手臂。
“这是什么,爸?哦,这是什么呀?”卡瑞的语气中带着欣喜。格蕾丝好奇地想摸摸看,却被卡瑞一把拽住,“不许碰它,格蕾丝。”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鸟,”爸说,“肯定是在暴风雪中飞不动了,掉在干草堆上,于是索性爬进干草堆里躲避风雪。”
“这是海雀,”劳拉说,“只不过是个小不点儿。”
“这只鸟已经成年了,不是雏鸟,”妈细细观察后,说道,“瞧瞧它的羽毛就知道了。”
“没错,是只成年的鸟。”爸点头同意。
小鸟直直地站在玛丽柔软的手掌里,睁着明亮的黑眼睛,定定地看着大家。
“它从来没有见过人类。”爸说。
“你怎么知道,爸?”玛丽不解地问。
“因为它不怕我们。”爸回答。
“哦,我们能留下它吗,爸?可以吗,妈?”卡瑞央求道。
“看情况吧。”爸说道。
玛丽伸出指尖,轻轻地把小鸟摸了个遍。劳拉在一旁向她描述鸟儿光滑的胸脯是多么的白,背部、尾巴和小翅膀是多么的黑。接着她们让格蕾丝也小心翼翼地抚摩小鸟。再瞧瞧小小的海雀,静静的,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陌生的人类。
大家把鸟儿放在地上,鸟儿稍稍走了几步,接着用长蹼的脚尖蹬了蹬地板,小小的翅膀一扇一扇的。
“它飞不起来,”爸说,“它是一只水鸟,只有在水里利用长蹼的双脚加速,才能起飞。”
最后他们把鸟儿放进屋角的一个盒子里。鸟儿眨着圆圆的、明亮的黑眼睛注视着大家。大家有同一个疑问:该给它喂什么食物呢?
“这场暴风雪真是奇怪,我一点儿也不喜欢。”爸说。
“查尔斯,不过是一场暴风雪罢了。”妈说,“我们会迎来温暖宜人的天气的,气温已经上升了。”
玛丽又忙活起手中的针线活儿,劳拉继续扫地,爸站在窗边,不一会儿,卡瑞牵着格蕾丝离开了海雀,也从窗户向外张望。
“哦,快看呀,是长耳大野兔!”卡瑞兴奋地大叫。只见几十只野兔在马厩周围活蹦乱跳。
“暴风雪来临时,这些淘气鬼一直偷吃我们的干草。”爸说,“我应该拿上猎枪,打一只回来炖着吃。”
话虽如此,爸并没有拿枪,只是站在窗边盯着蹦蹦跳跳的兔子。
“求您放过它们这一回吧,爸,”劳拉恳求道,“它们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总得找一个能避风雪又能填饱肚子的地方呀。”
爸看向妈,妈微微一笑,说道:“查尔斯,我们不饿,谢天谢地总算熬过了这场暴风雪。”
“好吧,给兔子们吃点干草也没关系。”说完,爸拿起水桶打水去了。
刚一打开门,寒冷的空气就灌了进来。不过在阳光的照射下,小屋南面的积雪已经开始融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