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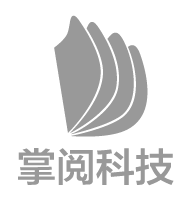
|
书名:腰门
作者:彭学军
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ISBN:9787514822519
本书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有限公司授权掌阅科技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彭学军,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具有清新的诗性格调,善从真实的儿童心理世界寻找支撑,不露痕迹地将幻想元素糅入现实题材,表现世象的缤纷和成长的疼痛。
出版有《你是我的妹》、《腰门》、《奔跑的女孩》等四十多部小说和散文集,被译作英、法、韩、日等多种文字输出海外。所获奖项有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小说大奖、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









 1 叫我沙吉
1 叫我沙吉
我喜欢对着太阳做这个游戏。我眯起眼睛,看见一粒一粒的沙子重重地砸断了太阳的金线,阳光和沙砾搅在一起,闪闪烁烁的,像一幅华丽而炫目的织锦。
有时,我不厌其烦将沙子捧起,漏下,只为欣赏那瞬间的美丽。
我从小就是一个有点自闭的孩子,不合群,喜欢一个人玩,我可以一个人玩得有声有色。我还喜欢胡思乱想,自闭的孩子都有这个毛病,胡思乱想是一种常玩常新的精神游戏。
有一阵子,我非常非常热爱沙子,当然,这肯定不是因为我姓沙的缘故。
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工地,只打好地基就停工了,一大片地荒着,荒地上坟一样隆着一堆堆的沙子,我每天都去那里玩。
我会用水把沙子浸湿,做成城堡、房子、城墙什么的,这些都是我想象中的,在别人看来,它们也许什么都不是。或者,我什么都不做,只是跪在沙砾上,双手捧起沙子,高高地举起,然后双手分开一些,留出一道缝隙,沙子就从缝隙中漏下来,我尽量使它们漏得均匀一些,像流水一样。
我喜欢对着太阳做这个游戏。我眯起眼睛,看见一粒一粒的沙子重重地砸断了太阳的金线,阳光和沙砾搅在一起,闪闪烁烁的,像一幅华丽而炫目的织锦。
有时,我不厌其烦将沙子捧起,漏下,只为欣赏那瞬间的美丽。
我的神态庄重严肃,像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妪在做某种祭祀。
当然,我最喜欢玩的还是挖沙洞。
掏一个很深的坑,捡一些小树枝架在上面,再找几张废纸或塑料袋铺在上面,轻轻地盖上一层薄薄的沙子。然后我闭上眼睛,自欺欺人地装着一无所知的样子朝前走去,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陷在沙坑里,我很“意外”地惊恐地大叫一声,然后嘻嘻哈哈地乐上半天。
这天,我伪装好一个沙洞,走到离它远一点的地方,正准备闭上眼睛重蹈覆辙时,看见一个人朝这边走来。
他背着阳光,身体的轮廓被套在一个金黄色的框子里。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能断定他是个男的,他比我要大很多,但又不是一个真正的大人,是个小大人,我在心里这么叫他。
小大人一步一步朝这边走过来,而且是对着沙洞走,他离沙洞越来越近了,我的心怦怦地欢跳起来——要知道,在我看来,这是唯一的一次真实的游戏。
小大人离沙洞只有一步了,我捂住了自己的嘴,不知是怕一颗紧张、快乐的心跳出来,还是怕自己忍不住会替他尖叫起来。
可是,他站住了,看着我。我赶紧扭过头去,装模作样地东张西望。
突然,小大人对我笑了一下,然后一抬脚,一分不差地陷进了沙洞里。
“啊哈——”我蹦了起来,憋了好久的欢叫终于冲出了喉咙,比平时要响十倍。
然后,我咯咯咯地笑。小大人的样子好狼狈,差不多是摔在了沙地上。但他一点儿也不恼,还和我一起大笑,并不理会一身的沙子。
笑够了,我们坐在沙地上开始交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奇迹,我很少和人交谈,更不用说是陌生人了。
“你叫什么名字?”
“沙吉。”
我是想告诉小大人他的额角沾了好些沙子,可能是很少说话的缘故,我说话时有的字一直咬不准,比如我常把“沙子”说成“沙吉”。他就以为我叫“沙吉”。
“哦,你姓沙?”他抓了一把沙子问我。
我点点头。
“沙吉,是个特别的名字,如果叫沙莎就一般了,只要姓沙,这个名字谁都会取。”
我本想纠正他的,可听他这么一说,我就不吭声了。
“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小大人又问。
我摇摇头。
小大人就弄平一块沙地,用手指写了我的新名字——沙吉。然后抓住我的手教我写。
小大人从后面环住我,我差不多是靠在他怀里,这样学写字,我觉得很舒服。
我还算聪明,写了几遍就学会了。小大人把沙子重新抹平,说:“再写一遍。”
我默写出来了。然后,仰起头,有点得意地看着他。
我看见他的下颏有一道我小手指一般粗的月牙形的疤,嘴唇周围有一圈细细的绒毛,让我想起坏了的馒头上的霉菌;我还看见他的睫毛又长又密,我活到六岁还没见过谁有这么长的睫毛。
我还注意到了他的喉结,他的喉结不如爸爸的显眼,只隐隐地有点轮廓,害羞的、发育不全的样子。所以,我的判断没错,他只是个小大人。
这时,我听见妈妈在叫了,她当然是叫“沙莎”。
“沙莎——”
我一跃而起,急吼吼地朝妈妈奔去。
平时,我是不会这么随叫随到的。我要么装聋作哑地不吭声,要么嘴上敷衍着“来了来了”该干吗依旧干吗。这会子这么乖主要是担心小大人听出我叫沙莎——很“一般”的沙莎,而不是“特别”的沙吉。
果然,妈妈看见我奔过来就不叫了。
妈妈一把抓过我,拍掉我身上的沙子,然后把我牵到一盆清水旁。一会儿,水就浊了,我的脸和手臂被擦得白里透红。
这时,爸爸也回来了。妈妈把脏兮兮的水倒掉之后,和爸爸一起站在我面前,定定地看着我。
我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一声不响地站着,等他们说话。
“我们又要搬家了。”妈妈轻叹一口气说。
我松了口气,这一点儿也不稀奇,我们经常搬家。爸爸妈妈是修铁路的工程师,铁路修到哪儿,我们就搬到哪儿。听说,更小的时候,奶奶带过我一段时间,后来奶奶去世了,外婆病瘫在床好几年了,根本没法照顾我,爸爸妈妈就只好带着我不停地搬家。
“但是,你不能再跟着我们这样跑了,我们没时间照顾你,而且,你很快就要上学了。”爸爸接着说。
他们说这些的时候我有点心不在焉,我总朝门外张望。
门口的一棵树挡住了我的视线,那棵快枯死的树在夕阳中熠熠生辉,有着无比瑰丽的色彩,可我对它的美丽视而不见,我只是想看看小大人走了没。
等我回过神来时,听见妈妈说:“我们想、想把你寄养到别人家里,那家人很好,会待你很好。”
妈妈的神情期期艾艾的,妈妈的脸晒得黑黑的,现在好像更黑了,我觉得屋子里的光线也一下子暗了下来。我紧张地叫起来:“你、你们不要我了?要把我送人!”
“不,不是送人,是寄养。”爸爸解释说。
“什么是寄养?”
“就是,就是我们暂时没有时间照顾你,托别人照顾,我和你爸说好了,等我们修完这条铁路就不干了,我们去干别的,我们搬到省城去住,买套房子,三个人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也不再搬家了。”妈妈说。
“那我要在人家家里待几天?”“天”是我最长的时间概念。
爸爸妈妈对视了一下,妈妈别过脸去,爸爸吞吞吐吐地说:“几天……这个,说不准,我们要修一条很长很长的铁路……”
屋外的光线也暗了很多,太阳不见了,沉到我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了。我想早点结束这场谈话,去看看小大人还在不。
于是,我干脆地说:“好吧,那我就寄养,但是你们得答应我改名字,我不要叫沙莎。”
爸爸妈妈惊讶极了,眼睛大大地瞪着,几乎同时说:“那你要叫什么?”
“我,要,叫,沙,吉。”我郑重其事、一字一顿地说。
“怎么……想到改这个名字?”
“沙莎多好听。”
“我就要改!”我倔倔地说,然后,拧着脖子,不想和他们啰唆。
僵持了一会儿,爸爸终于说道:“嗯……不过,沙吉也不错。”说着,还朝妈妈眨眨眼睛。
“沙吉沙吉……”妈妈嘴里念叨着,然后对爸爸说,“叫着倒也顺口,哈?”
…………
最后,爸爸妈妈同意了我的决定,改名叫沙吉。他们没有理由不满足一个将要寄养在别人家里的女儿的“莫明其妙”的要求。
“好吧,沙莎……”爸爸说。
“叫我沙吉。”我一本正经地纠正他。
“好吧,沙……吉,你就叫沙吉吧。”爸爸说了句很废的废话。可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觉得我很爱他。
终于,他们忙自己的事去了,我迫不及待地冲出门,朝远处张望。
工地上空无一人,一堆一堆的沙子静静地矗立在淡淡的暮霭中。
这是我对童年的“玩具”投去的最后一瞥。
 2 不会说话的水孩子
2 不会说话的水孩子
男孩挽着裤腿,没穿鞋,桶里的水荡出来,弄湿了他的脚,路面上便拓下了一串脚印。这是一条青石板路,无数的日子和鞋底将它打磨得又光滑又细腻,干爽的路面是铁灰色的,湿湿的脚印拓在上面,颜色深了一块,像游弋在他身后的一串鱼。
一大早,我就被一个声音吵醒了。
支起耳朵一听,听见身子底下有哗哗的流水声,怎么会有水声?是睡在船上吗?睡意随着流水声渐渐淡去,我想起来了,是睡在卧房里,而卧房是悬在水面上的,靠水的那一边用几根粗粗的木头柱子撑着,让人觉得像是一排巨人背着房子站在水里。这就是吊脚楼。
这条老街叫北边街,一溜都是这样的吊脚楼。吊脚楼一面濒河,一面临街,褐木黑瓦,灵巧古朴,远远看去,像是童话里的景致。
昨天一到这里,就好新奇这里的房子。
首先是那扇腰门——在高大的木门前面有一扇小小的门,比我高出许多,须站在小凳子上,才能将下巴搁在门框上。而腰门的长度正好是大门的一半,是因为这个就叫它腰门?
但一开始,我自以为是地听成了妖门,说了我是个喜欢胡思乱想的孩子,好好一件事就会想歪了,不得要领。只是我想不明白,怎么会叫妖门,是妖精进出的门?这里会有妖精?要是真有,我倒觉得来这里寄养是来对了,有妖精的地方一定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听过彼得·潘的故事,那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可爱的小妖精。
后来我常倚在门边等候妖精。我特别留意黄昏这段时间——据说,这是妖精出没的时段。
有一回,我等来了一只白猫,它喵的一声从虚掩的妖门挤进来,它有着纯然一色的白毛和湛蓝的夜空一样的眼睛,它站在门边歪着头望着我,那神情自负而又娇憨,而它的眼睛在沉暗的天光中闪着诡秘的光。我正要过去抱它,但它闪烁的眼光让我突然警醒起来:它会不会是妖精变的?
立马,跟踪追进来了一个男孩,把它抱走了。
还有一次,也是黄昏的时候,有一片白色的羽毛从妖门飘了进来,落在地上。我捡起来,那羽毛十分柔软,我只轻轻地哈了口气它就好像要飘浮开去。凭我已有的经验,我不能断定它是鸡,或者鸭,或者鹅,还是别的什么动物的羽毛。突然,我又想到了妖精,是妖精的羽毛?妖精是可以千变万化的,那么,这回她又变成了什么呢?肯定是一种会飞的东西,羽毛都飘进来了,说明她就在附近。
一时间,我兴奋得浑身战栗起来。我趴在妖门上,恐惧而又欢欣地期待着。
我自然是白等了。
推门进去就是厅堂,厅堂是结结实实地建在地面上的,往里走才是木地板的卧房,人走在上面嗵嗵地响,下面是空的,并有细细柔柔的流水声传来。我走到木格窗前张望,可我太矮了,什么也看不见。这时,从后面环过来一双手,把我抱了起来,还有一个流水一般柔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看看,下面是条河。”
下面果真是一条河,河水清幽幽的,对岸是一排排的麻条石的台阶,一直铺到水里,有好些人蹲在那里洗衣洗菜。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桥”,那“桥”很特别,是一个个的石墩连成的,石墩的间隔大约是大人迈一步的距离,我想我是绝对跨不过去的。后来,我才知道,那“桥”叫跳岩。
我回过头,看到了一张清秀和善的脸,眼角虽布满了细细密密的皱纹,但微微凹陷的眼睛却闪着煦暖温婉的光,头发一丝不苟地拢在后面,挽了一个圆圆的髻,鬓角有几缕银丝在闪烁。她从后面环住我,轻轻地揽我入怀,她的怀里异常的柔软,我像是靠在一垛棉花包上面,而且,我还闻到了一丝丝类似蒸肉包子的暖暖的香味。
妈妈抱我的动作常常很猛,奶奶带我的时候,她每次离开和见到我都要狠狠地抱我一下,她用力地把我往怀里按,好像要把我塞进她的身体里去一样。妈妈瘦,她的肋骨硌得我不太舒服,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汗味。
想起刚刚进门的时候,妈妈告诉我,这是云婆婆。当时我只是瞪着一双眼睛傻傻地看着她,我不习惯和陌生人打招呼。可这会儿,也许是她这轻轻一抱突然就对她没了隔膜,有一种令我自己都惶惶不安的想亲近她的感觉,我居然很乖巧地叫了一声:“云婆婆。”
这一声恰巧被走进来的妈妈听见了,我这样甜甜地主动叫人是十分罕见的,妈妈大大地吃了一惊,随即十分宽慰地笑了,说:“这孩子有点怪,却和你这么有缘,好了,这下我就放心了。”
安顿好了我,妈妈就走了。
云婆婆拉着我的手送妈妈,只送到门口妈妈就不让送了,把我们往屋里推,说:“别送了,我看着难受。”说完背过脸去。
云婆婆扶着我站在门槛上,我就正好将两只手臂搁在妖门的上框。我朝妈妈挥着手,可她并没有回头看我。妈妈急匆匆走得好快,好像是怕我追上去,缠住不让她走。
看着妈妈越走越远,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难受起来,正想追过去,“水哎——”我听见一个人在喊。
扭头一看,是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挑着一担水边走边喊。
男孩挽着裤腿,没穿鞋,桶里的水荡出来,弄湿了他的脚,路面上便拓下了一串脚印。这是一条青石板路,无数的日子和鞋底将它打磨得又光滑又细腻,干爽的路面是铁灰色的,湿湿的脚印拓在上面,颜色深了一块,像游弋在他身后的一串鱼。
“水哎——”男孩走过来了,朝着我们喊。
“水,过来。”云婆婆招呼他,并打开了妖门。
他点点头,快乐地、无声地一笑,挑着水欢欢地快步走了过来。进屋,然后把水倒进一口大缸里。云婆婆给了他五分钱。
云婆婆告诉我,这个男孩是以卖水为生的,他和他的麻脸奶奶住在这条老街的西头。麻奶奶是个孤老太婆,一脸麻子,很丑。麻脸奶奶不是他的亲奶奶,他其实是捡来的,麻脸奶奶把他养大。五岁那年,他得了一场大病,麻脸奶奶倾其所有为他治病。麻脸奶奶的“所有”很少,是她平时卖水攒下的一点点钱。命总算是保住了,但病好后他就不会说话了。
麻脸奶奶年纪大了,挑不动水了,男孩就接过了麻脸奶奶的扁担,卖水养活麻脸奶奶。前两年麻脸奶奶中风偏瘫了,他还得伺候麻脸奶奶。
男孩不会说话,却能非常清晰地喊出一个字:“水。”
所以,大家就叫他水。
后来,我才知道,每天早上把我吵醒的是水的吆喝声,而不是楼板底下的流水声,流水声细细碎碎的,蚕丝一般绵绵不绝,正好是可以枕它入梦的。
“水哎——”一声声飘过来,由远而近,我惊醒了。看见一缕阳光从木格窗子的缝隙间挤进来,猫一样悄无声息地跳到裸露着木纹的地板上。
我坐起来,旁边已经没有了云婆婆,云婆婆每天总是起得很早。我赤脚跳下床,跑到窗边,推开窗子,“哗”的一下,一大堆的阳光和着清凉的晨风迎面扑来。我搬来一张矮凳子,站上去。河面上飘着一层淡淡的雾气,跳岩那边的雾要浓一些,模糊了石墩和人的脚,从这边看过去,过河的人像是在水面上飘,怪异又有趣。
“水哎——”水过来了。
我赶紧跑到厅堂,云婆婆不在家,可能去买菜了。大门开着,可妖门却插上了——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只要不是出远门,都只把妖门插上。只要小妖精不溜进来就是了——我想。可这会儿我很想出去,又拨不出闩子——云婆婆用绳子绕住了闩子,我解不开。她不准我出去时就这样。我急得大叫起来:“水,水,过来帮我开开门!”
水的头从妖门上探了进来,很轻松地帮我解开了绳子,打开了妖门。然后,把水挑了进来,倒在水缸里。
他边倒我边在一旁嚷:“可是,我不知道云婆婆要不要买你的水,她现在不在家,我又没有钱给你。”可水不听我的,倒完水后就往外面走。
没走几步,我叫住了他:“水,你帮我把妖门闩上,我跟你去玩好不好?”
水停住,看了我一眼,继续往前走。
“水!水!”我跺着脚尖声尖气地叫。
水终于走过来,把妖门闩好,然后扭头冲我咧嘴一笑,笑容像雨后的阳光一般纯净,并伸手在我的额头上弹了一下。我的额头有点奔儿,很方便别人弹,弹起来音响效果也不错。不过,水弹得很轻,一点也不痛。我看出来了,水喜欢我,而我也很无拘无束地一下子就接受了水。
我的自闭在带着一个新的名字来到这片别样的土地和别样的人们中间时,自然而然地好了很多。云婆婆话不多,温和又安静;水干脆不会说话,但他是快乐的,无忧无虑,有着十分纯净的笑容,这一切都让我觉得亲近和心安。
我赶上去,乖巧地拽住了水的手。水的手很粗糙,有很厚的茧,是从井里打水拉吊绳磨出来的。
我跟着水来到井边。我是第一次看到井。
井口不大,井沿是用麻条石砌成的,上面有一道道的痕迹。看到别人打水我才明白,那些痕迹是让提水的麻绳勒出来的。那时,我还不知道滴水穿石的典故,我暗暗惊诧于绳子的力量,并不知道,那其实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我趴在井沿上,井不太深,我看见离我并不是太远的地方又有一块小小的、圆圆的天,还有一张扎着小辫的胖乎乎的女孩的脸,可是,那女孩的头上怎么会长出两只角来呢?惊恐地回过头来,见水站在我身后,无声地坏笑着。再看井里,女孩头上的角没了。
知道是水捣的鬼,可一时还弄不明白水是怎么做的。我有时笨笨的。
我喜欢看他打水,把吊桶放下去,接近水面时,手轻轻一抖,吊桶就一个猛子不动声色地扎了进去,一拎,就是满满的一桶水。
打好了一担水,我就跟在水后面去卖。
“水哎——”这回是我叫的。我的声音水珠一般清亮,听上去又像羽毛一样的轻盈,可以在清晨寂静的老街悠悠地飘来飘去。
水回过头来,我得意地朝他笑笑,水又在我的额头上弹了一下。
可没叫几声,就让云婆婆听见了。我以为云婆婆会说我不该一个人跑出来玩,可云婆婆却说:“我看见了,沙吉买水了,还会卖水呢。”说完,就给了水五分钱。
云婆婆给我买了桐油粑。
桐油粑是用桐油叶包的,打开来就闻到一股桐油的清香。桐油粑是糯米做的,中间有腌菜和腊肉做的馅,油汪汪的,又香又糯。我把头埋在宽大的桐油叶里,吃得抬不起头来,觉得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不过吃到最后一个时,我忍了忍,不再吃,把它藏了起来。第二天早上,给了水。
以后,云婆婆早起买菜时,就在水缸边放五分钱,听到“水哎——”的声音,我就从床上一跃而起,跑出去叫水,水替我打开妖门,把水担进来,然后我就跟着他出去玩。
我每次都要趴在井沿上看,看什么呢?里面除了一个圆脸的小女孩,也没什么好看的,当然还有绣着白云的天,那云沉在水里,好像一块块泡涨了的馒头,一只鸟从空中飞过,影子印在井里,鱼一般游过——我一惊,真有鱼来吃馒头了吗?
我将身子往里探了探,没想脚下一滑,就直直地朝井里栽去。
水正在井沿边拎水,他并没有看到什么,他好像只是下意识地伸手猛地一捞,就一把抓住了我的后襟。我的半个身子差不多都栽进去了,两条腿像被捉住的蚂蚱一样,惊慌地蹬着。还好他天天提水,手臂劲很大,一使劲,就把我拽了上来。
两人站稳后,都呆了,四只眼睛互相瞪着,一句话也说不出。
想清楚了刚才发生了什么和接下去有可能发生什么后,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好像要发泄什么,哇啦哇啦哭得惊天动地。我这样惊天动地哭的时候,觉得不那么害怕了。
我哭了一阵后觉得奇怪,水呢?他怎么让我一个人哭,也不来哄我?我扭头一看,吓了一跳:水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口井——原来水比我怕得更厉害,他一定是非常后怕,我若真掉下去了怎么办?
水这副样子让我立即停止了哭泣,我抹了把泪过去抱住他的手臂,说:“水,没事了,我不哭了,你别害怕。”
可水还是不停地发抖,眼睛像一只受惊的松鼠,在我和井之间惶恐不安地跳来跳去。
我摸了一把额头,额头上是细细密密的一层冷汗,凉凉的。我把凉凉的额头冲着水仰起,说:“弹呀,水,弹我一下你就好了。”
水已经好了一点,不再抖了,脸色也不像刚才那么难看,可还是木木地站着不动。
我就自己弹起来,将中指弯曲抵住大拇指,绷住,像一张弓,然后使劲一弹,咚!脆脆的一声响,好痛!
可水依然无动于衷。任我把自己的脑门当西瓜一样弹得咚咚响。直到我弹到第五下的时候,他才抓住我的手,不让我再弹。
我说:“那你弹我一下。”
水抓住我的手举起来,在空中停了一会儿,然后猛地捶打自己的头,也捶得咚咚闷响。水捶了好几下后,我才猛醒过来,大叫:“不要,不要!停下,水!放开我!”
可是水把我抓得好紧,我根本抽不出自己的手,水抓住我的手把自己捶得一下比一下重。我急了,然后急中生智,用另一只手啪啪地打自己的脸。
水没料到我会这样,瞪着我,愣住了。
两个人傻傻地对望着,我咧嘴一笑,水也想笑,可他只难看地咧了咧嘴,没笑出来。最后他抬手在我火辣辣的额头上弹了一下,可我觉得水只是用手指在我的额头上轻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