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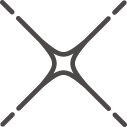
谈了“武”,再谈“侠”。我以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与其有“武”无“侠”,毋宁有“侠”无“武”。武功好的侠士自是相得益彰,但没有武功的寻常人也可以成为侠。与金、梁二人某一时期并称“三剑”的百剑堂主,在《三剑楼随笔》中曾有一篇文章题为“傅青主不武而侠”,是谈及梁羽生《七剑下天山》这部小说中傅青主这个人物的(梁把傅写成武功极高,但侠气却不显),就多少说明了这个道理。
读者们欢迎武侠小说,另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喜见抑强扶弱,行侠仗义的人物。可惜的是,许多武侠作者着力于创造离奇的武功,却忘记了武侠小说还有一个“侠”字。
金庸初期的武侠小说并没忘记一个“侠”字,可惜越到后期,就越是“武多侠少”,到了如今他所写的这部《天龙八部》给人的感觉已是“正邪不分”,简直没有一个人物是可以令读者钦敬的侠士了。
朋友们读金庸的小说,都有同一的感觉,“金庸写反面人物胜于写正面人物,写坏人精彩过写好人”。这个特点是一开始就有了的,越到后期越为显著。《书剑》中反面人物的代表张召重写得要比正面人物的代表陈家洛精彩,《碧血剑》中邪气十足的金蛇郎君,等于曹禺《日出》中不出场的“金八”,也写得很是成功,正面人物的袁承志相形之下反见逊色。到了如今的《天龙八部》,写恶人一个比一个“恶”,笔下人物种种阴狠残毒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香药叉木婉清之后有天下四大恶人,四大恶人之后有星宿派的老妖丁春秋,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妖气满纸,令人叹为观止。
把坏人刻划得入木三分,那也是艺术上的一种成功。问题在于如何写法,揭发坏人应该是为了发扬正气,而切忌搞到正邪不分。人性虽然复杂,正邪的界限总还是有的,搞到正邪不分,那就有失武侠小说的宗旨了。
假如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将《倚天屠龙记》作分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我们可以相当的清楚看出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
前一阶段,尽管金庸写反面人物比较成功,这只是他塑造人物的手法上有长有短,但正邪之分,忠奸之别还是清清楚楚的。《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这帮人物是正,清廷的一帮鹰爪是邪;《碧血剑》中赞助李闯王抵抗外族侵略的袁承志这帮人是正,通番卖国的一班奸人长白三英、曹太监等等是邪;《飞狐外传》中的苗人凤、胡斐等人是正,清廷权贵福康安、土豪恶霸凤人英和串通清廷谋害侠义道的田归农等人是邪;《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虽曾一时糊涂,后来毕竟也成为抗敌保国的大侠,郭靖、洪七公等人是正,认贼作父的杨康、私通金国的袭千仞等人是邪……正邪之间,毫不含糊。
当然,区分正邪的尺度可能因各人的道德观念、是非标准等等而有所不同,似乎以前也曾有人指摘过《碧血剑》中的高人不应追随李闯王的,这是是非标准不同之故,孰是孰非,不拟在此深论。我所要说明的一点是,金庸在前期的作品中,正邪有别,善恶分明,这说明他心目中自有一套是非的标准,通过他的作品体现出来。而这套标准,依我看来,也是绝大多数读者可以接受,而符合中国社会一般人所公认的道德标准的。
有一种文艺理论认为,人性复杂,倘若是非分明简单化了,就会减损了艺术价值。依我看来,恰恰相反,即以金庸的武侠小说而论,他的前期作品,艺术价值也要比后期的高得多。如《书剑》中香香公主以血来提醒陈家洛,叫陈家洛“不要相信皇帝”,打破了陈家洛对敌人所存的幻想(书中陈家洛是乾隆皇帝的弟弟),就颇有感人的气氛与艺术深度《飞狐外传》中金庸利用佛山的民间传说,刻划了凤人英这么一个土豪恶霸的形象,在凤人英的对面,则描写了胡斐的侠骨,发誓要为被凤惨杀的穷人报仇。是非分明,艺术价值又何尝减了?相反的,在近期的作品中,由于正邪不分、是非混淆,也就消失了感人的艺术力量了。
由于是非不分而消失艺术感染力的,我可以在他近期作品中,举一个显著的例子。《天龙八部》的乔峰,是金庸在这部小说中(到现在为止)最着力刻划的一个人物,他是契丹人,父母因误会而被汉族的英雄所杀,英雄们发现杀错人之后,将他交与一个善良的汉族农民抚养,长大后为丐帮帮主,丐帮发现他是契丹人,将他驱逐出帮。乔峰心怀愤怒誓报父母之仇,于是有一次独闯聚贤庄的英雄宴,大杀宋国的忠义之士,与旧日的朋友干杯,说:“从今之后,你杀我不是忘恩,我杀你不是负义!”于是就把丐帮昔日的兄弟也大杀起来。故事再写,乔峰的父亲当日其实未死,于是这个人又杀抚养乔峰的义父(即那个善良农民),乔峰的恩师(少林寺长老)等等。
金庸这个故事所要着力表现的是,一、人性的邪恶;二、契丹和中国,两国的人彼此仇杀,原因只是由于一个狭隘的民族观念,实在难说谁是谁非。故事中,他还通过了宋国官兵也同样劫杀契丹百姓,而渲染了这点。
当真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吗?大是大非,总是能够分别的。我们都读过一点中国历史,总会知道契丹是侵略者,是侵略者即“非”,是抵抗侵略者即“是”。至于宋兵也有劫杀契丹百姓的,那当然也该谴责,但这却不能改变了侵略与被侵略的本质,也即是不能改变是非敌我的标准。抵抗侵略,决不能归咎于狭隘的民族观念。描写两国百姓的仇恨互杀而模糊了敌我观念,这个恐怕大多数读者就很难同意了。金庸前期作品《神雕侠侣》中,曾借郭靖之口说过一句大义凛然的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而在《天龙八部》中,却又捧大杀宋国忠义之士,官居契丹南院大王(仅次于契丹皇帝的统治者)的乔峰为英雄。这种混淆是非的刻划,与他前期作品相去远矣。
故所以在聚贤庄之会中,金庸虽然着力的刻划了乔峰的英雄气概,公平来说,气氛也渲染得很是紧张刺激,是通过了艺术手法的。但无论如何,总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得到读者的共鸣。读者甚至会有这样的疑问:“作者是否要借聚贤庄中的酒杯,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这就是由于不分大是大非,以至减损了艺术感染力的例子。
依我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似乎还应该回到《书剑恩仇录》的路上才是坦途。金庸的武侠小说,从《倚天屠龙记》开始渐渐转变,至今也不过三年多点,“实迷途其未远,觉昨是而今非”,让我改陶渊明《归去来辞》的一字来奉劝金庸,不知金庸可能听得进去?
至于梁羽生关于“侠”的描写,以及两人小说中的思想内容,我将在本文的“下篇”谈到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