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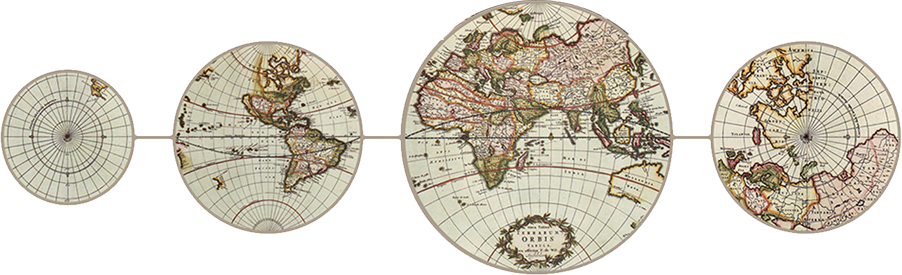
她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但7万年以来,没人知道她的名字。她确实会有名字,因为她生活在具备语言能力和高度社会化的人群中。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她确实配得上“母亲”这个名字。她大概很年轻,坚韧、结实,皮肤黝黑,跟随所在群体不断迁徙。她生过许多孩子。她的族人都是狩猎者和经验丰富的采集者,他们采集浆果、贝类动物、根茎植物和草本植物。他们身穿兽皮、携带工具,婴儿会随他们一起迁徙。不过,在行进队伍中,孩子很少见。那些不能很快学会行走的人、那些无法保持安静的人及那些落单的人都会遭遇不测——被尾随的猎食者捕获。
然而,这群迁徙者也令人生畏。他们拥有石矛和锋利的石器,这些武器是在长达10万年的狩猎生活和部落斗争中发展出来的。他们的平均年龄很小,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近代之前的所有人类社会。不过,有些人或许能活到五六十岁。今天,人们推测妇女的更年期可能就是为了适应环境而进化出来的。在成为祖母后,当更年轻的妇女怀孕时,她们就能担负起照顾母婴的责任:拥有祖母的部落可以将更多孩子抚育成人。因此,没有年长妇女的部落就会付出代价。
在狩猎中挂彩留下伤疤的男人会成为有发言权的谋士,他们了解动物的习性,是围猎的高手。部族中最年长的人(“族长”)大约六十多岁。狩猎者在三四十岁的时候捕猎能力最强。他们成年累月地迁徙,从北部今天肯尼亚和索马里这片地区慢慢向一条可以横渡的河流前进。水流比以往都要浅,露出了一块块陆地。横渡河流很冒险,但值得一试,因为周围的猎物和果蔬已越来越难找到。河对岸的生活也许会好过一些。
这群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离开人类诞生的大陆。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后代将会跋涉多远。他们沿海岸线前进,一年只走上一两英里。他们挖掘贝类动物,在退潮后的滩涂中寻找螃蟹,以搁浅的鲸鱼为食,用石矛猎杀山羊。整个生命就是一次旅程。通常,他们会找寻新的路线。无论身前身后,一旦他们离开居住地,那些猎物就会返回,但滞留一地相当危险。倘若定居一地,你就会饿死。因此,尽管水流是挑战,但他们在横渡时还会彼此照应。因为这群人拥有语言能力,可以交流自己的计划——这是新的开始。
某些迹象显示,他们可能已穿上衣服。对体虱DNA的研究表明:10万年前,它们就已经寄生在人类的衣物上。因此,有人认为,在数百万年前,人类就已褪掉身上的大部分毛发。这群人类的规模已远超单个家族的规模。他们很善于分工合作,而这与“母亲”的分娩之痛直接相关。像所有妇女一样,“母亲”深知分娩的痛苦。在很久以前,人类婴儿的脑袋就大得出奇,母亲在分娩过程中要承受极大的痛苦。在姐妹们的簇拥下,“母亲”很可能是站着分娩的。小婴儿很柔弱,无法行走,极易受到攻击。因此,人类婴儿的哺育期要远远长过其他动物的幼崽。
在漫漫长夜,人类会围在一起讲故事,但他们到底会讲些什么依旧是个谜。现代人类的婴儿很脆弱,而这却是一股持久的力量,迫使家族和部落进行分工合作。总体而言,今天的狩猎—采集型社会有明确的分工:男性负责狩猎动物,女性负责采集植物,而这一切早在“母亲”生活的时代就已经定型。在几万年之后,人类才意识到,导致步履蹒跚和分娩痛苦的大脑袋竟然是演化胜利的结果,因为这使动物具有了讲故事的能力。
出于相似的理由,研究人类演化史的学者怀疑:人类的好战倾向、排外意识和敌对特性已在非洲演化成型。部落的规模超越了家族,并且具有家族无法比拟的优势。如果部落成员能齐心协力,即使他们的行动一时令个体非常危险或不适,也能保障部落的顺利发展。这说明部落的团结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归属感和相互依存,部落就会解体。另一方面,在一个不断迁移、到处寻找猎物的群体里,对其他部落的敌意很可能会强化部落内部的团结。很显然,这两种强化部落团结的方式一直在发挥作用。
在这颗星球的各个角落,早期的人类社会似乎都在竭力将自己与相邻的人类社会区分开来。他们佩戴不同的饰品,穿着不同的衣服。最重要的是,他们讲不同的语言。英国动物学家马克·佩奇尔指出,即便在文化高度同化的今天,人类使用的语言仍有7000种之多,彼此无法直接沟通。这是为什么?其他动物与此完全不同。佩奇尔认为,人类有许多优秀品质——善良、慷慨和友善,这使我们可以相互合作,联合成更大的群体,“彼此和睦相处”。但人类也有黑暗面:“我们建立了相互竞争的社会,而这极易导致冲突。”以狩猎—采集部落为例,成员相互争夺土地,冲突司空见惯,而部落战争则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人类曾经是狩猎—采集者。我们从事狩猎—采集活动的历史要远远超过务农为生的历史,前者至少是后者的10~15倍。直到最近,我们才成为在城市定居的物种。如果说城市主宰了人类生活一二百年,那么狩猎—采集活动就影响了人类生活至少10万年。因此,人类的行为方式与狩猎—采集社会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人既具有社会性,又相互猜忌。这些特性都可以回溯至“母亲”生活的时代。
她几乎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还有一个生活年代更早、形象更模糊的女人——“线粒体夏娃”。她是所有人的母亲,包括非洲人。她生活在大约20万年前,其故事鲜为人知。)我们可以从字面意思理解人类特质中的“母性”,这并不是隐喻。人们对此还存有争论,而早期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尚无定论。但在综合各种意见后,我们可以确定她就是人类的“超级祖母”。无论是生活在纽约的律师、在肿瘤医院就医的太平洋岛民、德国农民、日本办公室的保洁员,还是在伦敦读书的巴基斯坦裔大学生,其祖先都可能是夏娃。牛津大学的史蒂芬·奥本海默是研究脱氧核糖核酸(DNA)的专家,他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生活在澳大利亚、美洲、西伯利亚、冰岛、欧洲、中国或印度的人,其遗传基因的起源地都可以追溯到非洲。”
 也就是说,我们来自同一群体,踏上了同一旅程。
也就是说,我们来自同一群体,踏上了同一旅程。
如今,上述观点似乎已成共识。但乍看之下,这个观点仍然不可思议。生了一个孩子的女人如何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祖先?我们可以通过“母系漂变理论”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每一代人中,总会有一些家族无法成功繁衍后代。由于疾病、狩猎时发生意外或近亲结婚等原因,一些母系血统会消失。经过漫长时间,母系血统几乎都会消失,而且是永远消失。这一过程就像一把舞动的大镰刀,将过往成千上万代人都一扫而光,只留下一片虚空。正像信奉达尔文主义的作家理查德·道金斯所说,我们都是幸存者的后代。
看起来矛盾的是,在镰刀没有收割到的地方还有一块更宽广的三角洲,人们得以在那里繁衍生息。这该如何解释?对那些活到生育年龄的人来说,如果其子女的幸存比率恰好高于2比2的自然淘汰率(以此类推,这一规律也适用于那些幸存子女的后代),根据数学法则推算,其后代的人数就会出现压倒性增长的现象。因此,今天的人类一定都是早期幸存者的后代(当然,人类也有父系祖先,只是我们无法通过追踪DNA的痕迹来追溯父系世代的历史)。虽然这似乎很难理解,而且给人感觉是遗传性的视觉幻象,但通过回想那个时代——人口增长极其缓慢,预期寿命也很短暂,“漂变理论”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演化现象。夏娃是所有现存人类的母亲,因为老虎、毒蛇、山体滑坡和病菌夺走了其他母亲的生命。
冲破重重险阻,夏娃的部落得以幸存。当时,有几十万人生活在非洲,他们正与其他聪明的猿类进行竞争。人类突破了“吃与被吃”的循环,不再是其他物种的猎物。我们挣脱了自然界的束缚,开始塑造身处的世界。也就是说,人类不再是偶然的存在,人类开始创造机会。
然而,智人只是人科动物中的一支。其他人科动物也逐渐学会了改变环境,只是能力不及智人。关于人类起源,学术界存在极大争议。事实上,这场争论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超过了任何一场争论。答案很简单:人类在DNA研究和骨骼碎片的年代学研究等方面的进步不断挑战,甚至推翻以往的理论。人类起源是人类历史研究中最古老的课题,而且比二战史研究进展更加迅速。这个领域着实令人着迷,但历史爱好者还是不越雷池为好。
不过,学术界已有一个共识:气候变化在人类演化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远超我们的想象。在太阳活动的影响下,地球时冷时暖。除此之外,陨石撞击、火山喷发或地球旋转角度的微小变化都会影响沙漠的盈缩和大陆桥的隐现,从而影响人类演化。例如,大陆桥的变化就会对人类迁徙产生影响。总体而言,气候变化越剧烈(有时候,剧烈的气候变化甚至导致某些动物灭绝),人类演化的速度就越快。
适应性强的生物才能浴火重生。在200万年前,寒潮和干旱袭击了非洲,生活在树上的类人生物开始直立行走,这是第一次尝试。气候变化形成了辽阔的草原,早期的类人动物被迫学习奔跑、狩猎和远眺。科学家相信,正是这些因素最终导致直立人的出现。直立人是早期人类非常重要的一支,他们的脑容量大约只有现代人类的三分之二。
在温暖的上新世之后,地球进入了更新世的冰河期,新挑战随之而来。在逆境中,人类大脑有了进一步发展。根据现代人的推测,类人动物在非洲大陆内部不断演化,整个演化过程非常复杂。在长途跋涉离开非洲后,直立人首先演化成为脑容量更大的海德堡人。50万年前,海德堡人曾生活在今天的英格兰地区,捕捉猎物、制造石斧。他们的脑容量仅比我们小一点:现代人类的脑容量约为1500克,而海德堡人的脑容量约为1200克。这种“不相上下的脑容量”是在非洲演化形成的,时间是在15万至10万年前之间。在同等体型的动物中,人类的脑容量最大,大约是正常比例的7倍。

我们只是极为简略地勾勒出人类发展的画卷。如果将史前人类编成目录,一定令你大吃一惊:他们在身高、头骨形状、股骨形状和体重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尽管科学家已经将他们逐一命名,通过分类归入进化谱系,但实际情况仍要复杂得多。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克里斯·斯特林格的提醒很有帮助,他说:“毕竟,物种只是人为创造的概念,它只是自然界真实情况的近似值。”
 同一时代的头骨具有相似性,但又不完全一样。早期人类的头骨只存在细微差异,所以我们不应被一堆错综复杂的科学名词吓倒。
同一时代的头骨具有相似性,但又不完全一样。早期人类的头骨只存在细微差异,所以我们不应被一堆错综复杂的科学名词吓倒。
我们最需要了解的是,现代人类不是唯一具有超级智慧的物种,也不是唯一征服了这颗星球的猿类。有人会产生错觉,认为早先的世界属于一群呆头呆脑的猿类,而现代人类仿佛借由魔法突然跳到了这个世界上。事实并非如此。早期的人类——包括尼安德特人和亚洲的丹尼索瓦人——也从剧烈的气候变化中幸存下来。像先辈们一样,他们也随身携带切割工具和武器,不断向陌生地域迁徙。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都晚于海德堡人,他们可能已懂得打扮自己,并且具有某种语言能力。在边缘地带,他们甚至可能已经与新到来的智人杂交。但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与现代人类相比,他们欠缺什么?
因此,我们还要回到“母亲”及其不断迁徙的部落。事情果真如此吗?人们普遍认为,非洲大陆保留了人类基因的多样性,在其他大陆还没有发现这种情况。而且,所有人种都起源于非洲。不过,学术界还存在一项大争议:即是否所有非洲以外的现代人类都是在7万年前一次性离开非洲大陆、扩散到世界各地的?有一种不同的观点认为:那些在更早时期离开非洲、移居欧亚大陆的人种事实上存活下来了。他们是否也演化为智人并在某地繁衍生息呢?
在两个极端观念之间还存在大片灰色地带,但这两种观念直接导致了两种如何看待现代人类的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本质上看,非洲人以外的所有人都是近亲,都是“母亲”的后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同的人种发源于世界的不同地区,是缓慢演化而来的。后一种观点在非西方国家很盛行,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的外貌和行为方式会存在巨大差异。我们的观点几乎无需赘言。这不是口舌之争,它与我们到底是亲人还是敌人这个问题息息相关。
科学界更倾向“走出非洲说”或“单地起源说”。因为科学家们通过追踪一种特殊形式的DNA标记(即线粒体DNA)发现,现代人类的线粒体DNA都可以追溯到非洲。大约20万年前,现代人类(即智人)已在非洲出现。过去的观点认为,古猿越来越聪明,然后“命中注定”要走出非洲,开始在空旷的欧洲和中东地区繁衍生息。现在看来,这个观点似乎不正确。和其他动物一样,原始人类早就踏上了迁徙之路。最近在南非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大约200万年前,直立人就已经学会用火烹饪食物,尽管这一发现仍存在极大争议。不过,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人类的脑容量为何会不断增大——烹饪可以极大提高食物的热量。也就是说,烹饪过的食物可以使人摄取更多热量,而大脑的运转非常消耗能量。
无论如何,在我们踏上迁徙之路前,其他人种就已经在世界许多地区定居了。那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也许,他们成了气候变化的牺牲品。当气温再次下降时,寒冷和饥饿最终毁灭了他们。或者,他们是被现代人类消灭的,因为后者的组织性更好、适应力更强。欧洲人曾一度认为,现代人类经由埃及离开非洲,首先进入地中海世界和欧洲,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首先向南进发,沿印度和东南亚的海岸前进,边走边捡食甲壳类动物,就像之前一样。最终,我们跨越海洋,到达澳大利亚。这一观点再次引发了科学家的争论。不过,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到达居住地的时间似乎要比法国或西班牙的土著居民早几千年。我们通过追踪DNA发现,欧洲克罗马农人的祖先曾居住在今天的印度,他们随后才转而向北迁徙。早在哥伦布或爱尔兰人抵达美洲之前,人类历史就已经是一部有关迁徙的故事了。
是什么因素导致智人离开非洲的?学术界再次出现许多针锋相对的理论。
大约7.35万年前,今天的苏门答腊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火山爆发。这是过去200万年中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难。
 当时,火山灰遮天蔽日,地球气温急剧下降。一些科学家认为,现代人类差点没挺过这场大灾难。还有一些人认为,当时的人口数量迅速下降,全部人类只剩下生活在非洲南部的几千人。这场突如其来的震荡使数万年的人类演化遭遇瓶颈,但也催生出更坚毅、更有组织性的人性。待环境改善后,人类以更好的状态重新踏上征途——“母亲”所在的部落就井然有序。另一些人则认为上述说法夸大其词:环境虽然恶劣,但许多物种仍然得以幸存。
当时,火山灰遮天蔽日,地球气温急剧下降。一些科学家认为,现代人类差点没挺过这场大灾难。还有一些人认为,当时的人口数量迅速下降,全部人类只剩下生活在非洲南部的几千人。这场突如其来的震荡使数万年的人类演化遭遇瓶颈,但也催生出更坚毅、更有组织性的人性。待环境改善后,人类以更好的状态重新踏上征途——“母亲”所在的部落就井然有序。另一些人则认为上述说法夸大其词:环境虽然恶劣,但许多物种仍然得以幸存。
然而,人类一旦离开非洲,严寒和酷热的气候就塑造了他们此后的行动,最终导致他们的胜利。经由今天的中东地区通往欧洲的道路是逐渐形成的,经过了相当漫长的岁月。但3.9万年前人类刚一到达欧洲,位于意大利的火山就突然喷发。由此,欧洲开始不定期地出现“海因里希事件”。“海因里希事件”是指崩裂坍塌的冰山掉入大西洋后导致的极寒期。北方的冰盖逐渐消退,然后又卷土重来,并多次反复。鹿和野牛等动物的迁徙模式随之发生改变。舒适的避难所变成严寒之地,但这些寒冷的荒野随后又焕发生机。为了生存,人类不得不一再改变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这又一次说明:适应性强的人才能浴火重生。
走出非洲后,为数不多的智人似乎比其他人种更好地适应了气候变化。如果情况属实,达尔文的古典进化论就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没有足够的时间演化),而源于文化的加速发展——语言能力、学习能力、模仿能力和记忆能力的加速发展——才更有说服力。我们的手越来越灵巧。在更大规模的组织中,人们各施所长——最优秀的猎手追踪猎物、最耐心的人编织绳索、最灵巧的人削磨箭头。分工合作使我们成为更有杀伤力的优秀猎人。人类群体在寒冷、干燥的世界中顽强生存,不得不学习新事物,其中包括构造更复杂的语言的能力和了解猎物习性的能力(哪种动物行动更敏捷)。他们和敌对部落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
克里斯·斯特林格认为,上述能力使人类进入了加速发展期,代替了此前“长达200万年的沉闷期”。“与单纯依靠某位领袖的才能相比,模仿和来自其他部落的反馈使人们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因为领袖的思想永远无法超越他或她身处的山洞,突如其来的死亡很可能使他或她的思想消逝。”
 其他智人群体也具备语言能力,还能预定计划,但他们做得不够出色。因此,当周边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他们就被淘汰了。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被我们消灭了(有可能被我们吃了)。布莱恩·费根是研究早期人类史的专家。他认为,这种新型的合作关系不仅催生出语言能力,还导致了抽象思维能力的出现。而且,抽象思维第一次囊括了艺术,也许还有宗教。
其他智人群体也具备语言能力,还能预定计划,但他们做得不够出色。因此,当周边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他们就被淘汰了。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被我们消灭了(有可能被我们吃了)。布莱恩·费根是研究早期人类史的专家。他认为,这种新型的合作关系不仅催生出语言能力,还导致了抽象思维能力的出现。而且,抽象思维第一次囊括了艺术,也许还有宗教。
具备上述能力后,我们首先进入亚洲,随后又到达欧洲。大约4万年前,我们抵达远东地区;大约2万年前,我们跨越“白令海峡”的大陆桥(早已消失)进入美洲;大约1.2万年前,我们来到南美洲的南部地区。太平洋中部的各个岛屿则是我们最后到达的地方。1000年以前,人类才最终到达夏威夷和新西兰。他们的文化本质上属于石器文化,但他们发展出了令人惊叹的星象导航技术和造船技术。与140万年前的早期人类相比,智人的扩散速度更快;与我们的祖先(直立人)相比,智人的进化速度也更快。
 在生物演化的时间轴上,现代人类的演化就像一场大爆炸。有证据表明,在我们所到之处,都会有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灭绝。
在生物演化的时间轴上,现代人类的演化就像一场大爆炸。有证据表明,在我们所到之处,都会有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灭绝。
坐在咖啡馆里或驾驶汽车的现代人通常会有自鸣得意的感觉。他们认为,自己在智力上肯定胜过那些在非洲苦苦挣扎了数百万年的狩猎—采集者。但事实并非如此。与现代都市人相比,那些狩猎—采集者更加能力非凡。据估算,与上一个冰期的人类相比,现代男性的大脑尺寸减少了10%,而现代女性的大脑尺寸则减少了14%。澳大利亚科学家提姆·弗兰纳里指出,与在野外生长的祖先相比,圈养动物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相同的:“总的来说,混合饲养的牲畜都大幅改变了行为方式,大脑获取的能量随之逐渐减少……如果你怀疑我们的文明会在多大程度上将我们变成自我驯服的无能动物,那么看看周围世界你就明白了。”
 这话听起来可能有些刺耳,但却有助于纠正当代人的骄傲情绪。走出非洲的早期人类具有非凡的特质,令人生畏。
这话听起来可能有些刺耳,但却有助于纠正当代人的骄傲情绪。走出非洲的早期人类具有非凡的特质,令人生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