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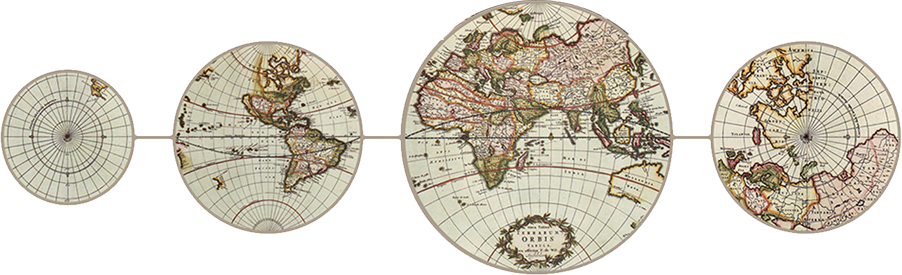
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有一位54岁的高官已经心生倦意。他辞去大司寇的官职,告别亲朋好友,外出游历了13年之久。这不是佛教徒为寻求隐居和顿悟的出走,而是一场政治之旅。他走访了许多国家,但郁郁不得志。后来,这位士大夫再次回到家乡,为壮志难酬而自嘲和慨叹。在他去世的时候,只有一小群朋友和学生追随左右。由此看来,孔子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
然而,他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好坏,孔子被中国很多皇帝都奉若神明。他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孔子也曾受到后世的批判,但在中国人开始寻求新的价值观以超越庸俗的物质主义的时候,他的影响力再次复兴。在政府的资助下,中国人拍摄了一部讲述孔子生平的电影。过去,皇帝们在北京的孔庙(在中国各地有大约3000座孔庙)祭祀这位思想家。如今,忧心忡忡的家长们也把孩子送到这里,希望他们在知识之外学习一些儒家的道理。
无论怎样估算佛陀的出生时间,孔子与他都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中国人更善于保存历史文献。因此,我们相信孔子的生活年代大致是从公元前551年到公元前479年。和悉达多一样,他也出生在一个小国,战乱频仍、社会失序。印度有身穿黄袍、隐居森林的“探寻者”,中国则有四处游历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流派纷呈、百家争鸣。和佛陀一样,孔子也能与统治者们直接交流,不受拘束。他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重要性,从未以神明自居。但在后世,孔子却被弟子们奉为神明,成为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思想流派的核心人物。
如同佛陀时代的印度和黄金时代的希腊,孔子时代的中国也正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在孔子死后,中国的诸侯争霸愈演愈烈。在中国,故事的主角不是雅典、斯巴达、般遮罗、摩揭陀和撒克拉等城邦,而是郑、齐、晋、楚等诸侯国。但从政治上观察,中国的局势似乎更混乱。中国的编年史书记载了超过140个诸侯国的史事,各国统治者和巫祝的行为在同时代的希腊人、波斯人或印度人看来没什么奇异之处。他们焚烧牛肩胛骨或者龟壳,通过观察表面的裂纹来占卜未来。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相比,这样的习俗并不显得更愚蠢——希腊的女祭司在吸入有毒的蒸汽后会以疯癫的状态传授神谕,而罗马人则嗜好用手指伸入鸡的内脏来探测神意。
中国后来成为大一统国家,这是其与众不同之处。孔子抱持一种浪漫的复古主义情怀,认为那个失落的黄金岁月曾天下一统。孔子时代的诸侯国都是由周王朝分封的,这个王朝在灭亡商王朝后存续了700多年。在外国人眼中,中国的帝国史实在不可思议。不过,在孔子生活的时代,故事却一目了然。商王朝是中国第一个有史可证的王朝,在它之前就是处于迷雾之中的夏王朝(据说,由大禹创建)。
与早期的印度一样,商代中国还处于比较蛮荒的状态。各地都密布森林和沼泽,尚未被开垦出来以种植稻子。中华文明很可能发源于黄河流域,那里有很多野生动物,如老虎、熊、大象、犀牛和黑豹等。当时的气候非常严酷,冬天寒冷,夏天酷热,还有洪水定期泛滥。从某种角度观察,商代社会与印度早期的雅利安人社会很像,贵族和武士阶层靠劫掠和狩猎集聚了大量财富,完全依靠穷困的农民来供养。
与亚述人和波斯人一样,商代军队也运用战车和弓弩作战。诸侯、贵族、地方统治者和武士的位阶都源于商王的分封。今天的考古发掘证实,城市和要塞都筑有高墙,棱角分明、非常坚固。他们的建筑都是木质的,这种具有硕大的矩形屋顶的建筑样式一直流传到后世。后来,木材最终被泥砖取代,茅草铺设的屋顶逐渐被黄绿色的琉璃瓦淘汰。但是,其基本建筑样式一直保持不变。后世的建筑样式和混合的建筑样式使欧洲的建筑呈现异彩纷呈的状态,但中国的传统建筑并未受到影响。商代贵族死后会葬在方形的廊柱式陵墓中,随葬品丰富多彩,包括精美的青铜器、丝绸和漆棺。他们沉迷于人牲,大量奴仆和囚犯被杀掉(甚至被肢解)以陪伴贵族前往阴间。
商代也不是漆黑一片。在商王朝的统治下,人们平整土地、挖掘水渠以发展农业生产。不同凡响的是,距今至少有4000年历史的文字——书写于占卜用的兽骨之上——与现代汉字非常像,考古学家可以直接读出部分文字。商文化与阿兹特克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有人牲及繁复、粗犷的艺术。就像中美洲那样,生机勃勃、拟人化的“民俗艺术”逐渐被更繁复、更严肃、更呆板的礼仪取代,折射出城市和宫廷中等级森严的社会状态。
 商代的青铜器世界闻名,他们的铸造工艺举世无双。不过,这些青铜器只能引发敬畏,无法打动人心。
商代的青铜器世界闻名,他们的铸造工艺举世无双。不过,这些青铜器只能引发敬畏,无法打动人心。
商王朝被国运绵长的周王朝取代,而孔子对周王朝非常倾慕。一位历史学家认为,商王朝的灭亡是罪有应得:“酗酒、乱伦、同类相食、靡靡之音和严刑峻法都是违反礼制的行为。”
 周公领导众人铲除了这些恶行,垂范于后世。在特洛伊城被攻陷大约150年之后,周公的兄长在“牧野之战”大获全胜,最终推翻了商王朝,周王朝顺应“天命”取而代之。周公的兄长不久就去世了,继位的周天子还很年幼,无法处理政事,周公代为摄政。
周公领导众人铲除了这些恶行,垂范于后世。在特洛伊城被攻陷大约150年之后,周公的兄长在“牧野之战”大获全胜,最终推翻了商王朝,周王朝顺应“天命”取而代之。周公的兄长不久就去世了,继位的周天子还很年幼,无法处理政事,周公代为摄政。
“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周王朝的统治家族兴起于商王朝的边鄙之地。因此,他们在治国理政时就格外谨慎。周天子维持了政策的连续性,收获了前朝追随者们的效忠。后世王朝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周公宣称,周王朝只是公正的上天用来惩罚商王朝的工具。承此天命,周天子必须敬天爱民。周公说道,平民百姓会误入歧途,也会犯错,但滥用刑罚的人是无法久居王位的,身为天子,要以美德垂范天下。那么,升斗小民就会起而效仿。

对孔子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信条。有德行的君王能教化出有德行的百姓。唯此,义务和互助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如果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做好分内之事——扮演好母亲、厨师、教师或士兵的角色,生活就会美好,社会就会和谐。“谨守名分”是一种社会美德,而不仅仅是驯服。这是一种以家庭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它反对个人主义。如果沉浸在偏执的个人主义文化而不能自拔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无法理解孔子和中国的历史,甚至无法理解当今的中国。
在向民众解释了“天命”之后,周公将权力交还给真正的统治者——他的侄子周成王。这一谦卑的姿态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孔子经常谈到周公。周代的盛世对孔子及其同代人意义重大,如同逝去的英雄时代对古希腊人的意义。周王朝在中国的核心地区分封了很多诸侯国。但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分封制已经名存实亡。诸侯国亲自统辖属地内的城池,统治权世袭罔替,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相互敌对的独立国家。有一位历史学家的见解很精辟:在诸国争霸的世界中,周王室“仅仅是名义上的权力来源……血缘和效忠的纽带早已断裂”。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孔子认为自己肩负匡正谬误的责任。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孔子认为自己肩负匡正谬误的责任。
孔子出生在鲁国陬邑的昌平乡,而鲁国与日渐衰微的周王朝关系十分密切。鲁国十分忠于周王室,这在诸侯国中很少见。据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身材魁梧,是一位著名的武士。他与颜氏女野合生下了孔子。出生时,孔子的头颅硕大,面部凹陷,有人说他头顶长了大肿块,也有人说他是颅骨下陷。
 成年后,孔子身材异常高大。在当时的中国,他很可能会被遗弃夭折。但孔子并没有遭受这样的厄运,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何终身都挚爱着母亲。孔子幼年丧父,尽管可以继承父亲的头衔,但他的幼年生活似乎很艰辛。
成年后,孔子身材异常高大。在当时的中国,他很可能会被遗弃夭折。但孔子并没有遭受这样的厄运,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何终身都挚爱着母亲。孔子幼年丧父,尽管可以继承父亲的头衔,但他的幼年生活似乎很艰辛。
《论语》是有关孔子言行最权威的记载。他曾说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但是,孔子饱读诗书,希望为分裂、动荡的鲁国效力。他曾担任“委吏”(管理仓库)和“乘田”(管理畜牧)等低级官职,后来先后成为“中都宰”(掌管刑罚的地方官员)、“司空”(掌管水利、营建的高级官员)和“大司寇”(掌管刑狱、纠察的高级官员)。孔子结过婚,但他的妻子鲜为人知。孔子对捏造事实的文人极尽嘲讽。因此,我们这些以笔墨为生的人要小心了!后世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认为,孔子的为官之路很顺利。在他的治理下,鲁国“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於途,途不拾遗”。

现代人理解孔子的最大障碍是破解他为何如此痴迷礼制。礼制规范着葬仪、节庆和日常饮食,不同身份的人都有礼制可循。据估计,一位有教养的君子需要谨守3300条礼法。我们主要通过一部简略的鲁国史书《春秋》来了解那个时代。这部史书主要记述了各国的外交,有可能出自孔子之手。此外,《左传》是我们另一处信息来源。
“春秋”只是时人对“一年”的诗意表达,但如今已成为我们指称特定历史时期的名称。当时的编年史书非常关注正统、地位、礼节和仪式等方面的内容。对孔子而言,上文提到的遵从礼制就是重中之重的事情。在一次祭祀活动之后,鲁公未能依照礼制分配祭肉,这可能导致孔子愤而离职、出走他乡。在母亲去世后,孔子坚持依照礼制发丧,即使旧式的葬礼花费不菲也在所不惜。随后,他为母亲守孝了三年。
“礼制”为何如此重要?
用一个字来回答就是“家”。孔子也许是不可知论者,从不妄谈怪力乱神。他认为,恪守礼制既是自我约束的方法,又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正途。在礼制社会中,家族间的纽带编织成一张大网。在传统中国,长幼有序的家族(这与希腊城邦恰恰相反)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哀悼逝者、庆祝节日、缅怀先人、聚集家人和祭拜神明等一系列活动将家族成员凝聚在一起,使他们获得了身份认同。在战胜对手后,胜利者会销毁失败者的礼器,清除敌人的集体记忆、传统习俗和身份认同。礼制塑造了人。倘若不循礼制、肆意妄为,人就不成其为人。
在早期中国,家族纽带是维系各邦国的社会基础,其功能就像组织有序的部落。但在良善社会中,这种纽带(以礼为标志,受礼的约束)会超越血缘关系。地主与农民、买家与卖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及附属国与宗主国之间都存在纽带。尽管这些纽带超越了家族关系,但同样受到礼制的约束。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这种古老的生存方式(谨守名分、向善而行)逐渐受到诸侯争霸的挑战,已经岌岌可危。将这样的国家界定为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略显草率,但这些日益崛起的诸侯国确实谋求民众的顺从,通过与家族无涉的官僚制度实行威权统治。我们确实可以嗅到一点极端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它们都敌视家族纽带)的味道。
在孔子的理想世界中,好的统治者就像慈父,拥有权威,但也很慈爱。我们可以在《论语》中读到这样的句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仁”的含义近似于“德行”,是指引人的“道”。在这里,我们可以把“道”比拟为《圣经》中的“称义之路”。礼制要求人们互相尊重。因此,孔子思想中的“黄金法则”听起来很像耶稣的教导:“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仁”的含义近似于“德行”,是指引人的“道”。在这里,我们可以把“道”比拟为《圣经》中的“称义之路”。礼制要求人们互相尊重。因此,孔子思想中的“黄金法则”听起来很像耶稣的教导:“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种思想看起来很保守,甚至是抗拒变革。但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孔子的保守主义是一种取代暴力和苛政的温和之举。莎士比亚也有保守主义思想。他认为,如果国王的言行符合自己的身份,父亲的态度变得公正、正直,那么世界就会更加美好。在中国,礼制要求人们自我约束,甚至是自我征服。在《论语》中,孔子曾提醒礼制的重要性,他的弟子引用《诗经》的句子回应: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作家凯伦·阿姆斯特朗阐述道:君子“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塑造的。就像雕刻师将一块砺石雕琢成美玉一样,人的修行也是如此”。
 这说明,“恰当的礼制”与冥想、祷告等自我提升的方法并无不同。礼制似乎是某种古代文明的回声,关乎个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这说明,“恰当的礼制”与冥想、祷告等自我提升的方法并无不同。礼制似乎是某种古代文明的回声,关乎个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诸侯争霸愈演愈烈,社会日益浮华和动荡,甚至鲁国也被篡位者搅得国无宁日,国君逐渐丧失了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恢复礼制就成了当务之急。在边鄙之地,蛮夷戎狄虎视眈眈。在华夏内部,一场更具破坏性的内战正在酝酿,将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后来的思想家发展了观点各异的论述。例如,孟子就认为孔子的论述过于精英主义,他提出的有关社会正义的思想更简单、质朴。但是,正如印度北部的动乱激发了悉达多、战争和被俘的经历刺激了犹太人一样,没有暴力的话,孔子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位教师。
鲁国的对手齐国非常担忧:鲁公会在孔子的教诲下奋发图强,进而侵略齐国。于是,齐国的统治者就给鲁公送去了财宝和美女,希望消磨他的意志。根据传说,这个招数奏效了。鲁公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不再遵循礼制。孔子出于愤怒决定另择贤君辅佐。看起来,孔子是个棱角分明的人。佛陀被信徒们塑造为圆脸、金身的形象,而孔子则是蓄须老人的形象。他身着官服,满脸威严。
然而,孔子本人无可指摘。后世御用的儒学掺入了很多刻板的教条,认为凡是背离传统的事情都是非法的。孔子首先被奉若神明,继而成为国家宗教的象征。不过,伟大的思想家只有通过后人的转化才能广为人知。我们是通过耶稣的门徒了解基督的,儒家思想也是如此。在孔庙中,继承和实践儒家思想的“四配”分列孔子的两侧,就如同四位福传者,次一级的则是“十二哲”,如同十二使徒。纵然西方没有孔子一样的人物——一位值得尊敬的保守的道德主义者,而非宗教的创始人——但是我们很容易就能对孔子产生亲近感。
孔子终其一生都未能找到可以效力的理想国家。他游历了很多地方,招收了很多弟子。他们将孔子的教诲和学说发扬光大。孔子又做过不少奇怪的工作,但再未回到诸侯的宫廷效力。《论语》等文献生动地刻画了孔子的形象。他很善于自嘲,喜欢美食(尽管他只吃得起家常便饭),酒量也不错。与古希腊的伟大导师苏格拉底不同,孔子与弟子们交谈是为了获得真理,而不是纠缠于繁复的逻辑,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辩才。不过,与苏格拉底的相似之处是,孔门弟子都很敬重老师,他们将孔子的思想传扬光大。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战争迫使人们思考何为良善社会、如何达至良善社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