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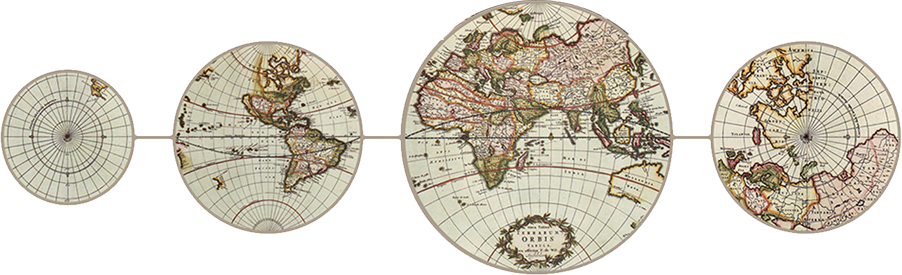
我们的第三个大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常常令人目瞪口呆,而非惹人喜爱。它与现代世界几乎毫无联系。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已成为一种全球化的媚俗视觉品位。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参观者都排起长队,争相目睹金饰或涂色遗迹。乘坐飞机的文化旅行者络绎不绝,游览帝王谷的神庙和墓葬群。埃及文化源远流长,成就卓著,但对后世的思维方式影响不大。对荷鲁斯和奥西里斯的崇拜曾在20世纪兴盛一时,但追捧的人不过是些喜欢超自然现象的半吊子或马戏团的泼皮无赖。神秘的法老曾吸引电影制片人拍出不少荒诞剧。但与犹太教、古希腊思想和古罗马政治的影响力相比,甚至与早期中国和印度思想家的影响力相比,古埃及思想的影响力都微乎其微。与古埃及的物质遗迹相比,美索不达米亚泥砖遗迹多已风化消散,简直不值一提。但他们在科学、数学和技术等领域的创造力远超前者,因为生活在沙漠边缘的埃及人只热衷于创造各种死亡仪式。
埃及学家(更不用说埃及人)或许会说,上述观点无知、褊狭。古埃及人是可敬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他们发展出一种复杂的宗教,护佑埃及人达数千年之久。一些低等级墓葬展现了埃及文化的多样性:与邻国相比,埃及人更尊重女性。他们热爱生活,醉心自然世界,沉醉于啤酒、美食、性爱和各种逸闻趣事。埃及人痴迷死后的世界,他们相信,今生的预备会为死后带来更多享乐。
埃及文化遗留下很多令人生畏的鸟首或犬首的神祇,还有神化的甲虫以及法老们冷峻的目光。那些大型纪念建筑至今仍屹立在原地,但似乎仅此而已。为何会这样?在历史上,古埃及文化缺乏与时俱进和因地制宜的灵活性,缺乏有形的变化——也就是说,埃及文化过于故步自封。古埃及文化存续了大约3000年,从前王国时期一直延续到古罗马时代,希腊化的法老们最终销声匿迹。在早期,尼罗河流域的艺术简单、质朴,显得与众不同。其中一些农民和动物的泥塑与美索不达米亚人的早期艺术颇为相似。但是,埃及的艺术风格很快就固化了,变得呆板、僵硬。虽然内行人能辨别出不同王朝、不同地区的艺术风格,但在2000年的时间里,埃及的艺术风格几乎没有发展。
法老哈谢海姆威的雕像完成于公元前2675年。如果将这尊精雕细琢的雕像与1500年后的法老雕像放在一起,你很难看出区别。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埃及登基。为庆祝他成为法老,人们在卢克索神庙内部又修建了一座小神庙。这座小神庙的壁画对面是1000多年前新王国时期的壁画,你会发现两者非常相似,尽管前者在细节方面略逊一筹。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对古埃及人来说,不存在“为艺术而艺术”,艺术只是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的表现形式。法力无边的神祇们居住在隐秘的世界,艺术的任务就是将这个世界描绘出来。此外,记录人与神的关系,以及用法老的权力恐吓旅行者或起义者,也是艺术的任务之一。因此,埃及的艺术总是重复同样的场景,有时将主人公描绘得异常高大。总之,埃及艺术不是一种展现人性的艺术,也不是写实的艺术。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在埃及登基。为庆祝他成为法老,人们在卢克索神庙内部又修建了一座小神庙。这座小神庙的壁画对面是1000多年前新王国时期的壁画,你会发现两者非常相似,尽管前者在细节方面略逊一筹。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对古埃及人来说,不存在“为艺术而艺术”,艺术只是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的表现形式。法力无边的神祇们居住在隐秘的世界,艺术的任务就是将这个世界描绘出来。此外,记录人与神的关系,以及用法老的权力恐吓旅行者或起义者,也是艺术的任务之一。因此,埃及的艺术总是重复同样的场景,有时将主人公描绘得异常高大。总之,埃及艺术不是一种展现人性的艺术,也不是写实的艺术。
在埃及历史中,尼罗河既是恶人,又是英雄。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与众不同之处是自南向北流。由于盛行风从北向南吹,乘船出航的人会发现,尼罗河是一条绝佳的双向传输带。更妙的是,尼罗河不仅为埃及人提供大量鱼类和野禽,而且(在纳赛尔修建阿斯旺大坝之前)每年定期泛滥,洪水带来的淡水和淤泥使土地非常肥沃。然而,洪水并不是非常规律。来得太早或太晚,太凶或太弱,都会破坏农业生产,引发饥荒。
周期性的混乱、起义和倒退是古埃及史的特点,这些似乎都与尼罗河的异常泛滥有关。然而,与两河流域、黄河流域和印度河(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流域的文明相比,埃及人是幸福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块4000英里长的沃土(这片沃土呈带形,北端是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尼罗河三角洲,是由洪水泛滥冲击形成的平原),还因为他们拥有许多天然屏障:东部和西部有沙漠和高山,南部是人烟稀少的非洲内陆地区。利比亚人、波斯人和神秘的“海上民族”都曾侵入埃及,但其遭受的外来入侵相对较少。更加平坦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及作为陆路通道的巴勒斯坦地区,更易成为战车和骑兵的争夺对象。
埃及易守难攻,无法被长期占领。因此,在上古世界,它总能恢复元气。
尼罗河也对政治产生了影响。事实上,所谓的“埃及”分为两大区域。这条“双向传输带”将生活在广袤土地上的人们凝聚在一起,使黑非洲的努比亚人和地中海沿岸的居民同住一个国度。“上埃及”位于埃及南部,更靠近非洲内陆;“下埃及”位于埃及北部,更靠近地中海。在大部分时间里,上埃及人都统治着下埃及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全面理解埃及人的地理观。今天,埃及人仍存在差异,体型和肤色均有所不同。与美索不达米亚相比,埃及是后起之秀,这部分源于其生长繁衍的土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片土地物产丰富,有很多动植物资源,人们根本无须过定居生活。随后,沙漠逐渐侵蚀了土地。来自南方的法老第一次统一了全埃及,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纳尔迈,意为“凶恶的鲶鱼”。

大禹和夏朝的故事说明,唯有集中化的王权才能将分散的村落凝聚成单一国家。为有效利用河流,埃及人也需要复杂的沟渠网络和灌溉系统,并且每年还要清理、挖掘和修复这些水利设施。因此,人们很早就形成了共同劳动的习惯,愿意离开农田,在远方修渠建堤。
这种习惯对修建法老的神庙非常有利。埃及人相信,尼罗河是从阴间流出来的。他们对尼罗河的泛滥忧心忡忡,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埃及人的信仰体系中,尼罗河诸神早就占据了重要地位。因此,当法老将自己与这条奔流的大河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获得了巨大的象征权力。地理不能决定一切。我们对河流方位或海岸形状的认知可能会被某一个人或某一种思想颠覆,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中屡见不鲜。倘若“地理决定论”有效的话,它正好在这片土地应验。尼罗河塑造这片土地,保护这片土地,为统治阶层提供服务,并最终抑制了这片土地的发展。
在古埃及的遗迹中,很少有像德尔麦迪那那般楚楚动人。德尔麦迪那是一处居民点,坐落在帝王谷的山脚,与卢克索神庙隔河相望。那一带有许多宏伟的遗迹。底比斯的卡纳克神庙气势恢宏。哈布城的拉美西斯三世神庙令人生畏,其目的是为了庆祝法老的军事大捷。这座神庙的规模异乎寻常,足以使任何一位20世纪的独裁者心生艳羡。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也有自己的神庙,“门农巨像”——一对面目全非的巨大雕像——矗立在神庙门口。而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的神庙则保留了一些如舞台布景般的遗迹。我们对古埃及人的想象都蕴含在这些古迹中。这是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场景,其展现的纳粹主义或极权主义风格令人印象深刻。
德尔麦迪那与众不同,它是一座由石墙和砖墙构成的灰色迷宫,目前残存的墙体只有几英尺高。德尔麦迪那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羊圈,或是苏格兰盖尔人遗弃的村落。不知为何,人们将它遗弃在沙漠的山丘旁。德尔麦迪那的上方有无数洞穴,地势较高,有的则被开凿在淡红色的峭壁之上。在一些洞穴附近,坐落着几个砖砌的小金字塔。与周边遗址相比,德尔麦迪那几乎无人光顾。这里曾经是一处居民点,居民都是为祭司和法老工作的工匠及其家眷。他们不是奴隶
 ,但工作非常勤勉。为赶在墓主去世前建成陵墓,他们常常要拼命赶工。这些工匠的酬劳通常是小麦、衣物,以及添加了蜂蜜的啤酒。工匠们周末休息(埃及的一周有10天,所以他们休息的频率比较低),平日则要工作8小时,每4小时休息一次。他们会召集贫困农民和奴隶来协助自己,以减轻工作强度。有2名监工负责监督工匠们的工作,他们就住在德尔麦迪那。每当法老去世,工匠们都会欢呼雀跃,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活计。在节日期间,工匠们会彻夜狂欢,喝得酩酊大醉。他们的手艺代代相传,制作木乃伊的技艺就是其中之一。
,但工作非常勤勉。为赶在墓主去世前建成陵墓,他们常常要拼命赶工。这些工匠的酬劳通常是小麦、衣物,以及添加了蜂蜜的啤酒。工匠们周末休息(埃及的一周有10天,所以他们休息的频率比较低),平日则要工作8小时,每4小时休息一次。他们会召集贫困农民和奴隶来协助自己,以减轻工作强度。有2名监工负责监督工匠们的工作,他们就住在德尔麦迪那。每当法老去世,工匠们都会欢呼雀跃,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活计。在节日期间,工匠们会彻夜狂欢,喝得酩酊大醉。他们的手艺代代相传,制作木乃伊的技艺就是其中之一。
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工匠们会抽空修建自己的陵墓,为死后世界做准备。他们的日常工作是修建庞大的建筑,或深挖地下的岩石层,为新王国时期的大人物准备安息之所。但同时,工匠们也为自己准备身后事,修建小型的金字塔和刻有精美壁画的墓室。这些墓室通常被建在地下20至30英尺的地方。壁画是彩色的,颜色鲜亮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壁画的内容包罗万象,例如歌颂夫妻恩爱、劳动者的家庭、周围的自然世界(包括农作物、鸭子和猴子),以及丰收的粮食等。普通人就安葬在这样的墓室中,远离那些“充满诱惑”的巨大神庙——即便在古代,法老的陵墓也会引来无数盗墓贼。因此,在近代被发掘前,这些平民的墓葬并未遭到破坏。
这已足够有趣。但是,这些人还会将自己的思想记录在小块的石灰岩(这些石灰岩是挖掘墓穴时产生的建筑垃圾)、陶片或莎草纸上。他们使用的是简化的通行文字。在3000年前,人们抛弃了这种文字,但大部分文字都能幸存至今。这些陶片记录了民间故事、法律诉讼、爱情诗、解梦、流言、争斗、智慧箴言、继承权的剥夺(一位妇女剥夺了自己孩子的继承权,因为她认为自己年老时这些孩子没有赡养她)、衣物清单和一头跛驴引发的麻烦等,甚至还有治疗痔疮的药方(将面粉、鹅的脂肪、盐、蜂蜜和绿豆混合成膏状物,在臀部连续涂抹4天)。
在这些记录中,有个叫帕尼卜的工头。他心肠歹毒,经常残忍地威逼其他工匠。他从皇陵中盗取财物,逼迫其他妇女为其缝制衣物。他还与一个叫图伊的有夫之妇通奸,而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最终,法老的官员将帕尼卜捉拿审问,剥夺了他的职务,但他最后的下场我们一无所知。这场官司或许是由村民之间的纠纷引发的,但这场审判说明埃及拥有一个公正、有效的司法体系。
这座村庄的故事记录了遥远历史中普通工匠及其家眷的心声。这些工匠不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们拥有专业技艺,受人尊敬。这些故事还反映了这些工匠与统治者拥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共享死后的世界。这些人是石匠、画师、木匠、裁缝和厨师,以手艺为傲。他们的伙食不错,有鱼有肉有蔬菜,还有面包和啤酒。他们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并借此理解整个世界。他们相信法律体系能惩恶扬善、公正无私。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有关古代劳动者生活在一个半奴役的世界中的想法就统统是错误的。这些村民的生活难道比不上今天生活在公寓楼里薪水微薄或失去营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