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 一 章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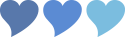
时间改变的不仅是脚的大小,还有人的心。
她曾以为,穿高跟鞋的女人,都应该是优雅地行走在路上的。
而此刻的她,飞奔在上海的骄阳下,那些化着精致妆容的白领女子,都用异样的眼神望向她。
脚上的那双鞋,隔着两年时间,又穿到了她的脚上,她这才清楚,原来两年的时间,变的不仅仅是心,连脚的大小都变了。
分明记得两年前,冯伯文把这双鞋送给她作为生日礼物,冯伯文托着鞋盒,温情款款地说:“亲爱的曼君,生日快乐。只要你帮我顶一次罪,我们的公司就能继续运营下去,等你出来,我带你过好日子。”
那双鞋,是黑色缎面镶嵌着珠宝,极高的跟,多么精美的一双鞋啊。
也是那双鞋,将她送进了监狱。
冯伯文的罪名,她一个人顶下来了,依照法律判刑两年。
在监狱的那两年,冯伯文没有去看她一眼。
两年后,她穿着这双鞋,飞奔在马路上。
你有见过一个穿着高跟鞋的女子在马路上飞奔吗?那样的女子,大多是在爱中受了伤害的。
阮曼君穿着近乎是三寸高的高跟鞋,绕过静安寺,从华山路往希尔顿大酒店跑。两年,上海变化这么大,原来的弄堂都拆迁了,幸好以前上班就在这附近,否则真会迷路。
她是要去阻止一场婚礼,她身无分文,甚至连打车的钱都没有,她只能不停地奔跑。
她短短的发,因为汗水和泪水打湿,贴在脸上,她边跑边在心里想,待会该怎么面对那场新郎新娘百年好合的局面。
脚上的高跟鞋竟一下就脱离了脚,飞了出去,一下就飞进了一辆半开着的车窗里。那辆车正在等红灯,车里坐着一个穿亚麻色西装的男人,那只鞋不偏不正地砸在了男人的头上。
她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光着,匆匆跑到了车边敲窗户,她甚至还没来得及把脸上的泪水擦干。她局促小声地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砸到你的。”
他的额头被高跟鞋砸破了点皮,他紧抿着薄凉的嘴唇,不怒而威的样子。
正想发作,却见是一个脸色苍白瘦弱的女人,满脸的汗水和泪水混杂着,他将鞋递给她,附送了一张纸巾给她,他一言不发,他一贯不喜欢和脏乱的女人多说话。
她点头,握着纸巾,指着他的额角问:“你的额头破了,没事吧?”
“没事。”他答道。他眼睛看着前方的红绿灯,显示还有十秒就可以通行了。要去参加一个商业伙伴的婚礼,不能误了时间。
她只能看到他轮廓鲜明的侧脸线条,她正欲离开时,又回头问他:“打扰一下,现在几点了?”
这时红灯跳了过来,他的车已经启动,他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车随着庞大的车流缓缓离去。
他从车的后视镜里,看着她落寞地站在路边,手提着一只高跟鞋,突兀的锁骨,消瘦的身子,同她身后那栋繁华大厦相比她显得那么的卑微。
这让他内心最深处的那一块隐秘一下被揭开,曾经也有一个女子,如她一样,孤孤单单地站在马路边,像是找不到家的孩子,等他带着回家。
她没有想到他会把车倒了回来,车在她身旁停下,从车里传来低沉的声音“十一点一刻。”
“十一点一刻,来不及了。”她嘴里念着,来不及了,等她跑到酒店婚礼都该举行了。她凄然一笑,又何止是十一点一刻就来不及了,一年前两年前就来不及了。
一个女人可以义无反顾地挡去男人身边所有的劫难,却挡不住男人的桃花劫。
“上车!”车里又传来他的声音。
没有任何感情的声音,就像是命令一样,她没犹豫什么,打开车门,上了车。车里有着极好闻的味道,不是花香,更像是一种木香,浅浅的香气,让她有种从烈日灼热下一下子就回到了清凉森林的感觉。
“去希尔顿酒店。”她亦是简洁的语气告诉他。
他用余光瞟着她,杂乱的短发,满脸的汗渍,一张脸被晒得通红,穿着发黄的宽大白衬衣,牛仔裤,一点也不像他平时接触的那些精致女人。
而她竟然是要去希尔顿酒店,这正和他是同路的,他是要去参加一个商业伙伴的婚礼。
一路上,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车开到了希尔顿酒店,车还没有停稳,她就打开车门跳下了车,高跟鞋没站稳,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她姿态狼狈地撑在地上,手腕膝盖都磕破皮,白衬衣上沾满了灰尘,鞋跟也断了。
而她一抬眼,就看见新郎冯伯文站在酒店门口,白色的西装上,别着的那朵红花上清楚地写着“新郎”,冯伯文在迎接参加婚礼的来宾,站在一旁穿着红色礼裙的是新娘。
新娘身高一米七左右,长长的礼裙穿得十分高贵,松松挽着的髻,那么的优雅。
整个酒店都被冯伯文包下来了,酒店的门前挂着一条长长的横幅,写着:新郎冯伯文与新娘雅琪喜结良缘,百年好合。
她看看自己,再看看穿着华服高贵的新娘,她突然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来这里之前,脑子里闪现过的那么多假想的画面,她想也许自己会冲上去狠狠甩冯伯文和那女人一个耳光,然后就哭天抢地的指责冯伯文的负心。也许干脆就很冷静地上前,犀利的眼神看着这一对人,诅咒他们早结早离。
可是,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她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只能狼狈不堪地站在酒店的台阶下,抬头仰望着上面一对璧人在笑脸迎宾。
“冯伯文……”她用尽全身的力气喊了一声,声音很大,把坐在车里的他也惊了一下,这个瘦弱的女子怎么有这么强大的爆发力。
众宾客都望向了这边,都很快就明白了,都在小声议论着,而新娘雅琪的脸色都变了,冯伯文急忙敷衍了一下,就往台阶这边大步地走来。
她站在原地,望着冯伯文朝她走来,冯伯文当新郎就是这样子啊,看起来还是那么的春风得意,经历了那么多的大风大浪,这个男人脸上看不出一点沧桑,仍是两年前的俊逸模样。
冯伯文走到她身边,就像是见到了瘟疫一样,脸上的笑容僵着,低声说:“你怎么到这来了,你来干什么!我今天结婚,到场的宾朋都是商界名流,你别捣乱!”
她看着冯伯文的脸庞,她想不过是两年的时间啊,两年前她为冯伯文背负一切罪责,她傻兮兮地坐了两年牢,怎么能想到再见面,会是这样的一个境地。
确实是结婚,只是新娘换了人。
她没有作声,只是望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像是失语了一般。烈日下,她的发丝滴着汗,她知道自己的狼狈不堪,她在没出狱之前,想了好多好多要说的话。而今面对面,在喊了一声冯伯文后,她不知道该再说什么了。
周围没有一丝风吹过,空气都带着狂躁的闷热,压着人透不过气,冯伯文没有耐心再耗下去,宾客们都在等着,冯伯文见她不说话,便说:“你赶紧走吧,瞧你一身脏得和乞丐一样,我给你点钱,去买些吃的穿的,找个地方先住下,我改天再找你。”
钱递了过来,她却没有伸手去接,她只是盯着冯伯文那只握着钱的手,手指上戴着的婚戒,她全身都在轻微地颤抖,她抱住自己,想让自己可以平静一点。
冯伯文气得朝四周环视,又转身朝身后的新娘雅琪笑了一下,见曼君仍是一言不发也不拿钱,压低了嗓音凑近她耳边,对她说:“如果你不要钱,那请你马上走,马上给我走。”
她喃喃地点点头,拖着已经透支了体力的身子,伸手拉开车门,想上车走,见冯伯文也要走,又轻声喊了一声冯伯文。
冯伯文回头,不耐烦的眼神扫过来。
“祝你幸福。”她强装出微笑。说完在眼泪落下的前一刻,仓皇钻进了车里。
“我远方一个亲戚的女儿,老家发了洪水,想来投奔我,大家不要受影响,婚礼照常进行。”冯伯文大言不惭地说。
他淡漠地看着这一切在发生,不过是一个老套的负心汉故事,本是来参加冯伯文的婚礼的,她又钻回了他的车里,这倒让他不好下车了,他一向是不喜惹事端的,他冷冰冰地说:“下车!”
她掩面,带着哭腔说:“开车,带我离开这个地方,好不好?”她不想自取其辱待在这个地方了,她得到了答案,她不是那种喜纠缠的女人,既然都亲眼看到了,她只想速速离开这里,不见,再也不见才是最好的绝望。
车内木香缭绕着,那么得安宁。他决定开车绕到远一点的地方,再让她下车,这样既自己落得清净,也算是帮了冯伯文甩掉一个包袱。
她告诉他,那个新郎叫冯伯文,两年前,是答应了要娶她的男人。为了这样的一个男人,她把所有的罪名都一个人背了,坐了两年牢,本以为该迎娶的是她。谁知道,冯伯文竟然有了别的女人。
他没有发表任何观点,他听着,没有说话。
她就是因为知道他不会说什么,所以才和他说的,就当是自言自语倾诉一下,说出来,心里也许会好受一些的。
她用手背拭着不停落下的泪,望着窗外一闪即过的高楼说:“不过没关系,早知道更好,我可以再找一个好的。我跟我自己说过,我没有那个男人我一样活着,男人嘛,没有了怕什么,又不会死!”
“但我这一辈子,我只喜欢过他一个男人。”她说着,泪又涌了出来。
他将车上的一盒面纸,放在她身上,也不看她,眼睛看着前方,开他的车。
“为了他,我坐了两年牢,连律师资格证也吊销了,我为了什么,我为了什么……”她说完又哭过后,真觉得轻松多了。哭过就好了,说得挺有道理的。
他的车在上海市区绕来绕去,最后绕到了高速上,他想,不如就把她丢在高速公路上,让她自己慢慢走吧,至少她是没法走去破坏冯伯文的婚礼了,下次聚会非要冯伯文这小子乖乖认他一个人情才行。
“下车。”他把车迅速停靠在路边,命令她下车。
她点头,下车,望着他的车绝尘而去。
他就那样把她丢在了高速公路上,他看到她的那双高跟鞋,东一只西一只歪在车上,其中一只的跟都断了,只剩一点点皮还连着。
高跟鞋遗落在他的车里,她光着脚,走在被太阳晒得很烫的路面上,周围都是快速一闪即过的车辆,她不清楚自己身在哪里,又要往哪里去,只能是沿着高速公路往前走。
他车开到中途,心里却乱了,是从未有过的慌乱。想到她是刚从监狱里面出来,身无分文,手机也没有,也没有认识的人。把她独自丢在高速公路上,还赤着脚,她苍白虚弱的面庞,他又担心起她来。
真是奇怪,这是怎么了,怎么计划全被这个女人给打乱了!他又不顾安危地在高速上调转方向,加速朝把她丢下的那段路开去。
此时的她,拖着几近是脱水的身子,踉踉跄跄地走在公路上,脚底很快就起了几个水泡。巡检的交警车辆驶过这里,竟发现一名女子走在高速公路上,忙拦下了她,将她带到了车上。
他的车就在警车的不远处,他看到了这一幕,他加速驶过警车边,见到她虚脱地靠在车座上,他内心也就安定了,被交警带走,至少她会是安全的。
冯伯文的电话打来,问他怎么还没有到,他突然对这个冯伯文有了些厌恶,男人玩玩女人正常,可冯伯文让一个女人去顶罪坐牢,自己倒逍遥高调另娶名媛,这让他觉得冯伯文太不像个男人了。
既然如此,他也不想去赴这场婚宴了,就推辞不去了。
她坐在警车上,一口气喝了一瓶矿泉水,交警将她放在了市中心,又塞给了她一百块钱,让她去买双鞋穿。
她六神无主地行走在繁华的夜景里,到处都是一对对相拥的恋人,看起来,爱情不该是折磨人的东西啊,为什么她好像被全世界抛弃了一样。
两年的与世隔绝,她再一次回到上海,这个城市变得更加诱惑,却发现过去的那些朋友,都断了联系,她身上没有一分钱,也没有什么亲人了,独有个在老家的外婆。父母都在几年前就相继过世了,她想到自己坐两年牢,父母的墓前都没有人去拜祭了,该多荒凉,她不由心里愈发难过。
她要找到工作,挣钱,然后回家乡看望外婆,给外婆盖一座舒适的房子,去父母的坟前上柱香,烧些纸钱。
她想起了多多,对,找多多,多多是肯定能收留她的。
李多多,诨名多姑娘,缘自《红楼梦》里的鲍二家的,因为为人轻浮,只要男人有钱或有权,都可以轻易地被搭上。
多多的更贴切名字,应该是叫“拜金小姐”,当年在大学里,她和多姑娘是一个寝室的,旁人都不喜欢又拜金又随便的多姑娘,而她倒不排斥多多,能帮多多的时候她还是会帮。
所以她入狱后,多多还来监狱里看过她几次。
走投无路了,总不能露宿街头吧,她只要凭着记忆里多多的手机号码,在电话亭旁拨了多多的号码。
真没想到电话还就打通了,多多在电话那一头气壮山河地说:“喂,哪位啊?说话大点,老娘在唱K呢!”
“多多,是我啊,我是曼君,我出狱了。”她抬高了声音说。
电话亭的老板一听出狱二字,马上用异样的眼神打量了阮曼君一眼。
多多欣喜地让她待在原处别动,说十分钟后会出现在她面前给她接风洗尘。
自己所在的位置告诉了多多,就等着多多来接自己了。
她蹲在电话亭旁边,抱着自己的膝盖,她等着多多来接自己。她有些旧了的白衬衣,杂乱的短发,瘦瘦干巴的身子,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糟糕。
上海的夜晚那么的繁华,可繁华背后的凉寂,谁又能懂?
如果上天能再给一次机会,她绝不会为了一份所谓的爱情,葬送自己。她后悔了,她曾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后悔,可如今,她真的后悔了。
见到李多多,彼此都很难认识彼此了。
她抬眼看着多多,俨然是上海里走出来的摩登女郎,穿着细细镶着水钻的高跟鞋,黑色香云纱及膝裙,挎着爱马仕的包包,手指上艳红的丹蔻,金色的卷发,香艳的红唇。
简直是国色天香。
而她,短而凌乱的头发,破旧的衬衣,还光着脚,满脚的脏。
多多抱着她,在她肩上拍了几下,轻轻地说:“没事了,亲爱的,出来就好,有我在呢,什么样儿的男人找不着啊,他冯伯文就是个乌龟孙子!”
她乖乖地跟着多多。多多牵着她,上了多多的宝马车,然后去了徐家汇商业街,她看着多多给她张罗着买了两套长裙,又买了两双鞋,刷卡包好了之后,又去洗了桑拿。
多多将一件紫色长及脚踝的裙子递到她手里,让她穿上,又配上一双鞋跟上绘着芙蓉的金色高跟鞋,她站在多多的面前,有些羞涩,伸手遮在了胸前的春光乍泄之处。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多多将自己佩戴的祖母绿吊坠取下戴到她的脖子上,她看着镜子,竟恍惚得认不出自己来了。
“可是,多多,你把我打扮成这个样子,要做什么呢?这裙子这么长,分明就是晚礼服。”她望着镜子里的多多,疑惑地问。
“你穿着吧,过会儿我带你去个地方。我告诉你,做女人,你要是找不到柳下惠那就不如找个西门大官人。”多多点上一支烟,抽了一口,修长的手指,夹着烟,打量着她。
她摸着自己刚洗过的及耳短发,飘着动人的香气,衬着她精致的锁骨,她对自己说,即便是没有了冯伯文,她也会美丽的活着,没有那个男人,总会有更好的。
那是一栋爬满了常春藤的哥特式别墅,多多说这房子在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就屹立了,住着的是一对西班牙人夫妻,那对老夫妻去世之后,房子就被后人专卖给了袁家。
袁家世代是行医之人,抗日战争时,开了一家制药厂,成为首批爱国民营企业,制药厂规模发展至今,已经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企业,袁正铭就是现在的董事长。
她听着多多从进楼就开始介绍袁正铭,但她的目光都集中在这栋洋楼上,这栋有些斑驳但不掩风花雪月的洋楼,简直是旧上海风华绝代的再现。
多多挽着她,笑语盈盈地与擦肩而过的人问好,似乎早已熟络这里来往的上流人物,多多在她的耳际浅笑着说:“今晚是我很重要的日子,豪门相亲,你也许只在电视上看到过,今晚我就带你体验一番,当然,你遇见好的,只管扬帆直上,除了袁正铭——他是我的。”
她微微点头,明了这不过是有钱的企业家们另类的选秀,目的是找情人而已,她对这种交易毫无兴趣,既然来了,也没有走的道理,况且她又能往哪里走呢。她就当是参观一栋漂亮的洋楼了,她对旧上海的风情十分感兴趣,尤其是石库门的洋楼,这比这场豪门相亲宴更能吸引她。
这是一栋复式洋楼,奢华极致,布局与摆设俨然是三十年代旧上海滩复古的模样,几位衣冠楚楚的男士站在落地窗旁,举着红酒杯,高谈阔论。
她在自助餐桌旁站着,肚子不争气地闹腾了起来,她挑了几种甜点吃,喝了一杯橙汁,然后就坐到大厅角落一旁,挑了一本杂志,见多多正与一个穿驼色西装的男人在浅笑谈话,期间多多的肩膀有意地在男人肩上擦过。
想必这个男人就是多多相中的袁正铭,她又打量了一眼,袁正铭倒不像那种大腹便便的有钱男人,看起来满是书生之气,脸面生得清俊,站在多多身边,倒显得多多有些铜臭气了。
阮曼君落寞地坐在角落高脚椅上低头翻阅杂志,旁边餐盘里放着一些她爱吃的巧克力甜点,身边那些觥筹交错与她无关,她就当是陪多多过个场子。
直到晚宴开始,来宾都到齐,她才抬头看周围整个大厅。那是怎样的一个场面啊,她以为只有在百老汇的电影里才能看到,十几名打扮得气质不同的女孩,穿着各不同款式的长裙,或典雅,或性感,都是活色生香。
多多也周旋在其中,见曼君孤零零地待在大厅冷清处,就绕到她身边,拿过她手中的杂志,说:“坐在宴席上的,都是商界名流,他们都是离异或者未婚的,莲姐就是这场豪门相亲会的策划人,她专门为这么富豪和想嫁富豪的女孩提供媒介。你知道吗?能进这个相亲会,要交八万中介费的,你的我给你交了。你怎么能花八万块钱当进图书馆一样就看杂志呢?”
她并没有想到,原来参加这场富豪相亲宴会的女孩子,都是交了中介费八万块钱来获取一次和富豪相亲的机会,冯伯文已让她对爱情失望,要是早知道还让多多花了八万块钱,她是断然不会来的,她对这种花钱选秀找情人的男人毫无兴趣。
她立了起身子,反正肚子吃饱了,再待下去也没有意思,她对多多说:“多多,花了八万块钱你带我来这里?你这钱恐怕是要打水漂了,我对有钱男人没好感。你去招呼你的袁正铭吧,我先回车里等你。”
多多拉住了她,在她的眉心上轻轻点了一下,说:“傻妞,多好的机会啊,你对有钱男人没好感,那你对钱总有好感吧,谁不爱钱啊!谁跟钱作对不就是跟自己作对吗!你就先坐一会儿,待会儿我给你介绍个好的。再说你要是走了,待会我醉了,被哪个色鬼揩油了怎么办?”
她只好又安静地坐在高脚椅上,吃自己的甜点,冷艳观望一对对的男女成功配对,相互挽着在跳着慢四。多多也和袁正铭相谈甚欢,那个所谓的中介人莲姐穿着唐装,双手抱怀握着一杯红酒,微笑着看着一对对跳舞的男女。
那是一本旅游杂志,她翻开一页有着加州瀑布的景观图片,那么的美,在阳光的照耀下,那一条瀑布呈现着像火一样的颜色。她想到了自己小时候,跟随着爸爸下海出船,落日黄昏之时,海面上就是这样的颜色,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她记起当初毕业刚来上海,她下了火车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黄浦江,她对着黄浦江大声喊着:“上海!我来了!”
也是在黄浦江的夜景里,她认识了冯伯文,她想如果不是冯伯文,她又该是在怎么样的一番境遇里,也许她正在高级写字楼里做着白领律师,和一个同样是公司职员的男人结婚生子过最简单的生活,为在上海谋求一个家而奋斗。
她望着杂志竟发了呆。
多多染着妖娆丹蔻的手指在杂志上弹了一下,多多的脸嫣红一片,像是醉了,手搂着她的脖子指着对面沙发上一个同样握着杂志的男人说:“瞧见没?那个穿着白衬衫黑色西裤的男人,他就是佟少,忒有钱。你可别看他有时开奥拓车,人那是开厌了宾利,弄辆奥拓玩玩,他都能把法拉利的车给拆了用零件来组装奥拓车。”
她听了,再一打量,他不就是那个把她丢在高速公路上的男人吗。要不是交警带她回市区,她肯定还在高速公路上找不着北,她还傻兮兮地感激他,想想就对他没好感,便说:“败家子罢了,烧钱而已。”
多多拉着她站起来,又给她整理了长裙和额间的发丝,说:“你可别以为佟少是个纨绔子弟,他家的企业全是靠他经营起来的,在美国留学两年回来后就接手公司,把公司办得越来越大。我可以说,他身边的女人都爱他。”
“那么你呢?”她合上杂志,反问多多。
多多爽快地笑了一声,在她的耳边说:“我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我有自知之明,佟少根本都不喜欢我这类型的,我去招惹他等同于自寻没趣,倒不如做普通朋友招呼着,你瞧那个女人,就属于一个不自量力型的。”
曼君顺着多多的目光望去,是一个穿着黑色皮裙吊带袜的女人,借着酒劲,端着酒杯就往他的身边靠近,结果扑了个空,他直接站起身来,扔下手中的杂志,潇洒地转身就走。高大颀长的身子,一举一动都牵着在场每一个女人的眼神。
“看得出来,他是多么的骄傲。”曼君想起搭他的车时,他惜字如金的谈吐,对白那么的简单,“没事”、“上车”、“下车”,好像就这几个词,实在是傲慢。
多多鼓动着她去找他主动搭讪,她倔着不去,那么多貌美如花的女人都前仆后继地扑过去,她才不去,倒不如多吃点甜品,她继续在餐桌边挑选形状可爱的小甜点。
八万块钱,就是来吃点心来了。
多多又劝说她,说其实今天的相亲会最主要就是为佟少举办的,要是她能够攀上佟少,那就是荣华富贵享不尽了,那冯伯文又算是哪根葱呢。
她被多多的苦口婆心地教导着,她纹丝不动,淡然地将甜点往嘴里送,心都苦了两年了,苦苦等待的两年,得吃多少甜点才能去掉一点苦涩的滋味。任凭多多把佟少说得和二郎神一般神通广大,说得就像是有着西门官人的外型和柳下惠的操守,她倒是一点心也没动。
这时一个谢顶了的中年男人靠近了过来,嘴唇黑而厚,嘴角边还长了一个瘊子,大腹便便,一米六五的海拔,还真糟蹋了身上的那件名贵西装,被其撑得像是雨披。
她厌恶这种男人,大多都是家有贤妻,不过是有几个臭钱就在外养情人二奶小蜜的,满脸横肉,她避之不及。
多多却拉住了她,对她使了使颜色说:“来,我给你介绍认识认识,这位是秦总,秦总可来头不小啊,台湾来的,满身带着的都是宝岛的气质啊。”
曼君勉强淡淡地一笑,岂料这位秦总已伸出肥厚的手掌想握手,她将手中的盘子直接就递到了秦总的手上,直白地说:“不好意思,我肚子不舒服,去一下卫生间。”
在卫生间,她冲洗了一下脸,将脸上的妆都冲洗去,额前的短发沾湿了,她望着镜子里褪去妆容的面孔,还是素面朝天的舒服。只盼着这场宴会能早点散去,她实在是没办法再待下去了,除了那些诱人的甜点外。
她顺着走廊上的壁画看着,都是文艺复兴时的一些画作,有写实主义,也有抽象主义,她一幅幅的看着。走到了走廊的拐弯处,一个大的露台,周围是廊柱绕着,摆着几张躺椅,中间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些甜点和酒品。
索性她就躺在了一张椅子上,仰望着天空上的那轮皎月,想着自己为冯伯文顶罪坐牢的两年,总是痴痴地望着外面的天外面的世界,总盼着出来会有爱情会结婚的,到头来婚礼举行了可娶的不是她。
而她是那么的懦弱,她甚至连给那个男人一个巴掌的勇气都没有,她甚至连骂一句负心汉王八蛋的冲动都没有,可是她,确实是后悔了。她到这里就甩手朝自己的脸上狠狠抽了一巴掌,她说道:“阮曼君,你真贱!”为了一个男人这么的没有骨气!
她抽完自己,就拿起桌上的一瓶酒,瓶盖是开启过的,她直接就往嘴里灌,阮曼君,你也会有今天啊,你不是一直都自欺欺人地认为那个男人还爱你吗,为此在牢里不管谁说你被男人骗了你都和谁急,还自我安慰说伯文是太忙了,不然他不会不来看我的。娘的,他又不联合国主席日理万机!
不过是她自己骗自己,不过是她逃避现实,甚至在快要出狱的时候,她总在梦里惊醒,她其实已经渐渐清醒,残存的希望总是要幻变成泡沫破灭。
她想起小时候,跟随父母在海边渔船上生活的那些年,她的脚上总是被系着一根粗粗的绳索,绳索的另一头绑在船舱中一个固定的木桌腿上,因为父母忙着捕鱼,怕她会掉到海里去。
船飘飘荡荡的,绳子只有半米长,她的活动范围只有半米的范围,她是一个从小就孤单的女子,记忆里的童年就是在飘飘荡荡的船上度过的。
她的世界原本是很小的,从小到大那些年她就一个人在船上的大木桌底下玩耍,大木桌下有一个小椅子,她玩累了就趴在小椅子上睡着了,那个木桌子底下就是她的世界。
后来,长大了,离开了渔船,父母随后也先后去世,她独自在外求学,毕业后在上海求职,她渴望着大世界,她认识了冯伯文,孤身在监狱两年,终是分开了。
细想这些年,毫无趣事,她灌着自己酒,看着身边的白色大圆桌,突然就有了一种归属感,少年时在船上的木桌下的那些年,虽孤单,但她一点也不担心,无忧无虑的。而今身处繁华大上海,却无限的惆怅,一无所有,踽踽独行。
她脱下了高跟鞋,醉眼迷离的,钻到了白色圆桌下,坐在桌子底下,手里还拿着酒瓶,长裙拖在地上,她喝着酒,打个酒嗝,忙捂住了嘴,然后傻笑几声,笑到眼泪出来。
于是抱着自己的膝盖,下巴放在膝盖上,酒瓶被扔在了一边,她抬眼看,拭去眼中的泪,好像又回到了在船上的那些年,飘啊飘,她以为遇见冯伯文之后,她不用再飘了,不在再在风雨中飘荡了。兜兜转转,她依旧是一个人。
她抱着一只桌腿,难过地哭着,这多年了,别人是身边的亲人家人越来越多,而她,却是越来越一无所有,她嘴里念着:“我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都不要我,都不要我!我还是一个人飘……”
晚风吹着,她觉得累了,一直在路上奔跑,为爱而追逐,最后她什么都没有得到,真的累了,她就在桌子底下睡着了。
她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又回到了那条船上,她蹲在桌子底下画画,会听到父亲的捕鱼的劳作号子声,还有母亲欢喜地说着又有一条大鱼,那么的清晰而真实,就好像他们从未离去。
佟卓尧缠绕不过那些朋友的介绍,见了一个个花枝招展的妞,他倒只觉得视觉疲劳,推辞了一下跑到露台上,有个喘息的余地。他见自己刚打开的一瓶酒不见了,他坐在椅子上,百无聊赖。点燃一根雪茄抽着,他看着星空,想着自己浑身的铜臭味,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遥远了。
这几年来在商场里摸爬滚打,挣了不少钱,可钱就是个混账玩意,多则无益,少则有害,他失去的又何止是这些钱能够赎回的?外界人看来佟卓尧是何等的叱咤商界风云人物,在各个商务杂志上他总是被冠以“天才商人”,可真正坐在他这个位置,又是何等的寂寥。
阮曼君此刻仍在圆桌底下抱着桌腿酣睡着,酒瓶就歪倒在脚边,却不知多多正到处在找她,多多问众人有没有见到一个穿紫色长裙的女孩。
这时有人推了一个穿紫裙子的女孩出来,多多一瞧不由得直摆手,眼前的女孩胸部北半球全部露出,整个人最先入人眼的就是两个半圆,这哪里是曼君的风格。
多多又找到了露台上,见佟卓尧独自坐着抽雪茄,便笑迎着上去问:“佟少,你在这里抽闷烟啊,外面那么多美女你怎么反倒寂寞了。”
他淡淡地说:“里面太吵。”
这样多多也不好再多攀谈,便问:“佟少,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紫色长裙的女孩啊?看起来很瘦,不是丰满的那个。”
“没有。”他依然是简洁的回答。
多多素来是知道佟卓尧的孤高,或许商人的天性就是这样的吧,多多转身就准备走,去别处找找曼君,心里还惦记着袁正铭,怕有别的女孩子趁机找袁正铭攀谈。
“砰……”桌子底下突然就发出来了声音,多多扭过头又望了过来,他也好奇地低头一看,都同时看见了抱着桌腿睡得正酣畅的曼君,她可能是伸了一下腿,用脚将酒瓶踢滚到一边发出来的声音。
她被多多从桌子底下给拖了出来,多多轻拍打着她的脸,才把她给拍醒,她才恍然知道自己竟在桌子底下睡着了,就站起身子,有些晃晃悠悠搀扶着多多。走过他身边时,她抱歉地微微笑了一下。
他倒莫名其妙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女人,竟然喝了他的酒,还醉卧在桌子底下洒脱地睡着了,真是个笨得可以的女人。他再想想,又觉得她的面目有些熟悉,像是在哪里见到过,又一想,她不正是白天在路上遇到,还被他丢在高速公路上的女人吗?
怎么她跑来参加豪门相亲会了?他摇摇头,嘴角上浮起一丝不屑的笑意,又是一个贪慕虚荣的女人,上午还哭丧着脸跑到前男友冯伯文的婚礼上悲伤欲绝,晚上就改头换面参加豪门相亲,无非就是想找个富豪嫁了。
想到自己白天还真为此对冯伯文这小子有了看法,现在想想,其实冯伯文甩了她也是对的,女人都是白细胞比男人丰富的啊,受了伤出了血,总能迅速地自我愈合,很快又去寻找下一个猎物。他想了会儿,自嘲了一下,犯得着为这样一个装得可怜兮兮,实则贪图荣华的女人伤脑细胞吗?
他起身,不想在这地方久留了,要不是好友袁正铭和家族里的长辈莲姐极力邀请,他才懒得浪费时间在这样的一个派对上。
她醉醺醺地被多多拉到了大厅里,音乐放着慢四舞曲,灯光渐渐暗了下来,十来对男男女女都在跳着慢四,多多把她扶到沙发上坐着,就和袁正铭一起跳舞去了。
那位宝岛来的秦总肥大的臀部坐在了她身边,笑盈盈地看着她,横竖地打量着,她十分不自在,手撑在沙发扶手上,头泛着晕。
秦总端着红酒杯递到她面前,浮肿的大眼泡像金鱼眼一般看着她,说:“阮小姐,你刚才去哪里了,我到处找你呢,咱俩喝一杯吧,我给你钱,只要你陪我喝杯酒,我这要求不高吧。”
她转过脸,白了他一眼,懒得说话。
“真美,连白眼都这么美,好,我为了阮小姐的美貌自饮一杯!”秦总一饮而尽,眼神又扫了过来,见她不作声胆子又放肆了起来,说:“阮小姐,不知道你的身体是不是和你的姓一样的软呢?”说着手就要伸了过来。
她簌地站起身,虽然酒性让她头重脚轻,但她实在是不想和这个肥头大耳的家伙待下去。
秦总将酒杯啪地重重放在茶几上,对站在不远处的莲姐喊道:“你都找来的是什么小姐,一点也不给老子脸面,我有的是钱,你去找那个姓阮的谈一下,我要她陪我!我可是花了钱给你莲姐的面子才来参加相亲会的!”
莲姐笑着走过来,给秦总道歉,并说会去找曼君谈谈。
她蹲在角落里,眼睛被周围的灯光刺得睁不开,模模糊糊只看见那个多多口中的莲姐站在她面前,端详着她,说:“你就是多姑娘带来的阮小姐是吗?秦先生要你陪他喝酒跳支舞,你过去应付一下。”
她摇摇头,不说话,她蹲在地上抱住了自己的腿,身子往前摇啊摇,眼泪一颗颗地往下落。她以为自己醉了就不难过了,可是醉了之后,反而更清醒地感受到了疼。
莲姐见她这副模样,也没说什么,就只好去向秦总道歉,看能不能换一个姑娘陪伴。
那个秦总也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态度坚决,就像是他的钱是万能的没有解决不了的事,一听说她还是不愿意,就走到她跟前,从兜里掏出一叠钱,像是丢给乞丐一样丢在她脚边,说:“你来的目的不就是想嫁个有钱人吗?你装什么清纯装什么清高,那你来这干嘛来的!我有的是钱,你看我长得难看是吧,可老子的钱不难看!你闻闻,这钱多香啊!”说着将一叠钱就往她鼻子上推。
多多见状就要过来,却被袁正铭拉住且使了眼色,大家都不想得罪秦总,多多只好忍气看着事态的发展。
她捡起地上的一叠钱,站了起来,秦总的脸上露出了笑意,以为她是见了钱就答应了,刚笑着脸想伸手揽她的腰,却不妨被她抬手一叠钱迎面砸了过来。
遭到了羞辱的秦总黑着脸,没了个台阶下,手指着她,说:“你这小丫头片子有骨气,你不爱钱是不是?我告诉你,被我看中的女人还没有能逃脱的,你不要钱也不行!”
这话说的口气多像《红楼梦》里贾赦逼鸳鸯的那一段,她仍记得鸳鸯当时说的那句——“我这一辈子,别说是‘宝玉’,就是‘宝金’、‘宝天王’、‘宝玉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
她想到这里便觉得十分的好笑,扬起清淡笑容,说:“我管你是秦总还是禽兽,总之,别以为你有两个臭钱就玩弄女性,我告诉你,我阮曼君不是没见过有钱男人,我照样把他甩了,听见没?”说着她又打了一个酒嗝,坐在了沙发上,不去理会。
颈间的短发错综缠绕在面庞上,她随意地拂过发丝,她起身去拉多多,她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这简直就是在拿刀割她的自尊。
秦总拉住了她的胳膊,嬉皮笑脸流里流气的样子,说:“阮小姐,你生什么气啊,我多加点钱给你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