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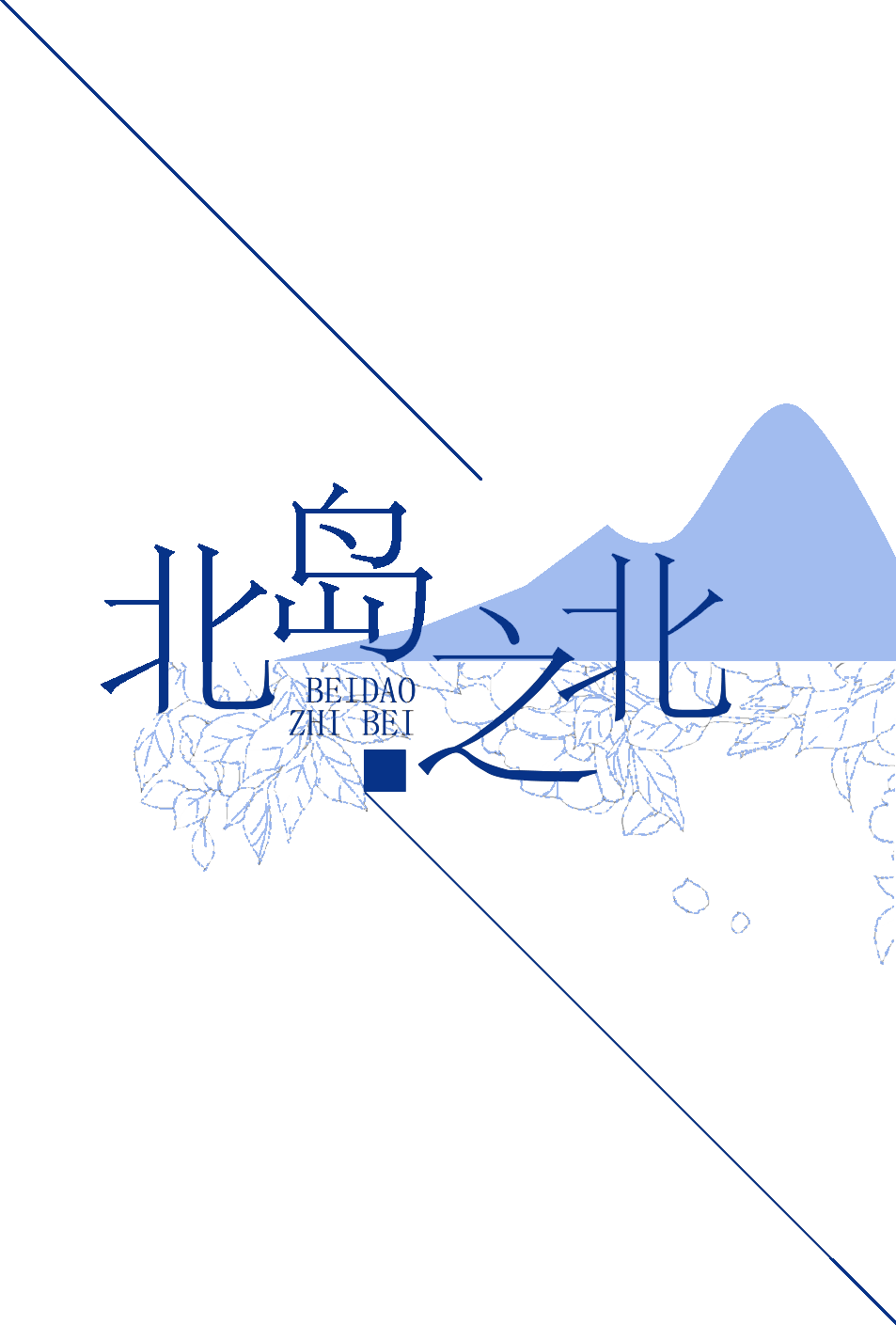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整体的一部分。
——约翰·多恩
曾经偶然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一个人必须是这世界上最坚固的岛屿,然后才能成为大陆的一部分”。
我曾把写这句话的作者当成我的偶像,然后把这句话写在了我的社交平台上。我每天提醒自己,不能认输,在我成为大陆的一部分之前。
但现实总是很残酷,当你作为一座小岛不断游向大陆,好不容易看见了大陆的海岸线时,却被一阵突袭而来的海浪淹没,以至前功尽弃。
我每天都在这样的噩梦中醒来。
医生说,这是病,得治。
我微笑着乖巧地点头,然后转过身就把那些药全都冲进了马桶。
看着它们全部消失在下水管里,我瞬间神清气爽。
我知道,我没病。
这件事被我那好事的“阿姨”看见,告诉了我老爸。就这样,她如愿以偿地将我踢到了我爷爷那里。
把我送到机场,她就潇洒地挥一挥手,然后就忙着和她的闺密约会去了。
我只能呵呵冷笑,我老爸那么听她的话,总有一天他得栽在这个只比我大五岁的“阿姨”手里。
不过,我也没闲工夫去管老爸的私事,我们一向井水不犯河水。他不会过问我的生活,我也不会去干涉他的感情,他只要负责给我生活费就行。不过这一次,他却假装负责起来,让我去爷爷那里好好养病。
其实就是嫌我待在家里太麻烦了吧,我还不知道他们?
不过正好,我可不想整天待在家里面对那张糟心的整容脸,也不知道我爸是什么眼光,就不能找个正常点的姑娘?虽说我是他女儿,但我一直无法理解他的审美。
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代沟。
在机场的卫生间里,我把老爸硬塞进我包里的药全都扔进了垃圾桶。我根本不需要,那些医生就会糊弄小孩儿,一会儿说我神经系统有问题,一会儿又说是压力太大。就连我爸最后都忍无可忍地说:“医生,我女儿怎么会有压力呢?我给她赚了一辈子都用不完的钱,她还有什么压力?”
然而这时,我只能和医生无奈对望。没错,需要看病的好像不是我,是我爸,一个除了赚钱,什么都不懂的老男人。
在医生尴尬的微笑中,我和我爸退出了诊疗室。
回家的路上,老爸心血来潮地提议说:“要不去你爷爷那里住上一阵子吧?那里空气好,景色也好,说不定住上几天你的病就好了。”
我自然是拒绝的,我就想天天待在家里,哪里也不去。谁还不知道我老爸那点心思,儿子刚出生就想把女儿一脚踢开,门儿都没有!
我爸知道我的脾气,如果我不说话,那就是没得谈,但是这一次他有些啰唆:“楹楹啊,你平常呢,从没让老爸担心过,老爸也从来不会勉强你做你不喜欢的事。可是这次你这个毛病已经持续好一阵子了,你阿姨说你又不肯配合医生吃药,你爷爷就你这么一个孙女,也是担心得不得了……”
“爸,你说错啦,新来的那位阿姨不是刚给爷爷新添了个孙子吗,怎么就我一个孙女呀?”我故意揶揄他。
我爸被我呛得只能求饶:“行行行,我的姑奶奶,算我怕了你了。我不说了,不说总行了吧?”但他最后还是不死心地搭上一句,“不过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
后来,因为我那刚出生的弟弟整天吵得不得了,我最终还是决定去爷爷那里避上一阵子。
爷爷生活在北岛,北岛顾名思义就是北方的一个小岛。网上说这个岛方圆不过四平方千米,常住人口不到一万,实在是够小的。但因为岛上有着绝美的海景和日落,每年去那里度假的人挺多,爷爷在那里经营的民宿,每到旺季都是爆满。
我曾去过两次,那里十分适合喜欢安静的人居住,但实在是太远了,坐两个小时的飞机后需要再坐两个小时的大巴,最后还要再坐一个多小时的轮船才能到岛上的码头。每去一次那个地方,我都像是经历了一次彻头彻尾的重生。
当我趴在轮船边上把胃里能吐的东西都吐完之后,坐在身边的大婶好心地给我递来了纸巾。对于陌生人,我一向抱有戒心,但这个时候也没气力计较那么多,只能一边擦着嘴一边说谢谢。
这位大婶儿见我稍微好了一点,于是开始找我说话。
“学生吧?有亲人在北岛这边?”
我无力地点头。
“你还在读书吗?在哪个学校啊?”
“在南方那边的学校……”话没说完,我又趴在船舷边上继续吐。
这位大婶全然不顾我狼狈的模样,继续自顾自地说:“南方来的啊,我正好有个姐姐的侄子的姐夫在那边。你是南方哪儿的人啊?”
能不能闭嘴让我好好吐啊?我突然很想骂人,但是我忍住了,因为胃酸不断上涌,让我连骂人的力气都没了。
好不容易挨到了下船的时刻,我整个人几近虚脱,无力地走下甲板。码头上的爷爷从人群中间一眼就看到了我,立刻跑上来扶住了我。
“楹楹,可受苦了吧?赶紧的,咱回家休息去。”
我和爷爷大概有两年没见了,但一点也没有生分。小时候父母闹离婚,爸爸忙着赚钱,我妈跟着一个外国人去了国外,爷爷就从北岛过来照顾我,直到我念完幼儿园。
可以说,我的童年没有父母的陪伴,只有爷爷的守护。也幸好还有爷爷,要不然我的人生真的是太凄凉了。
“楹楹啊,你爸给我打电话说你生了怪病,到底是啥怪病啊?还能不能治了?要不,爷爷带你去咱岛上有名的中医那儿瞧瞧,说不定还有一线转机呢。”
大概是我爸夸大其词,再加上我此刻看上去又真的虚弱,爷爷以为我得了什么绝症,一路上都紧皱着眉头。
“爷爷,你别听我爸瞎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你看我现在这样,是刚才晕船呢,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我无所谓地说。
“那到底是啥病啊?”爷爷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
想到他老人家年纪大了,经不起操心,我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就是写不了字。”
爷爷好像一时理解不了:“那怎么会啊?乖孙女,我看你家好多奖状的嘛,你不是成绩一直挺好的吗,咋会写不了字呢?”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能叹气说:“医生也不知道原因,我就更不知道了。反正,考试的时候,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大脑就这么‘唰’地一下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现在也写不了字,一拿起笔,就心慌。”
爷爷问:“你是不是压力太大啊?”
我摇摇头,说:“我爸说了,他给我赚了一辈子都用不完的钱,我没压力。”
爷爷冷哼一声,说:“你爸眼里就只有钱,别听他的。”然后又安慰我说,“不过不管啥原因,你现在别去想了,这次考试不行,还有下回嘛。”
“爷爷,重要的考试一年就这么一回,要想再考的话,得等一年。”我强调说。
“啊?这样啊?”爷爷被我弄得愣了一会儿,接着又乐观地说,“那就明年再考呗!考试对咱孙女来说不是小菜一碟吗?”
“爷爷,你这是在拍我马屁吗?”
“小孩子,别胡说,知道拍马屁是什么意思不?”
“对对对,不是拍马屁,是拍人屁。”我纠正。
“鬼灵精!”
我和爷爷这么一边说着一边往民宿的方向走,原本压抑的心突然轻松了不少,我顿时觉得自己做了一个英明的决定,来爷爷这里果然是来对了。
爷爷经营的民宿在北岛的半山腰,离码头不远。从一条宽敞的直路向上,步行不过一刻钟。因为视野极好,拉开窗帘就能看到壮阔的大海,又加上价格亲民,常常提前半年就有人预订民宿了。
“住在这里,果然是一种享受!”我躺在院子里的沙滩椅上,迎着海风,舒展开四肢。
一眼望去,无边无际的大海与天空湛蓝无比,我心里的烦闷瞬间消失得干干净净。
“真舒服啊!”我享受着日光浴,昏昏欲睡。
正当我沉浸在美景之中兀自陶醉的时候,突然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咔嚓”的声音,吓得我一屁股从沙滩椅上坐了起来。
环顾四周,我一抬头,就发现二楼的阳台边站着一个神情紧张的男生,手里拿着一台单反相机。他可能忘了关掉声音,被我发觉后,正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我。
居然偷拍本姑娘!
老实说,从小到大我不是没有碰见过色狼,但我还是第一次碰见这么笨拙的色狼!我指着他,做了一个口形:“你,给我等着!”
然后我提起地上的拖鞋,冲进客厅,直奔二楼准备找这个看上去好欺负的色狼算账。
当我跑上二楼的时候,那色狼已经站在了走廊上,双手合十,一脸歉意地说:“对不起啊,我看你睡在那里,觉得很好看,就忍不住拍了一张,你不会介意吧?”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厚脸皮的人!
我伸出手,不客气地说:“我当然介意,把相机交出来。”
他赶紧护住相机,像护住宝贝似的说:“不行,这个东西不能给你,不能!”
“你不交,我可要报警了啊!”我冷笑了一下,从裤兜里摸出手机,假装要报警。
他明显慌了神,把相机迅速挂在身上,然后伸手过来抢我的手机。尽管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护住手机,无奈他身高占了太大的优势,最后手机还是被他抢了过去。
“你冷静一点,我不是坏人!”他连忙为自己的行为开脱。
鬼才会信啊!
没了手机的我,气得差点吐血,拿起手里的拖鞋,“啪”的一声,使劲扇在了他的脸上。
只见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左脸微红,还印上了灰色的鞋印,神情有说不尽的委屈。
装,你继续装!我叉腰怒瞪他,看他还要耍什么花样!
他撇着嘴巴,极尽委屈。忽然,他望向我的身后,像遇见救星一般开口喊道:“哎呀!老宋,你快来帮我跟这位美女解释解释!我真的不是坏人!”
我疑惑地扭头,这才注意到身后不知何时站了个男人。
他看上去二十四五岁,年纪轻轻的,却一副毫无生气的样子。不过,穿着倒是很讲究,头发也明显经过了精心的修剪,看上去有些帅气,但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奇怪感。
我忽然注意到他的眼睛,像有一层纱覆在上面,暗淡无光。常有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扇紧闭着的窗户,不让任何细微的光亮透进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对这个男人有些在意,可能是因为他实在是太奇怪了。怎么说呢?我自诩异类,算是从小就看破红尘的那类人,可是这个人,比我还奇怪。
我盯着他愣了几秒钟,但他显然无意加入我们的战争,把冰冷无神的目光从我和色狼的身上移开,转身就上了楼。
色狼彻底绝望了,伸出手臂喊道:“老宋,你别走啊!”
这个色狼喊他老宋,看起来是熟人,但是那个冷漠脸似乎并没有想要理睬色狼的样子。看着色狼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我竟莫名觉得他有点可爱。
外出买菜的爷爷正好回来,大概是听到我们的动静,急急忙忙地跑了上来。
“蒋嘉逸,你大白天的在喊什么啊!”
蒋嘉逸看到爷爷,又像是看到了救星,上前抱住爷爷的双臂,躲在爷爷身侧说:“爷爷,你总算是回来了,你快帮我向这位美女解释一下,我真的不是坏人。”
爷爷瞟了一眼蒋嘉逸挂在身上的相机,瞬间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拳头“咚”的一声落在了他的额头上。
蒋嘉逸吃痛,大喊:“爷爷,你干吗打我!”
爷爷开始骂:“我说你这臭小子,平常拍拍其他人也就算了,现在居然把主意打到我孙女头上?你这个臭小子,把相机给我!”
蒋嘉逸拼命护住自己的相机,然后把手机塞进我爷爷的手里,转身跑开了。爷爷依然不死心地对着蒋嘉逸的背影喊:“臭小子!赶紧把照片给我删了!”
被爷爷这么一闹,我大概猜到是熟人了,不禁放下心来。
“那家伙是什么人?”
爷爷说:“怪人一个,别理他。明天看见他,看我怎么收拾他,臭小子!”然后他把手机还给我,挽着衣袖,怒气冲冲地下楼了。
嗯,看起来,爷爷比我还生气。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有点开心。大概是很久没有享受过被人关心的滋味了吧?对于被偷拍这件事,我反而不在意了。
晚饭的时候,爷爷从碗柜里拿出了三副碗筷。我以为爷爷记性不好,正打算把多出的碗筷放回去,爷爷连忙叫住了我。
“哎,放着放着。”
“干吗啊爷爷,住在民宿的人要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吗?”我隐隐有点不爽,我可不希望自家餐桌上多几个陌生人,那样吃饭可不自在。
“没有啊,我们这里一直都不供应午餐和晚餐的嘛。”爷爷把热乎乎的汤端上了桌。
“那你拿这么多碗筷干吗?就我们两个人。”
“宋先生比较特殊,你快去帮我叫一下他,他就住在阁楼。”爷爷催促我。
“宋先生?谁啊?”我不死心地一问到底。
“就是住在我们这里的租客啊,他叫宋曦阳,每年都会在我们民宿住上一段时间,算是老熟人了。”爷爷推了我一把,扬了扬下巴,“见了人家有礼貌点啊。”
虽然不情愿,但我还是上了楼,途中想起今天在转角处见到的那个奇怪男子好像也姓宋,应该就是他吧。
我狐疑地来到阁楼,敲响了房门,对方倒是很快就开了门,只是冷冰冰的一张脸莫名让人不舒服。
果然就是那个奇怪的男人。
姓宋的用一种不带情绪、仿佛凝滞的目光直直地看着我。我被盯得有些莫名其妙,一时间竟然忘记了要说什么。
最终,他疑惑地皱起了眉头,我赫然回神,摸着后脑勺说:“啊,那个……爷爷叫你下去吃饭了。”
他面无表情地说:“好。”
然后,他便又将门关上了,“砰”的一声,吓了我一跳。
真是气人啊,爷爷让我有礼貌点,可是没有礼貌的分明是这个男人啊!我对着房门冷哼一声,憋住怒气下了楼。
回到一楼的饭厅,爷爷见只有我一个人,就问:“宋先生呢?”
“不知道。”我没好气地回答,拿着碗筷正想开动。爷爷制止我:“楹楹,等等人家宋先生,别没礼貌。”
“哼,谁没礼貌还不一定呢。”我用筷子戳着碗里的饭,不满地嘀咕。见爷爷如此在意这位宋先生,我八卦地问;“爷爷,为什么他如此特殊?这位宋先生该不会是你的大客户吧?给了你双倍的钱?”
“小孩子,就知道胡说。”爷爷无奈一笑,“不是你想的那样,宋先生……”
爷爷正想说什么的时候,那位奇怪的宋先生从楼上走了下来。
他换了件干净的白衬衫,勾勒出了他结实健美的身材。
不知为何,我的脸颊微微发烫。我看向爷爷,爷爷对我使了个眼色,让我乖乖的别乱说话。
为了不说错话,我只好埋头苦吃,面前的菜几乎被我一扫而光。旁边的爷爷问宋先生明天要不要吃螃蟹,最近的螃蟹又大又新鲜,他只是轻轻应了声,算是晚饭时间里唯一的交流。
等晚饭结束,确认宋先生上楼之后,凝滞的空气终于开始流通了。我深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瘫在椅子上拍拍胸脯对爷爷说:“真是要憋死我了。”
爷爷说:“你习惯就好了,宋先生其实很好相处的。”
这叫好相处?我满脑子疑问。
“爷爷,你对于好相处的定义太低了吧?要我跟这样的人一直生活在一起,简直生不如死。”
爷爷叹气:“乖孙女,你收敛收敛你的嘴。以后在宋先生面前,千万别说这些话。”
“行行行,在他面前,我会把嘴巴闭好的。”
不过,也要看我的心情。我偷偷在心里说道。
“对了,爷爷,他要住到什么时候啊?”我可不想接下来的整个假期都有这个怪人存在。
“不知道。”爷爷一边回答,一边收拾碗筷。
我挪动自己此刻像僵尸一样的身体,努力站在了洗碗台前帮爷爷洗碗,不死心地问:“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他已经提前交了两个月的租金。”
“什么?”我把手里的洗碗布一扔,哭丧着脸问,“也就是说,他这两个月都不打算走了?”
“哎呀,楹楹,宋先生不是什么怪人,他可是小有名气的建筑师,厉害着呢。你咋那么不喜欢他呢?”
爷爷很少夸赞人,此刻竟然对那个宋先生这么赞不绝口,真是不爽!而且爷爷完全没有察觉到我此刻的情绪,自顾自地说:“等你们熟悉了你就知道了。他每年都来我们这儿,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我总不能赶人家走吧?你啊,就当是给爷爷个面子,好好跟人家相处,行不行?楹楹啊,这次你就听爷爷的吧,你平常呢,当他不存在就好了。”
爷爷的话都已经说到了这个份儿上,要是我再不答应,就显得有些过分了。
“好吧。”我勉为其难地同意了。
爷爷乐呵呵地说:“楹楹懂事了,明天去菜市场给你买你最爱吃的龙虾。”
“行,我要最贵的那一种。”我嘟着嘴说。
“没问题!你想吃啥爷爷都满足你!”
爷爷对我的有求必应让我觉得开心,仿佛在这里我才找到了家的感觉。即便宋先生让我不快,但为了爷爷,这些都是可以忽视的小事。
其实直到现在,我都很少会回忆小时候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的事对我来说多半是不快乐的。
印象最深的是,每当幼儿园放学,别的同学都有妈妈或者爸爸等在幼儿园门口,但来接我的永远是我家的保姆。渐渐地,幼儿园里就开始流传我没有父母的谣言。我很想证明我其实是有父母的,所以向老爸哀求了很多次让他来接我,哪怕一次也好,然而到我幼儿园毕业,他也没有出现过。
到了小学,因为大家都说我是不幸的孩子,所以很少有人愿意跟我在一起。整整六年的小学时光,我几乎都在独来独往中度过,后来,孤独也就成了一种习惯。我从来不会乞求别人跟我待在一起,我宁愿维护这小小的自尊。
至于中学,女生之间的孤立就更加严重了,因此我反倒喜欢和男生玩在一起,尽管学校里到处都是流言蜚语,但是我并不介意。我的原则一向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羡慕嫉妒恨吧!
但我一直想要证明自己,并且因此想了一个最笨的方式:考试。
所以,我的成绩一向不错,也曾被老师寄予厚望。但就在关键时刻,我却出现了无法写字的情况。医生没办法解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都这样,本就无章可循,就好比我原本是有父母的,却如同没有。抱怨也没用,我只能自认倒霉。
但是有些人的人生恰好相反,从小就在父母的疼爱下长大,然后享受最好的教育,考上最好的大学,成就最好的人生。大概,宋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我窝在沙发里,偷瞟了一眼坐在天台边望着远处发呆的宋先生,他骨节分明的手拎着啤酒罐,入神地看着星空下的海面。
多亏了阳台昏暗的灯光,让他不会注意到天台上还有我这一号人物。也不知道倒了什么霉,本就是为了避开他刻意等到晚上才到天台上来吹吹风,没想到他居然也在。本来想打道回府,但又心有不甘,凭什么我要走啊?这个天台又不是属于他的。就像赌气似的,我决定坚守阵地,绝不离开。
仔细想想,我和宋先生也没什么矛盾,但是他这个人实在是太难懂。我不太喜欢去猜测别人的心思,他又让人完全看不透他心里所想,跟这类人相处实在是太累。所以,对于这种人,我一向采取能避则避的策略。
就在我愣神的时候,宋先生忽然朝我的方向看了过来。他狐疑地偏了一下头,似乎在确认着什么。可能是天台上的灯光昏暗,他看不清楚我的脸。过了片刻,他忽地转身,意外地朝着我走了过来。
我吓了一跳,手里的书“砰”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他默默地弯腰帮我捡起掉落的书本,并未急着还给我。见我不是很想理会他,他就自顾自地在我身边坐下,摇了摇手里的啤酒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试着喝点啤酒。”
“我没觉得心情不好啊。”我从他手里抢回书,朗声说,“要是你不在的话,就更好了。”
对于我的“不怀好意”,他并没有反驳,只是轻笑一声,又仰头喝了一口酒。
“别总喝酒,月黑风高,孤男寡女,你喝醉了万一对我有非分之想怎么办?”我调侃地说。
他喝酒的动作一顿,目光落在我身上,探究似的问:“你似乎很不喜欢我?”
“哪里敢。”我笑眯眯地看着他,有些不怀好意。
“小孩子,你全身上下都散发着不友好。”宋先生摇了摇头,说。
“彼此彼此,你也并没对我多友好。”我耸耸肩。
宋先生愣了片刻,被我的牙尖嘴利弄得摇头。
然后,天台又是一阵沉默。
我觉得有些尴尬,于是找话题,问:“那个……宋什么阳来着?”
“宋曦阳。”
“宋夕阳?你怎么不送朝阳呢。”我觉得这个名字有意思,忍不住拿他开涮。
宋先生纠正:“‘曦’就是晨光的意思。”
“你一点都没有晨光该有的活力。”我白了他一眼。
宋曦阳笑笑,说:“你倒是有一副学生的样子,只可惜考试没考好,真是给你的活力人生抹了一滴墨点啊。”
“喂!你嘲笑我!”我气得站起来,但转念一想,宋曦阳是如何知道我考试没考好的?难不成是爷爷多嘴,在他面前说起了?
宋曦阳自顾自地说:“有些事情有果就有因,找到事情的原因,那么结果也是可以扭转的。”
“宋先生,你太爱管闲事了吧?”我直直地瞪着宋曦阳。
宋曦阳不以为然地说:“不是我爱管闲事,是你爷爷心疼你。”
“所以找你来当说客?”我问。
“不算,毕竟说或不说是我的事,听或不听是你的事。”宋曦阳淡淡地笑道,又饮了一口酒。
他说话文绉绉的,令我一点都不舒服。我重新坐下,抱着自己的膝盖,思忖着他的话。
其实爷爷还是挺懂我的,他知道我叛逆,家人说的话一点也听不进去。他知道我的性格,不爱服输,即使与人理论也要分个输赢。于是,他就找了宋曦阳来劝说,理论着理论着,宋曦阳该说的话也都说完了。
这样一想,我觉得宋曦阳真是一株奇葩。明明之前冷冷淡淡的,仿佛世间一切都与他无关,但让我没想到是,他竟然还有这么“好事”的一面。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如果说宋曦阳是一种奇葩,那么蒋嘉逸算得上是另一种奇葩了。
自从第一天把他当成色狼之后,我就常常在民宿里碰见他,以及不同的美女。他嘴上说,这些美女都是他找来的模特,但谁知道他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
不过要说他是色狼,算是我一开始看走眼了,后来才发现,这位大少爷不但不缺女朋友,更不缺钱。除了那台价格不菲的相机,他全身上下全是名牌,手腕上的那块表也是好几万的价位。如果不是家里有钱,一般的学生哪有这样的装备?更夸张的是,他在离岛之前包了一艘游艇,把他在岛上交到的一众好友都邀请到游艇上彻夜狂欢。
当然,也叫了我,我自是予以了回绝。
我并不是特别讨厌蒋嘉逸这样的直肠子,只是每次见面他都表露出过于浮夸的热情,让人难以招架。何况,我讨厌闹哄哄的地方。
在民宿的天台上,我又一次见到了宋曦阳。原以为他是蒋嘉逸的熟人,自然也参加派对去了,但是没有想到他依旧孤零零地坐在天台最前面的椅子上看着涨潮的海水发呆。
平常在天台碰见他时,他也常望着同一个方向,然而目光的那一端除了一望无垠的海水以外什么都没有,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
我对他的人生没什么兴趣,正想找个角落听音乐看书,他冷不丁地来了一句:“你怎么没去嘉逸组织的聚会?我看你们平常挺熟的。”
他并没有在看我,而是盯着远方,所以我迟疑了许久,才确定他在跟我说话。
“你不也没去吗?”我撇撇嘴。
“那不都是小孩子喜欢玩的吗?我还以为你会喜欢。”他又摆出一副大人的嘴脸,实在招人烦。
“说得好像你很老似的,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我鄙夷地说。
“看来你不太喜欢被别人当成小孩。”
他倒是说对了,我最讨厌别人把我当成什么都不懂的人,谁说年龄就代表了一切?
“别说得好像很了解我似的。”
我正要戴上耳机,屏蔽掉他时,忽又听他自言自语般问道:“你听说过归冢岛吗?”
归冢岛?
我听爷爷说过,那是位于北岛以北的一个小岛,据说每年的五月和六月岛上会开满鲜花,形成大片的花海。然而路途遥远,又很难预知花期,所以很少有人会去。
宋曦阳怎么会问起归冢岛?
“你对那个岛很有兴趣?”我在他身后的椅子上坐下,他依旧背对着我,看着大海的方向。
“曾经和一个人有过约定,想要去看岛上的花海,但是可惜今年又错过了花期。”他喃喃地说。
“但我听说那个岛很远,要坐大半天的船,很少有船会专门过去。而且海上的风浪很大,你就不怕回不来啊?”我随口吓唬他。
他忽然沉默了下去。过了许久,我才意识到,刚才我的话或许触碰到了某种禁忌。我莫名有些担忧起来,望着他在夕阳余晖下更显孤寂的背影,不知道该怎么打破这种不自在的寂静。
海浪的声音在一阵一阵咆哮,天台上却安静得可怕。
“喂,你怎么了?”我试探着问。
这是我第一次开始反思自己的口无遮拦。爷爷总说我说话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这样不好,我总是不以为意。但看到宋曦阳这个样子,我着实有些害怕。
“喂,你干吗不说话啊?”我站起身来,快步走到他的身后,拉着他的胳膊,皱眉问,“我不会触及到了你的伤心事吧?你别一难过要跳海啊。”
他恍然回神,扭头看着我,眼中忽然升起笑意:“跳海?”
看到他的样子,我才确认他没事,于是松开手拍拍胸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
“以为我如何?”他微微翘起嘴角,问。
“没什么。”我摆摆手,松了一口气,跟他站在一起。
“你刚刚问我怕不怕回不来。”宋曦阳提到刚刚的问题,转而又望向大海,说,“我曾经去过那个岛,就在去年的时候。当时天气不太好,没有游船愿意过去。后来我找到了一艘要去外海捕鱼的船,他们愿意顺带载我,但是我只有半个小时的停留时间,而且要跟着他们在海上待好几天。人说来很奇怪,在岸上时,对深不见底的大海总是心存畏惧,然而当真正历经波涛汹涌的黑夜后,却反而什么也不怕了。”
他娓娓道来的话语像是在讲述一个漫长的故事。我不敢再胡言乱语,于是问:“那你最后到了那座岛吗?”
“到了。”他意味深长地说,“我到了那座岛,花期也过了。”
我心里有些遗憾,不为自己,而是为宋曦阳感到遗憾,为那场已过的花期感到遗憾。
“你问我二十多年来有没有经历让我过不去的坎坷,这就是。”宋曦阳回眸望着我,说,“但我自己也知道,过不去的坎坷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它不会妨碍我的正常生活。正是因为有这样过不去的坎坷,我才得以有牵挂和想念的东西,才得以有要为之努力的东西吧。”
我轻轻咬着嘴唇,这一刻我才发现我的确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儿。比起宋曦阳,我什么也算不上。
那次交谈是我们在北岛最后的一次交谈。第二天,宋曦阳比蒋嘉逸先一步离开了北岛。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宋曦阳的那些话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影子,但很奇怪的是,自那以后我很少会再做被海水淹没的噩梦。反而,我会时常想起宋曦阳所说的那座归冢岛。
我在网上搜了那座小岛的照片,数量寥寥,的确很少有人踏足那个地方。我只在一个喜欢到处闯荡的驴友那里见过归冢岛花海的照片,漫山遍野,粉色花开,映衬着湛蓝色的海水,美得不太真实。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心里也有了一个梦,关于归冢岛,关于繁花盛开。
关于宋曦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