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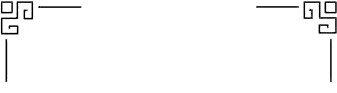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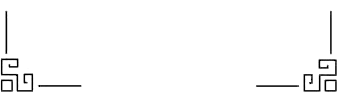
阿谁拉着玉团儿的手,抱着凤凤慢慢的退到一边。有几个中原剑会的剑手护卫她们的安全,玉团儿在人群里东张西望,只盼见到柳眼,阿谁紧紧的抱着凤凤,站着一动不动。
这个地方聚集着几百人……每个人都对柳眼势在必得。她笔直的望着前方,眼前有许多人在摇晃,她什么也没看在眼里,只记得那个时候……那天,他那种哀伤的眼神。
凤凤的头靠在她的肩上睡着了,她只有在感觉到凤凤的温暖的时候,才会有安全感,才能相信自己能正常的继续往前生活。她为自己设定的将来之中,没有其他男人,只有凤凤,所以无论柳眼以多么哀伤的眼神看着她,她也不会有所改变。
但他……真的很可怜……她私心期盼他不要来,藏匿在这世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好,就是今天不要出现。玉团儿拉拉她的手,悄声道,“这些人都在骂他。”阿谁点了点头,“他做了很多错事,伤害了很多人。”玉团儿低声问,“他们都中了他的毒吗?”阿谁叹了口气,“嗯,很多人都中了他的毒,谁能抓到他,谁就能控制这许许多多人,大家都想要解药。”玉团儿低声道,“他没有解药的。”阿谁微微一怔,“你怎么知道?”玉团儿哼了一声,“我都帮他洗过澡啦!他全身上下什么也没有,哪有什么解药。”阿谁微微一笑,“你对他真好。”玉团儿笑了起来,“那当然了,因为他对我也很好啊。”她指着自己的脸,“他治好了我的脸,救了我的命。”阿谁摸了摸她的脸,轻声道,“他真的对你很好很好。”玉团儿连连点头,浑身都洋溢着快乐幸福。
如果她不够坚强,是不是会在这样的笑容下崩溃,变得支离破碎?阿谁有些恍惚,人们总是对无知善良的东西宽容、喜爱……而对像她这样只会忍耐的女人,是不是就习惯吹毛求疵,习惯了想要挑衅她忍耐的极限,想要看她崩溃的样子……然后引以为乐,然后证明其实她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揭穿了以后不过同样是一堆不堪入目的东西?人与人是不能比较的,她很早就知道,但有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很……很难以接受……难以接受她是个连玉团儿都远远不如的女人。
她一直很努力的在生活……努力的不想让自己显得很难堪,努力的想拥有自己的生活,不依赖任何人。但谁也不曾看得起她,他们会爱护宠溺比她更脆弱更无知的东西,但不知道怎样善待她、也从未打算善待她。
他们都指望着她对他们好,并且会因为她做得不够体贴不够热情甚至不够真心实意而受到伤害,郝文侯、柳眼、唐俪辞都是如此,但……但……世界的规则本不该是这样,她深深明白这都是错的荒谬的,但现实就是如此。
她无依无靠,唯一能自持的,是自己尚能忍耐。
“阿谁姐姐?”玉团儿见她默默望着远方,“怎么了?”阿谁摇了摇头,微微一笑,“没什么。”
丽人居的二楼安静的异常,仿佛林逋被劫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董狐笔和文秀师太商议了一下,将来到丽人居前的二十六个门派,六百三十九人分成二十个小队,既监视风流店众人的动静,又观察是否有人接近。
然而日过正午、又过黄昏,丽人居的厨房接连不断的往二楼上菜,却是谁也没有来。
柳眼和雪线子藏匿在山谷的密林之中,到处有土狗游荡,两人虽然不惧土狗,但被发现了也很麻烦。雪线子给柳眼洒了一身花粉,他向来好色爱花,怀里藏着不少奇花异卉的花粉用以向美人讨好,今日却用在柳眼身上。那花粉气味并不浓,散发着清奇的幽香,雪线子希望这奇花的香气能掩饰柳眼身上的味道,扰乱那些土狗的嗅觉,但究竟扰乱了没有谁也不知道。两人看方平斋离去,山下妖魂死士尚未归队,仍是混乱,雪线子灵机一动,下去抓了两人上来,点了穴道扒下衣服,将两条赤条条的男人埋在山上杂草堆里,自己和柳眼穿了妖魂死士的黑衣,戴上他们的人皮面具,大摇大摆的走下山去。
走进敌人的大本营,雪线子扶着柳眼,被方平斋所伤的人不少,眼见柳眼一瘸一拐,旁人也不觉奇怪。两人寻了个没有烧掉的帐篷钻了进去,里面躺着五人,一照面尚未问话已被雪线子放倒在地上,两人拿起桌上的酒菜便大嚼,吃了个饱,略略休息了一下。吃过饭后,雪线子又大摇大摆的出去探听消息,回来说林逋已经被救,究竟是何人所救并不清楚,但已经不在丽人居的楼头。柳眼听后静默了一阵,“那些中毒的人都还在?”
“门派里有人中毒的都在丽人居等着,风流店丢了林逋,但也没有撤走,我看大家都等着你这尾大鱼,反正林逋也已经被救走,你不如拍拍屁股溜之大吉,大不了我替你悄悄通知你的徒弟儿,叫他天涯海角找你去。”雪线子一摇头,“你现在出现,没有半点好处。”柳眼缓缓的道,“我若不出现,大家要么以为我死了,要么以为我躲了起来,永远不会再出现——那江湖上如此多中毒之人都不得不屈从于风流店,因为只有风流店有猩鬼九心丸,可以延续性命、增强功力。风流店非要抓我不可,一是他们自己很也想要所谓解药;二是他们怕我当真有所谓解药。所以如果我不出现,江湖大局将倾向风流店,等候在丽人居外的那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将不得不做一些违背良心的选择。那都是我造的孽……”雪线子扑的一声差点把刚喝下去的汤喷了出来,“江湖传说,风流客柳眼是个阴险狠毒,又淫又恶的魔头,是小唐的死对头。我看你做人还不错嘛!而且你和小唐分明是过命交情的朋友,为了你小唐连我老人家都敢拖下水,可见江湖传言真不可尽信,唉!”柳眼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道,“我要出去,告诉他们猩鬼九心丸有解药,我还没死,叫大家不必听风流店的威胁。”雪线子连连摇头,“你的想法很好很伟大,可惜你如果出去,两个雪线子都未必保得了你的命,一个没有命的柳眼有什么用?难道你的尸体能变成解药解去猩鬼九心丸之毒吗?就算能,一个人百来斤连头发都算下去也不够这许多人吃,就是死了别人都会说你偏心。”
“解药没有做出来,谁也不敢要我的命。”柳眼沉声道。雪线子哈哈一笑,“那要看你有没有能够抗衡两方的力量,只有我一个人,远远不够。风流店要拿你下油锅,江湖白道要抓你去凌迟,除非你找到神仙当靠山,否则你做出解药一样要死,而你做出的解药一样沦为别人登上江湖帝位的筹码。”柳眼眼珠子微微一动,“神仙?”雪线子颔首,“神仙,玉皇大帝、太上老君、二郎神之类……”柳眼低声道,“那唐俪辞呢?”雪线子重重的敲了下他的头,“你是想害死小唐吗?谁也不知你和小唐有什么过去的交情,他没有任何理由给你撑腰。他要是站出来给你撑腰,别人都会以为他为的不是你柳眼,而是江湖帝位,所有反对小唐的人立刻找到借口,证实他居心叵测,小唐立刻落到人人喊打的地步。”柳眼默然,凡遇到棘手的事,他习惯的以为阿俪什么都能解决,纵然是明知无法做到的事也都抱着幻想,但显然是他错了。过了一会儿,他慢慢的道,“我写一封信,你帮我带去丽人居那里,交给成缊袍。”雪线子眉开眼笑,“哎呀,妙法妙法,快写快写。”
柳眼自雪线子换下的白衣上撕了一块白布下来,在帐篷里找到笔墨,写了几行字在白布上,递给雪线子。雪线子一看,只见白布上写着“奇毒有解,神逸流香,修仙之路,其道堂堂。半年后药成之日,绝凌顶雪鹰居会客,以招换药。”那上面还有一行弯弯曲曲,犹如花草一样的符号,不知写的什么,奇道,“这是什么?”柳眼吁了口气,淡淡的道,“这是写给俪辞的留言,说一点私事。”雪线子摇了摇头,“前面这段写得不错,很有枭雄的气魄,大家要是信了,这半年在家中勤练武功,江湖可就太平了。可惜——我要怎么证明这是风流客柳眼亲手所写的书信?你有什么信物没有?”
柳眼一怔,他可怖的脸上起了一阵细微的变化,似是心情一阵激荡,缓缓探手入怀,取出一样东西,“这个……”雪线子见他摸出一样软乎乎的东西,“什么?”柳眼双手缓缓打开那样东西,雪线子赫然看到一张既诡异、又阴郁俊美的脸。饶是他游戏江湖多年也被吓出一身冷汗,“人皮?你的……脸……”柳眼笑了笑,“嗯,我的脸。”雪线子抓起那张人皮,“好,我这就去了,你在这里等我,不见人莫出去。”柳眼平静的道,“若是见到我徒弟,告诉他我在这里等他。”雪线子颔首,一笑而去。
柳眼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黑色帐篷里,过往所发生的一切支离破碎的在眼前上演。他想起很久以前,他在风情酒吧里弹着吉他,唱着不知名的歌,人人都说眼哥是个温柔的人,对大家都好,做事很细心,这样的男人真少见。那时候他以半个保镖的身份住在唐家,白天大部分时间和阿俪在一起,晚上他就去酒吧驻唱,阿俪所拥有的一切,近乎也就是他的一切。那时不曾怀疑过什么,他全部的精力都用来设想如何完美的处理阿俪所惹的种种麻烦,如何尽量表现得优雅、从容、镇定而自信,不丢唐家的脸,他一直像个最好的管家和保镖,只要阿俪拥有了什么,他也就像自己拥有了一样高兴。
是什么时候……一切变得面目全非,他再也找不回当初自己那张温柔的脸?再也没有宽容任何人的胸怀?从他对阿俪失望的那天开始,在他还没有理解的时候,他的世界已经崩溃。而如今……他的崩溃的世界究竟是回来了没有?其实他也根本没有理解。
他从来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从来只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缺乏目的的概念,往往做一件事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只知道有人希望他这样做,于是他就做了。
这样性格的人很差劲是不是?他茫然看着空旷的帐篷,思绪有很长时间的空白。
帐篷外黑衣的死士已回归秩序,列队站好,山谷中的黑烟已经散尽,虽然伏兵已经暴露,林逋意外被救,但鬼牡丹并未放弃计划,众死士仍旧列队待命。
雪线子揣着柳眼写字的白布,一溜烟往丽人居而去,他的身形飘逸,穿的又是死士的衣裳,妖魂死士无一察觉,然而堪堪及丽人居后山坡之下,一道人影持剑驻地,仿佛已经在那里站了很久了。
那是余泣凤的背影,雪线子叹了口气,开始后悔为什么没有绕路?就在刹那之间,身后两人缓步走近,“雪郎,柳大尊主呢?”其中一人格格娇笑,“你把他藏到哪里去了?雪线子转过身来,三人将他团团围住,一人是余泣凤,一人是红蝉娘子,一人全身黑衣,衣上绣满了颜色鲜艳形状古怪的牡丹花。
雪线子的目光自那三人脸上一一掠过,余泣凤拔起长剑,红蝉娘子手握蓝色弯刀,浑身黑衣的人不知是谁,但显然不是什么轻易应付得了的角色。就在余泣凤剑招将出的时候,雪线子叹了口气,“且慢,我输了。”余泣凤一怔,三人都颇出意料之外,雪线子在身上拍了拍,“余剑王、小红蝉儿、还有这位虽然未曾谋面但一定不同寻常的花衣兄,与其大战一场连累自己伤痕累累依然是输,不如现在认输比较潇洒。”
黑衣的鬼牡丹盯了他一眼,突然仰天大笑,“哈哈哈,雪线子不亏当世英豪,请!”他抬手指路,“以你的气魄,足以当我座上宾客,这边请。”余泣凤咽喉上的洞咕噜一声,似乎满腹不快,但并不说话。倒是红蝉娘子笑盈盈的迎上来,伸手点了雪线子几处穴道,“雪郎受委屈了,跟我来。”
雪线子怀里揣着柳眼的书信和人皮,此时束手就擒,怀里的东西必定会被搜走,他心念急转,想出十七八个念头都是无用,索性探手入怀,把柳眼的书信和人皮一起取出,交了出去。“这是柳大尊主留给江湖的书信,方才他已被方平斋带走,只留下这封信要我到丽人居交付成缊袍。我和柳大尊主也没天大的交情,相助他不过是为了一万两黄金的银票,诺,我现在口袋空空,连银票都索性送你,可见我老人家没有骗你吧。”
红蝉娘子吃吃的笑,摸了摸雪线子的脸颊,“雪郎你素来没有良心,为了钱做这种事我是信的,就是不知道鬼主信不信了。”雪线子干笑一声,“我老人家难得插手江湖中事,这次真是阴沟里翻得不浅,老脸丢了一大把,可见人真不能爱钱,一爱钱就会栽。”红蝉娘子捏着他那如冠玉一般的脸,娇柔的笑,“哎呀!要说你老,真没人能信,雪郎你究竟几岁了?”雪线子哈哈一笑,“老夫七十有八了。”红蝉娘子眉开眼笑,腻声道,“妾身六十有六了,与你正好般配。”
黄昏。
众人仍然聚集在丽人居外,柳眼始终没有来,被分派成组戒备查探的众人开始松懈,即便是文秀师太、大成禅师这样德高望重的前辈也有些沉不住气,谁也不知道柳眼是否当真会出现?而即使他出现了,是否又携带了解药?柳眼是否仍然活着?他若死了,若是有解药,解药是否被他人所夺?若是没有解药,风流店持猩鬼九心丸相挟,各派掌门为了派中弟子是断然拒绝、或是勉强相就?有些人开始盘算退走,然而堪堪退到数百尺外,便见树林之中黑影憧憧,潜伏着不少风流店的人马,并且自己是一日未曾进食休息,对方却是休息已久,精力充沛,此时虽然尚未发难,却已让人不寒而栗。
天色一分一分变暗,众人的精力在一分一分消耗,包围的人马越来越多,而柳眼依然不知所踪。事到如今,连一派悠闲的天寻子、鸿门剑等人都有些轻微的焦躁起来,受骗而来,落入重围,该如何是好?
沉暗的天色突地一亮,随即轰隆一声,众人抬头相望,天空大雨倾盆而下,竟是触肤生痛,视物不清。
成缊袍招呼众人圈子往内收回,然而人心涣散,众人的脚步虽是退后,却是参差不齐。林中有拔箭之声,无数黑黝黝的箭尖在雨中指向退到一处的众人。文秀师太、董狐笔等人所领的人马虽然众多,但一无庇护,暴露在大雨和箭矢之中,一旦弓弦响动,死伤必定惨重。刹那间武功较高的成缊袍、天寻子、鸿门剑、文秀师太、大成禅师等纷纷抢到外围,准备接箭。
但树林里并不发箭,包围圈很紧实,大雨模糊了众人的视线,看不清究竟有多少人,丽人居二楼的灯光在风雨中显得昏黄朦胧,摇曳不已。众人全身湿透,均感寒冷异常,南方的冬天,雨水虽不结冰,却是冻入骨髓。董狐笔首先沉不足气,怪叫一声,“大伙一起冲出去算了,他妈的天寒地冻,不冷死也——”他一句话尚未说完,丽人居中突地传出麻辣毛肚那诱人已极妙不可言的香气,“哇”的低呼声起,不少年纪尚轻的门人馋涎欲滴,蠢蠢欲动,耳听董狐笔叫道“冲出去”,有几人拔起刀剑,往外冲去。
“且慢!”成缊袍冷声喝道,与文秀师太一起将那几人拉了回来,“冷静!沉住气!此时动手太过不利。大家在圈子中间掘土,挖一个大坑,众人躲在里面,把泥土推到外面来堆高挡箭!”他一声喝令,倒也起了作用,脚步迈出去的几人又缩了回来,武功较高的人外围挡箭,武功较弱的人奋力据土,很快地上便被众人挖出一个大洞,外头乱箭若射来,躲在洞内已可大大减少死伤。文秀师太、天寻子、鸿门剑等人均觉成缊袍应变敏捷,心下赞许。慌乱中的江湖群雄也有所安抚,较为镇定。但成缊袍心中却是忧虑至极,此地毫无遮拦,又无食水,团团包围的局面十分不利,若是等待雨停冲杀出去,死伤必定不少。而居高临下的风流店等人不知心怀何等诡计,若是有人被擒,牵连必定不少。
“素素,下面的人在挖坑了。”二楼眉开眼笑吃着毛肚的抚翠笑嘻嘻的道,“多大的一个坑,说不定可以埋下几百具尸骨。”白素车站在那里淡淡的看,“只要东公主出手几掌,就如风卷落叶,那群蝼蚁将死大半。”抚翠连连摇头,“鬼主还没来呢,让那群死士拿着箭围着,也不知道干什么,要杀就早点杀,让我等着等着,想杀人的心情都没了。”
“他莫约是遇到了要紧的事。”白素车目不转睛的看着外边黝黑的天色和大雨,“你不觉得现在这种天气,虽然圈子里的人冲不出来,但有谁自外面靠近这里,我们也看不出来吗?”抚翠哈哈大笑,“你想说也许会有变?”白素车淡淡的道,“我只是想……今日这等大事,难道唐俪辞真的不来吗?”
听闻“唐俪辞”三字,抚翠的脸色变了变,一直不语的黑衣人突地冷冷的道,“鬼主来了。”只见风雨中一道黑影如鬼魅般自丽人居后的山谷中升起,转眼间飘入二楼雅座,而未发半点声息。白素车、抚翠、黑衣人及一干下属一齐向来人行礼,这人黑衣绣花,正是鬼牡丹。
“鬼主怎地如此之晚?”抚翠笑了笑,“刚才是谁在下边捣乱,烧了许多帐篷?”鬼牡丹阴森森的道,“方平斋。”抚翠颇为意外,“真是见鬼了,他为什么要和你过不去?”鬼牡丹抬手,“六弟这人重情义,他来找人那是意料中事,放心,对他我另有打算。”他略略瞟了眼楼下的众人,“底下的谁在主持?”
“看起来是成缊袍和文秀老尼姑撑住场面,董狐笔之流早已按耐不住。”抚翠笑嘻嘻的道,“鬼主若要我等杀人,我跳下去就杀那老尼姑。”鬼牡丹自怀中抖出一物,“来的这几百人,我只要各派领头人物,我要生擒,不要你杀人。”他抖出的是一张人皮,白素车触目所见,微微一震,“这是——”
“这是柳眼的人皮。”鬼牡丹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底下的人听着,柳眼已入我手,猩鬼九心丸的解药也在我手上,他的人皮在我手上,有谁不信?”江湖群豪面面相觑,面上都流露出惊骇莫名的神色,解药被风流店所得,那大家要如何是好?只听鬼牡丹阴森森的道,“我知道你们各门各派都有人需解药救命,这样吧,各派掌门自废武功随我走,一年之后毒发之期,我如期向各门各派送发解药,绝无虚言,这样可好?”
“胡说八道!”文秀师太怒道,“我峨眉弟子就算毒发身亡,也绝不受你妖人要挟!”鬼牡丹尖声怪笑,“哈哈哈,你文秀师太怕死,就能牺牲门下弟子性命?我请你做我座上宾客,待以上宾之礼,你随我走绝不会死也绝无痛苦,但你门下弟子因你不受要挟,就要受那浑身长斑、全身痛痒而后全身溃烂烂得只剩下骨头的痛苦吗?你有种就服下猩鬼九心丸,陪你弟子一起受苦而死,否则就不要在这里做出那道貌岸然的模样说你峨眉的气节。”
文秀师太勃然大怒,拔出剑来,然而楼上高手云集,鬼牡丹所说并非毫无道理,一时也难以反驳,她又非能言善辩之辈,顿时语塞。要她服下猩鬼九心丸带领弟子退走未免不值,而要她为虚无缥缈的解药之约自废武功随鬼牡丹而去,更是匪夷所思;但话说到这份上,她若掉头就走,确也难逃不顾门下弟子死活之嫌。众人面面相觑,中毒在身的人满脸期盼,各派掌门眉头深锁,都知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局面。
“如何?各位深得弟子敬仰、名满天下、虚怀若谷、正气凌然的江湖侠客,你们的决定如何?你们的真面目是怎么样的?今天就让大家一起看一下,看一下是我风流店恶毒,还是你江湖白道的嘴脸难看?”鬼牡丹嚣张至极的狂笑自大雨中传来,越是模糊就越显得狰狞刺耳,夜里星月无光,风云急变,天地间宛若只剩下一张庞大的鬼网、一只强大得难以战胜的鬼王在狂笑,它每笑一声,雨就似下得更大、夜就似更黑,永远不会天明一般。
“拿到了一张不知是真是假的人皮面具,就能证明你抓到了柳眼吗?”哗啦啦倾盆大雨之中,有人的声音穿越雨水和密林遥遥而来,声音却依然秀雅温和,仿佛只是面对面在说话,连每个字最后的余韵都能让人分辨得清清楚楚。文秀师太一怔,蓦地脱口而出,“唐俪辞……”
围成一圈正在挖坑的众人一起站了起来,其实文秀师太未曾见过唐俪辞一面,但在如今情形之下,有人说出这么一句话,她不假思索就认定那是唐俪辞。
除了唐俪辞,无人能说这样的话,以这样的语气,在这样的雨夜里。
成缊袍又惊又喜,极力往密林中眺望,然而黑夜之中什么也瞧不见,只有耀花人眼的大雨反射着丽人居的灯光,唐俪辞不知在何处。但他怎会突然出现呢?他不是留在好云山和桃姑娘商讨大事?桃姑娘呢?她怎会没来?
鬼牡丹闻声已经大笑起来,“阁下居然能及时赶到,我真是佩服、佩服!只不过——听阁下方才的口吻,难道是说我没有抓到柳眼,难道是你抓到柳眼了吗?哈哈哈哈……”风雨之中,有人含笑回答,“你和我谁也没有抓到柳眼。”
鬼牡丹一怔,众人纷纷往声音的来路望去,心驰神往,只盼唐俪辞所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的。就在众人目光之中,一人的身影自密林中某处飘然而出,一身白衣犹如仙染云渡,临空摄步般横空掠过,轻轻落在成缊袍身前,瓢泼般的大雨对他仿佛没有任何影响,一头银灰色的长发在雨中闪烁生辉,正是唐俪辞。
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低呼,人人都不知不觉长长的吁出了一口气,唐俪辞右手握着一柄收起的白色油伞,左手里拿着一块白布,神色甚和,“一阙阴阳鬼牡丹,你我谁也没有抓到柳眼,何必拿解药之事欺人?你很清楚,你没有解药、我也没有解药,有解药的只有柳眼,而他留下人皮与书信,已经离开。你不过得了张人皮,我不过得了张书信,仅此而已。”
此言一出,丽人居里风流店几人神色一变,江湖群豪议论纷纷,文秀师太等江湖高人却是松了口气,围在唐俪辞身边,低声问他是怎么一回事?
唐俪辞扬起他手里的那块白布,那布上正是写着柳眼的那几句话,众人传阅下去,虽对柳眼突然要“以招换药”颇为不解,但却更是松了口气。
柳眼无意以解药控制何门何派,他只是要绝世武功。
如果武功能换取人命,那绝代的剑招、拳法还是有所价值的。
丽人居上,鬼牡丹的讶异更胜于愤怒,他方才将雪线子押下命余泣凤看管,而柳眼必定就在左近,红蝉娘子和一干妖魂死士带着十条土狗沿着雪线子的来路追踪,必定能抓到柳眼。但这张写有柳眼笔墨的白布怎么会突然到了唐俪辞手上,雪线子和余泣凤难道竟然落入唐俪辞手中?而唐俪辞又怎会知道自己其实并没有抓到柳眼?
这十里方圆遍布自己的人马,唐俪辞是怎么突然出现的?然而唐俪辞的确就在眼前,而他手上所拿的,的确就是不久之前自己才亲眼看过的那块白布。鬼牡丹挥了挥衣袖,白素车领命退下,过了片刻,她重新登上丽人居,低声在鬼牡丹耳边说了几句话。
唐俪辞站在成缊袍身前,自袖中取出了一个白色小袋,这袋子材质非丝非革,通体洁白柔软,甚是奇特。成缊袍接过白色小袋,打开袋口,里面是数十粒珍珠模样的药丸,略略一嗅,阵阵幽雅的清香飘散,不知是什么东西,“这是?”唐俪辞撑开白色油伞,挡住雨水,“这是茯苓散,虽然是疗伤之药,也可充饥。”成缊袍大喜,当下将这数十颗药丸分发给数十位体质较弱、武功又不高的弟子门人。询问起唐俪辞从何而来,又如何知道众人被困丽人居?唐俪辞目光流转,尽是含笑不语,却说桃姑娘身体不适,故而今日不能前来。成缊袍和董狐笔面面相觑,西方桃武功不弱,怎会突然身体不适?唐俪辞并不解释,压低声音道,“待雨势略停,大家往西北方冲去,西北的箭阵留有死角,身法快的人笔直向前冲,自认不惧暗箭的人两边护持。往前冲的时候两人并排,之后依次列队,连绵不绝往西北角突破。你往下传话,我们不停留不断开,不能给人从中截断的机会,谁不听号令我就先杀谁。”成缊袍吃了一惊,雨势渐停,丽人居朦胧的灯光下,唐俪辞的眼中光彩流转,说不上是喜是怒,唇角微抿,并没有笑,却有一股说不出的妖气。他低声传令,对文秀师太、大成禅师、天寻子等人一个一个传话过去,各掌门面面相觑,只见唐俪辞撑伞而立,虽是站得极近,却又似站得说不出的远,能遗世而独立似的。各掌门沉吟半晌,均传令门内弟子准备列队,往西北角冲去,严令不得擅自行动。
二楼看下,只见唐俪辞头顶的白色油伞微微晃动,他和成缊袍说了什么却听不见也看不见。鬼牡丹刚刚听闻白素车所言,心中又惊又怒,突然被他困在包围圈中的众人齐齐发出一声大喝,其声如龙啸虎吟,随即两人身法如电,直往西北角扑去,其后众人如影随形,如一道白虹刹那贯穿黑色箭阵!
“放箭!”抚翠振声疾呼,几乎同时,箭阵弓弦声响,成千上万的黑色暗箭向突围的众人射去。唐俪辞白伞晃动,真力沛发,挡住大部暗箭,成缊袍长剑挥舞,文秀师太拂尘扬动,各大高手齐力施为,将来箭一一接下。西北角却没有射出半只暗箭,众人并肩闯阵,穿过箭阵之后才知西北角的箭手僵立不动,早已死去,这些人显然是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被唐俪辞所杀,众人越过一处,心里便骇然一分。
黑影闪动,丽人居上众人眼见情势骤变,鬼牡丹提起抚翠方才据案大嚼的那张桌子往楼下摔去,各人方才醒悟,纷纷发出暗器往唐俪辞几人身上招呼。唐俪辞等人身陷箭阵之中,鬼牡丹几人若是跳入其中,不免也受箭阵之害。唐俪辞白伞挥舞,一一招架,忽而撇开白伞,对楼上微微一笑。
抚翠哎呀一声,鬼牡丹勃然大怒,他这一笑,分明乃是挑衅,只气得鬼牡丹浑身发抖,一声大喝,“碰”的一声大响,丽人居二楼栏杆突然崩塌,却是鬼牡丹一掌拍在上面,几乎拆了一层楼。
成缊袍一面为众人挡箭,一面正要开口问他怎能知道众人受困于此,几时来救?又想问他如何得到柳眼那块书信?突地火光燃起,只见丽人居后烈火熊熊,和飘零的细雨相应成奇观,浓烟冲天而起,烈火腾空之声隐约可闻,他骇然看着唐俪辞,“你做了什么?”
唐俪辞晃动那柄白伞,那柄单薄已极的油伞在他手中点打挡拨,轻盈飘逸,用以挡箭比成缊袍手中长剑要有威力得多,闻言微微一笑,“我放了一把火。”成缊袍闻言更是一肚子迷惑,唐俪辞分明一直在此,那把谷底的大火,尤其是大雨之中的大火是如何放起来的?
鬼牡丹一掌拍塌丽人居半边栏杆,勉强按压下盛怒的心情,低声喝道,“走!”今日已然不可能达成目的,不如退走,能生擒雪线子也不妄一场心机,但唐俪辞此人如此狡猾可恶,他日非杀此人不可!他率众自二楼退走,抚翠一声口哨穿破黑暗的雨夜,林中箭手纷纷停手,悄悄隐入树林中退去。
突然之间,风流店退得干干净净。狼狈不堪的一干人总算松了口气,数百人将唐俪辞团团围住,七嘴八舌的问他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得知鬼牡丹没有抓到柳眼、又怎样无声无息杀了西北角的箭手,又是怎样放火?唐俪辞的目光从众人脸上一一掠过,一直看到阿谁脸上,阿谁和玉团儿站得远远的,站在众人最末。他看着阿谁微微一笑,阿谁本想对他回以微笑,却终是未能微笑出来。玉团儿却好奇的看着唐俪辞,低声不住的问阿谁他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