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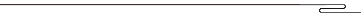
实际上现在发现的关于吉尔伽美什故事的泥板一共是十二块,但是有一块的故事在情节上无法并入到史诗的任何位置,讲的是恩启都向吉尔伽美什描述阴间的恐怖景象,但是在这块泥板的开端,恩启都并没有死,而且他死的原因是去阴间帮吉尔伽美什找回一件什么“玩具”,从而一去不返。由此可见,第十二块泥板自有因果,在情节上难以融入史诗结构的任何位置。所以现在的编排唯有将第十二块泥板单独列为史诗的外传。而实际上,这块泥板上的故事比史诗自身还要久远,它在史诗成本前早已在公元前两千年的苏美尔人之间流传。所以确切地说,第十二块泥板其实应该算是史诗的“雏形”,目前这段史诗最为主体的部分见于尼普尔出土的一块泥板。在对这块泥板的解读中我们分析一下位置的意象和死后续存的意象。
第十二块泥板的开端,吉尔伽美什的两件名叫“普库”和“奈库”的玩具掉入了冥府,见第4句“今天普库掉入了冥府”和第5句“我的奈库掉入了冥府”,他因而情绪低落。“普库”和“奈库”传说由伊什坦尔女神发明,后来在乌鲁克城风靡一时。民俗史学家考证“普库”是木球,而“奈库”是木槌,可能是原始的槌球或是门球之类的游戏,这与本文的主旨无关,在此不予探讨。而这里一个通常容易被忽略但是相当值得“钻牛角尖”的细节是这块泥板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重力感十足的词:为什么说普库和奈库是“掉入”冥府的?
这就是说,从重力作用的方向可以推算出,这个被称为“冥府”的地方,位置上处于吉尔伽美什当前位置的“下方”。这种世界观就很容易理解了,几乎所有的文明众口一词地认为,死后续存的世界,位置处在生者世界的“下方”;当然,也有一些较为多元的世界观认为在生者世界的“上方”也有一块供死后续存的净土。总之,古人对于生死的理解在某些角度上表现为一种奇特的、但是影响深远的、位置上的重力落差关系。
这并不奇怪,因为人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外部经验都是由视觉系统提供的,而视觉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捕捉事件的进程落差,从而感应世界。在此我们可以参考芝诺(Ζήνων,前490年—前425年)的“飞矢不动悖论”,如果我们将任何一个时空节点的当下共时状态定义为“现在”,那么这个“现在”必须是“静止”的才能维持时空的现实性。如果我们将“现在”的时空动量取值为0,那么任何一点微小的转变都具有了实际上的动量取值,过程也就真正的发生了。请注意,这个过程的前提:“现在”是静止的,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主观值。所以在理性的因果关系形成的时候,原始人已经习惯于将事件的时空发展理解为一种“位移”的发生。
以位移来理解一些较为抽像的过程概念已经是老生常谈之举。我们可以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做梦。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几乎所有需要以图形来表现梦境的场合,从戈雅(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1746年—1828年)的《理智入睡产生妖魔》到明代闵寓五(1580年—?)的版画《草桥店梦莺莺》,在构图上梦的内容一定被安排在睡眠者的“上方”,二者之间以一些不明所以的抽象符号或者干脆是突兀的空白予以分界,来暗示它们分属于彼此难以逾越的不同世界。与此类似的还有语言,语言在画面中的安排,只要布局允许通常也都是在言说者上方不远的位置。看来分量也是区分具体观念和抽象观念的一个标准,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安排对白的插画里,语言都被安排在位于人物斜上方的一个形似气球的东西里,而且看起来毫无重力感。
这种观念自身就隐含了人类通过位移来理解世界进程的寓意:世界因为重力感而分成很多“层次”,梦境无形无质,肯定要比肉身“轻”,所以它们的位置应该是在“上方”保持关联的有效距离之内。出于位置上的推算,应该从一个躺倒的人的上方不远、大约是离地面高度七十厘米的地方,就开始是五彩缤纷的梦境世界。范围则差不多是人体外围一米的虚构轮廓之内,这与很多宗教艺术品中的“背光”或是“三花聚顶”的构图位置大体符合。
语言和梦境“在上”,那死亡就必然“在下”,这令人联想到深达九原的幽冥的世界。毫无疑问这种看法与古人的土葬习俗有密切的关系,当遗体埋入地下之后,它随即处于生者活动的世界之下,生者由衷地热望在那里有一个属于他们(逝者)自己的世界,从死后续存进而实现永恒。由于这个世界在直观经验上很容易被证伪,所以如果希望它存在,它必须是不可见的,这样才能相安无事。而从位置体认的角度看来,只有地下是生者看不见的。有趣的是,古人有时候其实并非真的相信在脚下的厚土之中另有一个世界,至少也不觉得它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是一种简单的位置落差关系。我们来看《左传·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故事,庄公立誓不与武姜再见,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但是随即后悔,此时颍考叔建议说:“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黄泉”这个词的原意是地下水,见《荀子·劝学》“上食埃土,下饮黄泉”,但这段话里的“不及黄泉”及“阙地及泉”,两个“泉”字显然并非同指。颍考叔建议挖掘一个大隧道的时候,也明知挖出来的“泉”不可能是庄公誓言里所说的“黄泉”,这两个概念(黄泉一词的本意和引申意)之间是一种文化寓意上的转嫁关系。
挖坑埋葬死者,挖掘不得其法就会挖出地下水而功亏一篑,所以“黄泉”就成为了死亡的代名词。与此类似,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10章第28节,耶稣曾警戒世人说:“能把生命和身体都灭在欣嫩谷里的,你们倒要畏惧。”欣嫩谷这个词Gehenna,在希腊文中是γεεννα,曾经被误译为“地狱”,实际上只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常年被当作垃圾场的地名而已。早年这个地方曾有恶徒火焚活人献祭偶像信仰的行为,后来荒废成为设有焚尸炉的垃圾站。古代犹太人不准将罪人的尸体土葬而玷污大地,而是送到欣嫩谷当作垃圾焚化,所以欣嫩谷成为罪恶最终归宿的代表;在欣嫩谷焚烧垃圾及火化尸体时通常撒上硫磺粉助燃,所以地狱给人的印象也就是常年飘散着硫磺的臭味。欣嫩谷的位置在今天的Gey Ben Hinom St.,亚美尼亚区的西南面,它的北入口在雅法门南面,南入口在戴维城南面的汲沦溪畔。这个区域现在绿草如茵,边缘市镇犹太居民和阿拉伯居民杂处。1987年,法国著名杂技大师菲利普·帕特(Philippe Petit,1949年—)曾经在欣嫩谷的犹太区和阿拉伯区之间举办了一次震惊全世界的走钢丝表演,帕特原拟走到中段时,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只和平鸽放飞到空中。但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鸽子却停在帕特的头上、一会儿又停到他的平衡杆上,怎么也不肯飞走。帕特那一次的表演险象环生,一世英名差点付诸流水。
这就是说,你可以在地面上挖坑发现地下水,但是挖不到“黄泉”;你可以从耶路撒冷市中心坐轻轨线去欣嫩谷,但去不了地狱。死后的世界只有通过死亡的意象才能与现世联系在一起。
对死后续存(Survival After Death)这种普遍的世界观,英国人吉尼斯(Ivor Owen Grattan-Guinness,1921年—2014年)在主编《心灵学》(Psychical Research:A Guide to its Histor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英国太空时代出版社1982年)一书时,承认其始终存在争端。但是吉尼斯也提出了几个难以辩驳的证据,例如他转引了临终关怀领域奥西斯(Osis)和哈拉尔德森(Haraldsson)写于1977年的报告《死亡之刻》(At the hour of death,美国雅芳出版社)里举的好几个例子,尔后总结说:“例如,有几个垂死者显然看见了他或她至今还不知道(其死讯)的一个已经死亡的人,而这个人死亡的消息或者还没有到达垂死者的所在地,或者一直被有意地向他或她隐瞒着。”
我们认定一个事件不科学,并不是认为它不可信,而是无法以科学的手法来予以证明。而这些被看成是“不科学”的观点里,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死后续存的问题。几乎所有文明都构建了这样的一个世界,亡者的最终结局无论是即将轮回(佛教)还是等待复活(基督教),在死亡之后到最终结局之前的这段时间里都被允许在这个世界聚集和逗留。这个世界有时候具有奖惩亡者生前功过的特性,例如极乐或地狱;有的时候则是一个和生前没什么区别甚至一模一样的世界,例如西非传说中的“斯拉曼”世界;也有的观点声称根本没有这样的世界,只是一个过程。《瑜伽师地论》声称:“又此中有,若未得生缘;极七日住。有得生缘,即不决定。若极七日未得生缘,死而复生,极七日住。如是辗转,未得生缘,乃至七七日住。自此已后,决得生缘。”认为转世的间隔最多不超过四十九日。但是《俱舍论·卷十》则言:“应知中有初续刹那亦必染污。犹如生有。然余三有一一通三。谓本死中三。各善染无记。”这种观点却认为,死亡瞬间至来生出世之间绝无四十九天的漫长间隔,而仅存一“刹那”,也就是七十五分之一秒。在这时段(死亡至于转世之间)亡者的状态被称为“中有”,这个概念相当于密教的“中阴”(Antrabhara)。“中有”类似我们在梦中的自我,仅为意识之存在,而没有实质肉体,称为“意生身”。然而中有也受到各种缘及烦恼的影响而被“染污”,无法意识到自身之中有,而是“犹如生有”,在想象出来的、烦恼的泥潭之中继续裹足不前。
《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第十二块泥板在故事上虽然独立且更为原始,但是里面记录了很多苏美尔传说中的“阴间”的景象,因而阅读起来也妙趣横生。就好像人间一样,阴世也有很多清规戒律或是行为规范。在恩启都动身之前,吉尔伽美什告诫了他一些在阴间旅行的注意事项,这些告诫主要包括第13句“你(千万别穿)干净的长袍”、第15句“你切莫涂抹祭坛的香油”、第17句“你切莫在阴间挥舞提尔帕努(一种手杖或是飞镖类型的随身武器)”,以及第19句“你手里不要拿任何东西”。第23至26句是“你不要亲吻你心爱的妻子”“不要攻击你憎恨的妻子”“不要亲吻你心爱的儿子”“不要攻击你憎恨的儿子”,意思可能是在阴间如果遇到亲人的鬼魂也要低头避开,切不可上前相认。总之要尽一切可能避免受到鬼魂的注意,否则“冥府的嘶叫会把你抓住”(第27句)。但是第32句说“未将吉尔伽美什的叮嘱记在心头”,恩启都把吉尔伽美什的劝诫抛诸脑后,对于前面的所有戒律都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把阴间搅得鸡犬不宁。
前文提到过,生者对于亡者的心怀愧疚可能转化为葬礼上的自残、谀美以及贿献等一系列行为,这种亏欠感是确凿无疑的。因此,将心比心地认为亡者对于生者的态度是仇恨和敌视,这种推论也符合常理。在文明的神话发展出天堂里绿草如茵的溪谷花园、镶金嵌玉的琼楼玉宇之前,亡者的愤怒一直无法平息。
出于对死亡的恐惧,阴间的生活在生者们的想象中是凄风冷雨、家徒四壁的。《奥德赛》的长诗里叙述了奥德修斯在阴间的见闻,当他准备了一些蜂蜜和牛奶向阴间的孤魂致祭时,饥肠辘辘的鬼魂们一拥而上,情形实在是凄惨无比:
作过祀祭,诵毕祷言,恳求过死人的部族,我抓起祭羊,割断脖子,就着地坑,将波黑的羊血注入洞口,死人的灵魂冲涌而来,从厄瑞波斯地面,有新婚的姑娘,单身的小伙,历经磨难的老人,鲜嫩的处女,受难的心魂,初度零落的愁哀,还有许多阵亡疆场的战士,死于铜枪的刺捅,仍然披着血迹斑斑的甲衣。死人的魂灵飘涌而来,从四面八方,围聚坑沿,发出惊人心魂的哭叫,吓得我透骨心寒。
为我们所熟悉的《西游记》第十回的故事里面,太宗偶游阴世,也受到了阴魂的勒索:
前又到枉死城,只听哄哄人嚷,分明说:“李世民来了,李世民来了!”太宗听叫,心惊胆战。见一伙拖腰折臂、有足无头的鬼魅,上前拦住,都叫道:“还我命来,还我命来!”慌得那太宗藏藏躲躲,只叫:“崔先生救我,崔先生救我!”判官道:“陛下,那些人都是那六十四处烟尘,七十二处草寇,众王子、众头目的鬼魂;尽是枉死的冤业,无收无管,不得超生,又无钱钞盘缠,都是孤寒饿鬼。陛下得些钱钞与他,我才救得哩。”
《西游记》里地狱的描述取材自佛经。东汉有一位名叫安世高的安息国高僧,出身王族,舍身前曾短期担任过安息国王,于汉桓帝初年来到中土,《安般守意经序》中说他“博学多识,贯综神模……鸟兽鸣啼,无音不照”。安世高大师曾经翻译过一本专门记载地狱惨境的《十八泥犁经》。经中记载阴世一共分为十八个“泥犁”,梵文的读音分别是先就乎、居卢伜略、乘居都、楼、旁卒、草乌卑次、都意难且、不卢都般呼、乌竞都、泥卢都、乌略、乌满、乌籍、乌呼、须健渠、末头干直呼、逋涂、沈莫。在第一个泥犁里鬼魂的受苦时间“寿人间三千七百五十岁为一日,三十日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万岁,为人间百三十五亿岁”,然而一百三十五亿年只是最短的刑期,以后每深入一层泥犁,一日的长度加倍、总刑期的年数也加倍,到第十八个泥犁,刑期的长度是“寿芥种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斛,百岁去一实,芥种尽而寿未尽”,实际上应该是“不短于”2.3乘以10的25次方。此外,在此基础上每过一个泥犁,鬼魂的受苦程度增加20倍。
看来死后的生活真可谓度日如年。为了弥平这种生者对于亡者的亏欠,阳世对于阴间的祭祀不能停息,这一点在世界各个文明之间达成了共识。《吉尔伽美什史诗》第十二块泥板里,也借恩启都之口谈到了没有血食的阴魂在冥府的惨景。吉尔伽美什向天神祷告,招回了恩启都的魂魄,两人开展了一段颇为实际的对话。吉尔伽美什对于“那个世界”感到好奇,要求“告诉我,朋友、告诉我,朋友”(第90句)、“告诉我你在冥府的见闻”(第91句),恩启都却有些迟疑,觉得亡者世界的凄惨绝不是任何生者所能接受的:“我不能说,朋友,不能说。”(第92句),“如果我告诉你冥府的见闻”(第93句),“你会坐下哭泣”(第94句)。但是经不住吉尔伽美什的软磨硬泡,干脆带上吉尔伽美什到阴间一游,让他眼见为实。第100句和第101句意思不太明确,好像是恩启都指导吉尔伽美什在地面上挖了一个坑,将自己半埋起来,这可能是能令生者进入冥府的某种不传之秘。在吉尔伽美什的灵魂如愿下到阴间,这段观光旅程得以开始后,在第102至第116句里,恩启都首先指给吉尔伽美什看的是七个男人的鬼魂,他们分别有一到七个儿子。第一个鬼的境遇是“(一个钉子)钉在他的墙上,正在埋头痛哭”(第103句,此处意思不明确,可能是指“家徒四壁”之意),但第七个鬼却是“在一群初级神祇之间,坐在宝座上问理诉讼”(第116句,意为享用荣华富贵)。鬼的数量也有可能不止七个,因为第118句为“如同一面辉煌的旗帜,他倚在角落”,但是从第119句到第131句全部被损毁了,完全无法辨识。这几个鬼之所以境遇之差别判若云泥,主要因为后继香烟的数量。很明显,只有一个儿子的鬼,其阴间生活颇为窘迫,不得不以泪洗面,但有七个或八个儿子的那几位仁兄却已经扈从如云,出入衣香鬓影的上流社会。
从生物性上、以及伦理上延续自己的血脉,也是人类文明体认死亡意义、从而客观地看待主观畏死这一事实的一种解读。把永生看成是一种“事实”当然没有希望,但是永生作为现世的一种“意义”,却是可以追求的。人类至少能从三个方面来实现永恒的意义:有人追求名著竹帛、光耀青史;有人追求死后续存、轮回转世;有人则追求子孙绵长、不绝其祀。
从生物性上解读的人类对于血脉延续的追求,前文已经分析过了,就是丰产的意象,其极致情结(complex)是长子仇恨的意象。原始人希望自己的谷物丰产、希望自己的牲畜丰产,归根结底还是希望自己的子嗣丰产。所以原始人崇拜“丰饶”的意象而非“美”的意象,这个阶段持续的时间比有文字的历史要漫长许多倍,更不用说那种无中生有的美学史了。那位在史诗里每每兴风作浪、无事生非的伊什坦尔女神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恐怕不能理解为断臂的维纳斯那样的“美女”形象——就算是维纳斯自己,在现代人的审美眼光看来恐怕都是肥胖的——更不用说现代常用的诸如“楚楚可怜”“梨花带雨”之类的形容词了,原始人如果看到了这样一位袅袅婷婷的现代美女,只怕要大摇其头。1909年,几个挖铁路的工人在奥地利维林多夫一处工地旁的洞穴里发现了一尊女性小雕像,后来被命名为维林多夫裸女,更诗意一点的称呼是维林多夫的维纳斯。这尊雕像没有五官,但是乳房和下腹(子宫)却被扩大到相当夸张的地步,因而看起来胖乎乎的。维林多夫这位风姿绰约的佳丽就是典型的原始人崇拜丰产的证据。此外还有巴洛克时代的不朽名作,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1577年—1640年)的《强劫留西帕斯的女儿》,画面中两个肌肉发达的愣头青(卡斯托耳与波吕刻斯)正在试图绑架两位形如厨娘的胖姑娘,他们骑在巨马之上,对着两位佳人手忙脚乱地一通乱扯,而两位肥胖佳人的拒不合作使得整个劫持行动险象环生。这个场面与其说是暴力,还不如说是一场充满了喜悦的情欲游戏,力量和丰盈血肉的生命张力弥漫了整个画面。解读这种形象我们可以参考两方面的线索:首先,正如希罗多德在《历史》的第12章中记载的波斯风土:“子嗣繁多,在他们眼中看来乃是男性仅次于勇武的一项最大美德。每年国王都把礼物送给子嗣最多的那个人。因为他们认为人数就是力量。”在人类身处自然竞争弱势方的远古,人数是唯一可以倚重的资源,这一点需要依靠女性的丰产来实现。具有发达的乳房和子宫的女性,因为从外形上看起来更接近丰产的形象而被崇拜,至少是受到推崇。其次,母系氏族社会中晚期至于父系氏族社会,原始人虽然没有确立普遍的阶级制度,但是每个部落中总有一两位地位重要而养尊处优的女性,因为衣食无虞而肥胖,这种部族重要人物可能是人类肥胖史的先驱。原始人在羡慕她们优越生活的同时,也一并欣赏她们的体态,所以她们成为最受人爱慕的对象。“爱慕”和“羡慕”两个词,都有一个“慕”字,原始人可能并没有提炼出普适的、关于“美”的欣赏标准,但他们至少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这个“慕”字正好表达了这种虽不可得而心向往之的意思。“美”的原初含义包含了很大成分的占有欲,这种情况到如今只是变得文雅了一些,未曾根本改变。
所谓“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美的标准最初一定是实用主义的,然后经历了一个由实际转向观念的过程。其实血脉延续的传统也经历过类似的心路历程。前面说过,古人敌视身份不明的长子,这是一种实际的、追求血统纯正的需求,即要求后代必须“确实”是自己的血脉。但进入阶级社会之后,谱学逐渐发达,人们发现血统的纯正是一种隐性特质,终究虚无缥缈。所以古人开始由追求事实的血统转向追求“名义”上的血统,这种名义上的血统包括但不限于事实血统,我们称之为谱系。就是说,一个成年男性和一个男孩(通常是男孩)没有血缘关系,但是通过一系列的操作手续,社会也可以承认后者在谱系上的合法性。这些操作手续常常是过继、领养或是改宗,即使在今天也相当普遍。这就是说,一个孩子在实际上是不是自己的后代并没有什么关系(这在今天已经能够得到科学验证,但人们反而已经不介意它了),只要在名义上能够守灶就足够了。在有的时代和有的地方,甚至连通奸都是合法的,至少是被默许的。色诺芬(Ξενοφών,约前430年—前355年)在《拉栖代梦人的政制》一书的第1章记载,在城邦时代的拉栖代梦人,即斯巴达人的心目中,优生的分量重于道德。斯巴达人必须在最适合生育的年代婚配,老夫少妻的,就必须带一个年轻人回家;丈夫如果有一个在体质上有令他羡慕特征的朋友,可以把妻子寄养在这个朋友家借孕。所以普鲁塔克(Plutarch,46年—120年)在《米库古传》中也说过,斯巴达人完全不懂“通奸”一词是什么意思,更不明白这种行为有何不妥之处。这样,生出来的孩子和男主人(名义、谱系及社会关系上的“父亲”)毫无血缘关系,但还是会得到视如己出的抚养,并且在光大门楣方面更令父亲(养父)骄傲。
拉栖代梦人追求丰产出于其扩张性的政治特色,但是宗嗣繁茂的祖先在死后得到祭祀这一方面确实具有优势,这是古人眼见的事实。所以问题还是回到了人们最感兴趣的、死后续存的境遇问题上。祭祀祖先与葬礼祭祀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越是挥金如土,祭祀者和被祭祀的祖先越是光荣,子嗣繁茂的优势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在远古时代的祭祀,祭品或是被毁掉,或是干脆被神庙的祭司侵吞,例如《甲骨文合集》第32028片里有这么一句:“辛未贞,禾于河,三牢,沉三牛。宜牢?”“”字的意思是焚化,“沉”字的意思是沉入河底,可见都是在祭祀上直接摧毁祭品。这类似于现代人在祭祀上焚化纸钱,在现世的摧毁被看作向另一个世界交付的方式。不过近世人则精明得多,在祭祀结束后捏造出某种理由回收祭品,参考雷纳·格鲁塞在《蒙古帝国史》一书的第2章“蒙古国家的形成”中的描述:“这是在一个春天,俺巴孩的两个寡妇,斡尔伯和莎合台两位哈敦举行祭祀祖先的祭礼……但是在分祭肉的时候,没有分给诃额仑应得的一份。”这种回收祭品的行为在汉语中称为“散福”,所以祭祀也就逐渐转化为现代的节日。人间的一切悲欢无不与死亡密切相关。
至此史诗还剩下最后几句。在目睹了子嗣厚薄不一的鬼魂身后境遇的不同以后,从第144句开始,恩启都又指给吉尔伽美什看了五个鬼魂,这几句探讨的是死亡方式和葬礼规模的问题。前三个鬼的死因分别是被桅杆砸死(毫无价值地死于意外事故)、自然死亡、战死。显然战死者身后最享殊荣,“他的父母以对他的回忆为荣、他的妻子为他哭泣”(第149句);得享天年的鬼魂虽然谈不上有什么身后的荣耀,但他“躺在(众神)的卧榻上畅饮清泉”,也十分惬意;死于事故——“被桅杆击中”这个说法有点不明其确指,也许在苏美尔人的语言中有什么双关语用法或是典故隐喻,当然也不排除这个倒霉鬼真的是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被桅杆砸死的——的鬼魂最为可怜,第145句说“唉,他的父母啊!当钉子被拔出来时,他游荡无依”。恩启都又指了两个鬼魂给吉尔伽美什看,这两个鬼魂在死的时候没有举办葬礼,所以在阴间无家可归、乞讨为生。其中一个曝尸荒野的,“他的灵魂在冥府不得安息”(第151句),而另一个死时没有举办葬礼的更加凄惨,“他吃着瓶里的残渣和扔在街上的面包屑”(第153句)。这是现今最完整版本史诗的最后几句,这个戛然而止的结尾在现今考古发现的泥板中都大同小异,目前没有发现大段佚失的内容。尼普尔出土的一块泥板上多了几句,谈了谈那些死时举办盛大葬礼的鬼魂在阴间享受的较为优厚的待遇;而吾饵出土的泥板则多了一个结局,大意是吉尔伽美什看到了这种种的阴间奇景后觉得毛骨悚然,其中,还是最后不得葬礼的鬼魂的惨景最令他感触深刻,他当即决定回家给先父母补办一次规模盛大的葬礼,还要树立起宏伟的墓碑。史诗的第十二块泥板到这里就结束了。
所谓千古艰难唯一死,死亡方式可谓人生的最后一件大事。很多版本的阴间传说里,死亡方式是给亡灵分类的一个统计学手段。就动物的本性而言,自然死亡——死于衰老当然是最理想的死亡方式,这在当今司空见惯,但在原始时代其实连这一点也不容易做到,原始人其实是大多不知道“老”为何物的。参考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首席顾问宋兆麟教授在《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列出的资料,考古学家抽样统计了三十八位北京人的遗骨,这些先人中,寿终于五十至六十岁的只有一人,死于四十至五十岁的和死于十四至三十岁的各为三人,剩下的全都是死于十四岁以下的,多达十五人,比前面的“高寿”人数总和多出一倍有余。原始人死亡的原因中出现最多的是营养不良,其次是传染疾病,还有洪水猛兽之类的自然事故。我们的这些祖先在困顿中举步维艰地缔造着人类的文明,他们的平均寿命(抽样统计的平均,例如前面北京人那个例子里大致统计出的平均寿命是十岁零九个半月)不太可能超过十五岁。
所以上古神话中那些高寿人瑞的传说,不消说都是空穴来风了。在永生终属镜花水月的情况下,长寿是仅次于此的诱人选择。解读这些传说有三条思路。其一,我们来看这个例子,《楚辞·天问》中有这么一句说:“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东汉王逸注曰:“彭铿,彭祖也。”这位彭祖是中国历史上最富盛名的老寿星,《列子·力命》中说“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从此彭祖寿八百的传说千古流传。这种个人长寿的例子可能只是起源于古人的一个推论:“如果”一个人不出任何致死意外的话,他究竟能活多久呢?这种一时的遐想成为了很多长寿传说的基础。
第二种思路我们可以参考这样的例子,《圣经》的《创世记》第5章记载了亚当及其后裔的寿命,从亚当到闪、含、雅弗三兄弟,亚当活了九百三十岁、塞特九百二十一岁、以挪士九百零五岁、该南九百一十岁、玛勒列八百九十五岁、雅列九百六十二岁、以诺三百六十五岁(未死而归神)、玛土撒拉九百六十九岁、拉麦七百七十七岁,然后《创世记》第9章第29节记载挪亚活了九百五十岁。这一支长寿家族的前后寿算总和在时间跨度上迈越一万年,这基本和人类文明所能记忆的最早时间相吻合。这其中隐含的一条信息是:他们的传奇当然主要是出于夸张,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以文字记载历史的行为颇不发达的古代,很多默默无闻的祖先,因为其生平不能被记入档案而很快被遗忘。为了维护谱系在时间上的完整,后人只好将他们的寿算都加到那些赫赫有名、永垂青史的祖先身上。
长寿传说的第三点,人寿有尽而英名不朽。关于彭祖的长寿,汉代史学家韦昭(204年—273年)在注解《国语·郑语》时说:“彭祖,大彭也。”无独有偶,清代人孔广森(1751年—1786年)在注《列子》时也说:“彭祖者,彭姓之祖也……大彭历事虞夏,于商为伯,武丁之世灭之,故曰彭祖八百岁,谓彭国八百年而亡,非实篯不死也。”可见彭祖寿八百指的是大彭这个伯爵国从虞到武丁,持续了八百年。较早注意到历史人物长寿问题的是孔子的弟子宰我,在《大戴礼记·五帝德》中记载了他们师生的一段对话,宰我对于黄帝寿三百年感到困惑,问孔子说:“昔者予闻诸荣伊令,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三百年乎?”对于这个问题,孔子明确地表示自己不知道:“先生难言之。”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可见,生有涯而名无限,英名的流颂被看成是延续生命最伟大的方式。
这样,话题就自然地被引转到那位战死沙场的、光荣的鬼魂身上。尽管为了非个人的目的而献出生命一向被道德标注为至善和光荣,但我们还是要问,在与生物本性相悖时,“道德使然”的很多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年—1860年)将此解释为,“生存意志”这种东西——出于形象考虑,我们姑且将之想象成一个形如某种北欧野兔的、狡诈的怪兽,某种支配一切的地下之神——具有寄生的性质,为了其自身的延续而诱使宿主做出违背其个体本性而有益于群体的选择,但是他的私淑后学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900年)却对于这个解释非常不满意。尼采也不屑于假手某种虚无缥缈的、想象出来的新上帝来解释世界的混乱与虚无,他认为人就是人,连上帝都是不存在的。在《论道德的谱系》这篇文章中尼采认为,我们一直以为其存在的“道德”其实是一种“高贵道德”,也就是说附和地位高贵之人的价值准则,这被看成是“对”的。古代犹太人被埃及法老劫持为奴隶,本来逆来顺受,但因为埃及法老欺人太甚,所以他们发动了一场道德上的奴隶起义。然而这场起义即便是胜利了,结果也只是“教士道德”在埃及法老之后成为新兴的“高贵道德”。为此尼采愤怒地说:
接下去是金属的时代,也就是那些被践踏者、被剥夺者、被残害者、被拖走和被贩卖者的后代所看到的那个世界:据说这是矿石的时代,坚硬、冷酷、残忍、没有情感和良心;一切都被捣毁并沾满血污。假定,现在被当作“真理”的东西果如其然,假定一切文化的意义就在于把“人”从野兽驯化成一种温顺的、有教养的动物、一种家畜,那么我们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把所有那些反对的和仇恨的本能,那些藉以最终羞辱并打倒了贵胄及其理想的本能看作是真正的文化工具,当然无论如何不能说,那些具有这种本能的人本身同时也体现了文化。
人类道德的全部历史其实可以被解读为一种限制的历史,对于任何一个被看成是“社会的”人的个体而言,道德首先是不许他干什么,然后才是允许他干什么。而这种观点被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984年)坚信,他由此而归纳出,“限制”——而非道德——才是社会的一种实质性质。几乎所有的社会福利机构,例如医院、学校以及博物馆,都带有强制的秩序性质;而在所有的社会正义机构,例如法庭、警察局,这种强制更是作为威慑而被向公众展示,“善”的上古含义至今已经变成一种彻头彻尾的嗟来之食。然而缔造者自身——所有自诩为道德的人类——也难以置身事外,他们也同样成为了这种禁制的牺牲品。一个“社会的”人从八岁到十岁开始就被灌输什么是“对”的这个概念,这种仪式最终缔造了他们人格结构中被认为最为文明的部分,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然后他们按照这个被预设为“正确”的准则度过短暂的一生,并且真诚地相信这是他们微不足道的人生的全部意义(这一点令无数被虚度的人生看起来显得不那么遗憾,倒也没什么不好),并在死前竭力将其传承下去,好让其继续俘获他们的子孙。道德之所以青睐地位高贵者,也只是因为他们对于它(道德自身,我们在此暂且给它加上一个所有格)的传承不仅更不遗余力,实际上也有能力作出更大的贡献。而且,除了极少数地位高贵者,抑或是思想高贵者如尼采自己外,大多数人基本不会去思考道德这东西本身是对是错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大多数人对于道德自身的存在而言是没有威胁的。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也认为道德的本末倒置隐秘得几乎无人能够觉察:
首先,人们把个别的行为称作好或坏,完全不考虑这些行为的动机,而只是考虑有用或有害的结果。但是,不久以后,人们忘记了这些称谓的起源,误以为“好”或“坏”的特性是行为本身固有的,不管其结果怎么样。由于这样的谬误,语言把石头本身称为硬的,把树称为绿的——也就是说,颠倒了因果关系。
而在文艺复兴之后,教会思想没落了,符合现代社会的道德原则俘获了社会契约。我们根据它的新特质给它起个名字,就叫“知识道德”,即具有知识者——就像莎士比亚、伏尔泰或是康南海这样的人——有权设置道德的游戏规则。到当代情形又为之一变,“知识道德”蜕变为“传媒道德”,这个我想不需要解释了。然而无论如何嬗变,它——道德,一位悬浮的、鸟瞰的、无重力的、无所不在的、无远弗届的、温文尔雅的、义正辞严的、救死扶伤的……神——始终无法摆脱其“高贵道德”的本质。
这里似乎应该加一个脚注,“传媒道德”看似草根,判断的权力掌握在每一个后现代的、个体的“人”手中,看起来很像我们构思中的“自由”的某种皮相。但是在面对牢固的、价值体系的大厦时,这些“人”自己发声的“行为”即便是自由的,其“观点”是不是自由的,也很值得商榷。每当一个传媒的事件发生,人言谔谔,看似群情激愤,但是他们的理由和言论却很少超出能够推测得到的价值观范围。这一点非但不能证明时代许诺给凡人的那些自由的最终兑现,反而证明了枷锁变得无形、更加根深蒂固、更加难以挣脱。
这样一来,只要稳住了地位高贵者的位置,让他们因为符合自身利益的思路得到贯彻而高兴,道德可以说扫平了一切颠覆性的障碍。然后,个体死亡,但是道德得以延续下去,一切又将重演。这场拉力赛的一个凄凉的战果是,道德是不死的,但在道德彻底劫持人类的社会的时候,却唯有死亡是自由的。然而如同夹缝两侧两场永无止息的风暴,这两位势均力敌的强者都不是人类所想要的。道德试图以永生来为其价值加注,然而无论是“力者永生”“信者永生”还是“义者永生”最终都是镜花水月:无人永生、无人躲得过死亡永恒的追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