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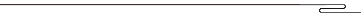
第一到第六块泥板通常被称为史诗的英雄悲剧部分,描写了主人公年少轻狂岁月的荒唐生活。乌鲁克城城主吉尔伽美什风流倜傥,拥有这个城市的“初夜权”而放荡不羁。在很多文明之中,处女的初夜属于祭司或是某尊神像,苏美尔是政教合一的文明,所以这可能透露出了吉尔伽美什宗教贵族的身份。另外一处的证据是第九块泥板的第49句“那靠近我们的人,带着神性的人”和第51句“他三分之二为神而三分之一为人”。凡人皆有神性,祭司之所以受尊敬是因为他们更为专业,这种专业性时常被理解为这样直观的数字比例。祭司或巫师其实是“神”的概念的第一直观印象,这一点在后文会专门分析。关于吉尔伽美什的初夜权,证据见于第一块泥板的第76句“不让任何一个女孩投入……”,至此泥板崩坏,但第77句是“那位勇士的女儿、那个年轻人的新娘”,所以第76句缺失的部分应该是“新郎的怀抱”,当然也有可能是“父亲的怀抱”,不过从文意推断,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吉尔伽美什的为非作歹使得乌鲁克市民不胜其烦。所以他的第一个任务是怎样变成一个操守高洁的人,也就是要放弃人的动物性,勇于承担起道德的压力。
命运将这个任务交给一位名叫恩启都的巨人完成,此人半人半兽,是一介游侠,从野人出身。有一个神庙的神妓沙姆哈特以身相许——古人,无论是在两河流域、印度还是西藏,都普遍相信性行为似乎具有某种给砂石注入生命的古老魔力——这使得恩启都变成了一个文明人。恩启都听到乌鲁克市民的抱怨之后决心为民除害,截杀吉尔伽美什。两人相遇后如何从生死格斗发展到惺惺相惜,结为刎颈之交,以致吉尔伽美什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两人一起行侠仗义扫荡群魔的情节,与母题探讨无关,在此略过。
英雄悲剧的第二部分主体情节是女神伊什坦尔爱上了吉尔伽美什,但是伊什坦尔生性淫荡、面首如云,深为吉尔伽美什所鄙薄。被拒绝的女神恼羞成怒,要挟神王阿努(伊什坦尔之父)放出天牛。女神威胁说,如果不放出天牛,“我将把地狱弄得天翻地覆”(第六块泥板第97句),而且“我将释放冥府亡灵吞噬一切生命”(第99句)。但是天牛随即也被吉尔伽美什和恩启都斗杀。
在英雄史诗中,除去两人的相识和行侠,性欲描写(吉尔伽美什的放荡生活、恩启都与神妓的交往、女神对于吉尔伽美什的挑逗)占了很大比重,我们不能将之仅仅看成是增加风味的香艳故事,而要分清其中的隐喻含义。
首先,关于宗教奴隶主的初夜权。欧洲中世纪的初夜权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古希腊斯卡门德尔河一带,准备出嫁的新娘要到河里当众洗澡,并高呼:
斯卡门德尔神啊,请接受我的贞操吧!
,扮作神的男子这时便上前与她性交。希罗多德('Hρόδοτος,约前480年—前425年)在《历史》中提到塞浦路斯的法律规定:每个女人出嫁前都必须先在神庙中充做神妓——一种将卖淫所得的嫖资布施给神庙的公娼——以向路过该岛的陌生男子提供性乐。无独有偶,《旧约》记载了亚摩利人(Amorite)也有同样的风俗,所有将要出嫁的女子,须先卖淫七日,方可结婚。这样的例子车载斗量,对此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年—1961年)在《心理学和文学》一书中认为:
我还可以提出“双重血统”的母题为例,所谓双重血统是指同时从人的和神的父母处获得的血统,就像赫拉克勒斯那样因受天后赫拉的抚养而获得了神性……(此外,)埃及法老的本质也是人神合一的。在埃及神庙的出生室里的墙上就描绘着法老的第二次神圣的孕育和诞生……这一观念隐伏在所有的再生神话中,基督教也同样包括在内。基督自己就有过“两次诞生”:约旦河中的洗礼赋予他以新的生命,使他从水与精神之中再生了……多亏了这一两次诞生的母题,今天的孩子们才有了一个“教父”和“教母”作保护人……两次诞生的母题与两位母亲的幻想无处不在的联系应和了人类中一种普遍存在的需要……如果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确是在圣安妮和圣母玛丽亚的形象中描绘他的两个母亲——对此我表示怀疑——那么他也只是表现了他以前和他以后无数人都相信的某种东西。
然而这种解读的问题在于,将人肉体和精神的缔造看成两次价值对等的诞生的看法,依然是一种对事实的解释,而非事实自身。我们承认这种解读之重要,已经深植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之内而成为人性的柱石,但它毕竟是解读,它还不够古老,通常我们对于这种“古老”的要求是:它的诞生就算是比有逻辑的语言出现要晚,也至少不能相差太多时间。这样看来,即便是古埃及最早期的关于法老的传说,也比我们构思中的“古老”的概念迟了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这些古老的意象,有的可以解释,有的则完全难明其中奥妙。
现在让我们把眼光放在奴隶时代以前,也就是晚期智人(五万年前开始)末期至新石器时代——现代人依然属于晚期智人,所以这个截止日期是必要的——的这段岁月。根据某些民俗学者的解释,原始人害怕见血,处女初夜谓之“见红”或是“撞红”。撞红的迷信是一种禁忌,禁忌一词,有的译本也直接选用澳大利亚土人语言tabu,巧妙地音译作“特怖”。特怖,也就是禁忌是一种带有传染性的纯心理能量,触摸过不洁之物的人被看成是不洁之人,他也变成了不可触摸者,这种一传十十传百的扩散是原始人最为恐惧的。虽然迷信中特怖将会引发的恶果大多是无中生有的妄想,但被特怖污染者会出现以恐惧和焦虑为主的多种心理疾病,甚至引发神经和器质官能疾病,所以结果往往也是一语成谶。因此有些地方的古人,女子初夜通常延请较有身份的人,或是具有一定神格的巫师进行,是考虑到也许他们优厚的社会地位来自某种超自然的保护;甚或是由不相干的路人代劳,这样至少诅咒降临不到自己人的头上。《旧约》引用古犹太的风俗,声称“凡妇女行经,必不洁七日。凡扪之者,必不洁至夕。不洁之日,妇女所坐所寝之物,皆为不洁”(《利未记》第15章19节至20节)。在这里月经其实已然成为了一种特怖,实际上是规定人们不可经期性交。
第二方面,除了作为原始氏族首领垄断交配权这种风俗的余韵以外,对初夜权的统一控制也是人类文明中仇视长子风俗的一种应对之策。原始人没有贞操观念,也不懂生育的科学,双方长期性关系确立(过门)以后,妻子和前一个性伴侣如果育有后代,这些后代就会被继父视为外人,而妻子过门以后生的孩子则是血亲。这时候,如果具有“外人”和“血亲”两种身份之间的模糊身份,地位就十分尴尬。一个老实巴交的乡佬倌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妻子,但他却吃不准头一个出生的孩子是他自己的、还是妻子和以前情人所生,而从次子开始则没有这层顾虑,处于这种尴尬地位的正是每一家的头生子。从这方面来说,每一家的长子都是一个“朮赤”——Djotchi,这是一个乞颜蒙古语单词,拉丁拼法来自雷纳·格鲁塞(René Grousset,1885年—1952年)的《蒙古帝国史》(L’Empire Mongol,1941年),它的意思是“不速之客”。成吉思汗新婚燕尔时妻子蒲尔帖被蔑尔乞惕人掳走,所以长子的血统一直是这位世界征服者的一块心病,出于疑虑,他给长子起了“朮赤”这样一个名字。成吉思汗虽然声称对朮赤视如己出,但实际上分给他的土地又差又远。朮赤因此而忧郁成疾,活到四十七岁就死了。他的封国远在额尔齐斯河流域的钦察利亚,土地又寒冷又贫瘠。
这种父权和长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一些文明中激化到了极致,《墨子》中有记载说:“鲁阳文君语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桥,其国之长子生,则鲜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岂不恶俗哉?’”在《博物志》中记载其地为“輆沐之国”,楚国南方(越)的“輆沐之国”,这就很容易考证了,现在普遍将之音译为“河姆渡”,其文化圈中心在今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第四文化层最早可以上溯到距今七千年前,那正是母系氏族社会较为繁盛的时期,此后则逐渐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尽管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女性在性选择上所享有的更宽泛更主动的权力,在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逐渐消失,但是对于先前开放的模糊回忆已然足以引发男性在后代血统问题上的警觉。这种杀死长子以宜其弟的行为其实是对于血统的保证,和狮群中新狮王咬杀前任狮王遗腹子出于同理。其他的一些文明对于长子的敌视虽然没有这么强烈,但至少也希望长子自己死去。《出埃及记》中记载了天使杀遍了埃及人的长子,与其说是一种威胁,还不如说是助力。天使们杀得兴起,索性连头生牲畜也一并干掉了。
正所谓不是仇人不成父子,看来从庞大的、人类文明的悲剧背景角度看,这句话还不仅仅是具有某种夸张比喻的修辞意义而已。有些原始文明中有“生育巫师”,荣格认为这是融合了“巫师”和“出生”两种原型产生的结果。目前还没有任何文献表明古代苏美尔有这样的风俗,但是这种巫师的初夜权职能是对于这种仇视长子风俗的应对策略:强行将各户头生子的身份统一——来自神,——能够最大程度地消除父亲们似是而非的顾虑。
然后我们来分析一下伊什坦尔女神的淫荡性格。紧跟在第六块泥板的第44句“来吧,让我数数你一共有多少位情人”之后,吉尔伽美什一共列举了植物神达摩兹、阿拉鲁鸟、狮子、战马、牧羊人、园丁伊殊拉努六个伊什坦尔的旧爱,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吉尔伽美什因此而质问女神说:“你会爱上我、并如(对待他们)一样(对待我)么?”(第79句)
滥交和高产本来就是丰饶的保证,这一点在氏族社会的上古文明中并不承担很大的道德压力,因为它们比道德本身更加古老。进入了道德至上的文明社会以后,性行为反而束手束脚,甚至成为了一种罪恶。很多文明的早期信仰里都有崇拜抽象的自然原生力的痕迹。凯尔特人中学识最为渊博的德鲁伊祭司为了膜拜这种自然原生力,将包括活人在内的祭品放在一个人形的木笼子里焚烧献祭。德鲁伊教的伦理也不禁止青年男女之间自行选择并建立不稳定的性关系,这种习俗在其他文明中被称为“偎郎”。考虑到族群内部的血亲障碍,人类的性关系进一步进化而出现“普那路亚婚”,也就是伙婚,即一个部落一定数量的年轻男子和另外一个部落数量对等(也许不一定对等,这取决于不同地域和文明中的性别政治现状)的年轻女性组成“伙婚”群落。普那路亚一词来源于夏威夷的土人语,意为“伙伴”,这种婚姻的原始状态的学名为“外婚制”。
伙婚是从部落到家庭的过渡阶段,它的科学之处在于,它的部落间匹配避免了近亲婚配——这是伙婚的最初优势。而借由普那路亚婚而诞生的孩子,血统非但不求明晰,反而被刻意模糊。这是原始婚姻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血统这东西,反正弄不清楚——应该说无论如何撇清都无法消除父亲心中的疑窦——索性让它变得更加模糊,也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办法。在这种相安无事之中人类度过了上千年的悠悠岁月,对于任何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而言,普那路亚家庭群落里的每一个男子都是他的父亲,每一个女子都是他的母亲。所以伙婚兼具优生学和谱学两方面的优势,尽管它从表面上看起来,常常被跨过了伙婚时代的自以为更文明的人们想入非非地理解为一种放纵的混乱性行为——即便那是真的又怎么样,在人类文明普遍的悲剧背景下,一切都是不需要解释的。
德鲁伊教在罗马皇帝提比略(Tiber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前42年—37年)时代被禁止,可以看成是生育崇拜最终让步于道德崇拜,而后者往往被看成文明的标志。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之中,吉尔伽美什的改邪归正和他对于伊什坦尔的鄙夷正是对这种交锋的暗示。
性欲就是生存,就是繁衍,就是丰饶,没有任何一种感觉比性欲更加给人以“生”的感受,唯其远远比语言古老,所以它是不可言说的,性是一个巨大的语言盲区,只能依靠暗示。
英雄史诗第一部分的另一种殊途同归的诠释,线索来自于弗洛伊德于1923年撰写的《自我与本我》一书。在这部晚年的成熟著作里,弗洛伊德将敏锐而予取予夺的本能称为“本我”,它是人格最动物化的部分,它就好像一口沸腾的大锅,受到“快乐原则”的支配而永不饕足,为人格提供动力。“自我”是“现实化了的本我”,是本我在无数次碰撞和受到惩罚之后变得事故和圆滑了的结果,它既要获得快乐,又要规避痛苦,是人格遵循“现实原则”在现世生活部分。而“超我”则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它在社会原则的熏陶下对于价值体系(道德)产生了仰慕之意,或至少是这种仰慕的自我暗示。超我所遵循的“道德原则”最关注的是对错、善恶之类语言派生的理性观念,它大约形成于人格八岁到十岁的时期。
“超我”是人格结构里最成熟、最高尚的部分,因而也是最虚伪的部分,它不仅要求本我圆滑避事,同时捏造出一种无中生有的道德原则,要求人格相信这种选择是正确的。也正因为此,我们把一个人格的重心从动物性的本我向社会性的超我的摆动,看成是一个文明人的诞生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英雄史诗里吉尔伽美什浪子回头、恩启都开启天智的心路历程。
至此不言而喻,《吉尔伽美什史诗》的英雄悲剧部分在描写两兄弟行侠仗义的同时,安排了吉尔伽美什的初夜权、恩启都与神妓沙姆哈特的相遇等大量的性描写,暗示的就是“生”这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