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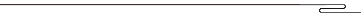
博尔赫斯对于文明的深刻剖析令永生的观念跃出了睡前故事的浅薄范畴。当然,认为死亡是文明之母的看法并非为博尔赫斯所独有,阿瑟·查尔斯·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e,1917年—2008年)在《城市和群星》这篇小说中,这样描述一群喜爱幻想冒险的封闭人群的生活态度:
那些设计出种种历险活动的艺术家受到了控制迪阿斯巴所有市民的古怪恐惧症的感染,就连他们为别人设计的那些冒险活动也必须安安稳稳地在室内、在地下洞穴中,或者在群山环绕、与世界其他部分完全隔绝的小山谷里进行。唯有一个解释。在很久很久之前,也许是在迪阿斯巴建立之前,曾经发生过某件事,它不仅摧毁了人类的好奇心和雄心壮志,还把人类从群星送回了家,蜷缩在地球最后一座城市的小小的封闭世界里,以求庇护。
而这些故步自封的人正是永生人,他们一潭死水的生活与博尔赫斯笔下的穴居人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拥有了无限的时间可供浪费,那么一切建设都没有必要进行了,至少没有必要马上进行了。情形恰如小学体育课上疲惫的令人苦不堪言的长跑,我们曾经多少次在长跑比赛的前一天祷告这一天在某种奇迹发生的作用下被跳过去,从今天直接跨到后天,而不介意我们的生命因此而被缩短了一日——我们有几万天的生命,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觉得这种舍弃是值得的;而如果我们拥有无限的生命,那么这种挥霍更是丝毫不值得介怀的了。
正是因为目睹他人之死乃至主观畏死,而死亡意识又是建设文明必不可少之物,悲剧及悲剧型的思索成为了人类文明的母题。母题二字的意义可以理解为最原初的思索,而后世所有的理性思考都根植在它的基础上。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入一个文明史中较为原始的例子,古代苏美尔—巴比伦文明。苏美尔人早在公元前36世纪已经建立了文明社会,比古埃及早王国的开端(前31世纪)要早五个世纪。世人通常将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前36世纪至前21世纪)看成是两河文明的第一谱系,古巴比伦(前19世纪至前17世纪)为第二谱系,亚述和新巴比伦(前9世纪至前6世纪)为第三谱系。到公元前24世纪,一个名叫萨尔贡(Sargon,约前2316年—前2261年在位)的园丁僭取了苏美尔卢迦尔(Lugal,此词并非人名,乃是苏美尔国王的一种称号,为苏美尔三种国王称号中权势最大者,类似埃及的“法老”)的王位为止,最古老的苏美尔文明已经持续了超过一千两百年。苏美尔灭亡了三百年以后,中国的夏朝(公元前21世纪)才刚刚开始。
文明有多久,悲剧就有多久。苏美尔的创世神话《埃努马埃利斯》一共有七块楔形文字的泥板,故事——或者说这个世界——开始于一次谋杀:创造者阿玛特和阿帕苏为他们创造出来的神灵所背叛并杀害,被肢解的尸体成为了这个世界的雏形。与盘古开天辟地这样的创世神话相类似的是,世界即是神的肉身的看法,在古代苏美尔人的思维中也很有市场。原始人很早就注意到,死亡—腐败—孕育—再生的过程乃是世界的物性特性循环的规律,这个过程值得被膜拜。现在很难说这种自然规律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禁忌性并开始被祭祀,但肯定比有历史的文明要古老。《埃努马埃利斯》里面描述的众神杀死并肢解创世神的血腥场面令人不寒而栗,其原形在古代也许只是一次非常普通的杀生涂血祭祀,祭品不一定是——但有时候是——活人;祭祀的对象是自然原生力的慈悲,及其令人敬畏的一面。这种祭祀在中国古代也有,《殷墟文字丙编》中的第七片甲骨,里面有一个字用现代的方块字写出来就是,意为将祭品剁碎的一种祭祀方法。死亡和生存之间的关系在古代非但不那么对立,甚至非常辩证。
对于神的不敬和敌意,我们后文会有所分析。不独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人,世界上很多古老民族的传统中都残留有膜拜某位被杀死的神、或是干脆亲手杀死神的痕迹。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年—1941年)在《金枝》第59章中记录了阿兹特克人在祭礼中杀死神的仪式:
……祭仪是在阿兹特克人年历的五月的头一天举行。……在这个节日上,这位伟大的神在一个人身代表身上死去,在另一个人身代表身上复活。……这一高贵尊严的职务是从俘虏中细心挑选体格健美的年轻人来担任的……他尊贵地住在一座庙里,贵族们侍候他,向他礼拜,送肉给他,对他像君主一样服侍。……到了最后一天……祭司们抓住他,把他面朝上仰着按倒在一块石头上,一个祭司划开他的胸膛,伸手掏出他的心脏捧着祭祀太阳。
然而神毕竟是虚无缥缈的,以一个肉身的人作为神的代表,无论将他打扮得多么光鲜、多么气势非凡,也终究难免自欺欺人。所以古人们有的时候退而求其次,杀死神在世间的代理人:祭司,或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中的国王。除了《金枝》中有所记载外,有些童话譬如博尔赫斯的《布罗迪报告》中都记载了原始人杀死国王成就祭礼的故事,这都是确有其事的。
《埃努马埃利斯》神话中潜藏有一种很有趣的观点需要被破译:其与其他文明的创世神话(例如盘古开天辟地)的区别在于,阿玛特和阿帕苏并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世界的诞生是凶手在毁尸灭迹时产生的一个意外。这样一来,世界的存在毋需为造物主的牺牲承担什么道义上的责任。
非僭取的合法取得也承受道德压力。这种道义上的不安源于人对于父母死亡的目睹,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这样想:
是他(她)给予我生命,现在他(她)死了,可我还活着。
对于每个人而言,父母不仅是生命的给予者,也是生活资源的给予者。但是对于这种资源的接受,被理解成是一种夺取,无论途径是否合法。这些遗产可不仅仅是几只用缺了口的瓶瓶罐罐而已,在我们的祖先尚未完全脱离动物界的时分(也是创世神话所能上溯到的最早时间),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在兽群中的交配垄断权。这种交配垄断权的解释揭示了一条令人毛骨悚然的解读:在一个族群中,所有的异性在谱系上其实是他(遗产继承者)的母亲,我们将此称为乱伦禁忌。参考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的分析,作为这种夺取的交换,祖先(主要是父亲)被高高在上地崇拜,因而形成图腾崇拜乃至于宗教,所以所有宗教里的神都是权威的、说教的和体罚的,与父亲相似。而对于父母死亡的目睹已经成为了一种本能,所有人都会梦见父母死亡和乱伦。但因为这种禁忌的原因太过于难以启齿,如其字面的意思,成为了一种“禁忌”,所以它变得不能面对了,只能以一种“移情”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所以我们就有了种种光怪陆离的宗教和仪式性行为。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说:
一些禁忌的目的十分清楚,另一些却相反。……强迫性禁忌极其易于转移替代。
这种生者对于死者的源于本能的亏欠感在《埃努马埃利斯》中被巧妙地回避了,造物主的死亡基于某个更直接的原因,道德责任非常明确,生者也不需要承担这种模糊的亏欠感。
在苏美尔文明中,诸神成为了替罪羊,而这个“罪”就是生存自身。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苏美尔神话中的神既不值得尊重——《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第十一块泥板(共三百零五句)中有这么一句话提到,饥饿的诸神“蚁聚于献祭者周围”,而“蚁聚”只是我们在翻译时借用的一个听起来较为文雅一点的词而已,原句是“像苍蝇一样”——也不是永生的,《埃努马埃利斯》接下来的一段传说就是,丰饶女神伊什坦尔的情人——植物神达摩兹横死,伊什坦尔痛哭哀歌道:
吾之夫君兮一去不归;
地下宝藏之主兮一去不归;
抚爱田中柔芽者兮一去不归;
地力之王兮一去不归。
伊什坦尔于是勇闯阴世冥府,寻求生命之泉。幸运的是,她成功了,恋人重新回到了她的怀抱。
伊什坦尔在苏美尔诸神传说之中的戏份很重,她完全被按照一个世俗女子的形象设计,行事不思后果,时常惊惶失措,特别惧怕死亡。这也许暗示了在坚如精钢的死亡面前,丰饶是敏锐、脆弱而善变的。《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第十一块泥板描述洪水泛滥、凡人葬身鱼腹的惨景时也巧妙地借伊什坦尔之口发出这样的哀叹:
过往的岁月付诸黏土!死者如鱼卵在海底积壑盈谷!
而实际上这次灾难的始作俑者就是她本人。
而对于这种普遍的、贤愚无差的凡人之死,《埃努马埃利斯》中有一首闲诗吟诵起来也颇有深度:
城垣倾圮,唯余荒岗。
古城之墟,萋草成行。
此间骸骨,昔日所亡。
云谁奸恶?云谁善良?
不难看出,苏美尔—巴比伦文明整体被一种哀怨的情感基调把持,这就是我们后面会反复强调的消极美学情怀。这种惆怅的思绪到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发展到了顶峰。现在我们转向通过《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分析继续探讨悲哀是人类文明母题的这一命题。这部不朽名篇被看成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部悲剧,后来成为《圣经》的犹太神话中的洪水和方舟故事基本完全取材于《吉尔伽美什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可谓是欧洲英雄文学的鼻祖。
《吉尔伽美什史诗》一共有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亚述、胡里安、赫梯六种语言的泥板,但是故事大同小异。在公元前30世纪的苏美尔文明时代,史诗的故事已经大体固定;而在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版本以后,史诗就不再有任何改动。《吉尔伽美什史诗》的主体部分主要由三方面的考古结果组成:来自尼尼微和尼姆鲁德遗址的泥板、来自瓦尔卡古城墙的泥板和来自亚述巴尼拔图书馆遗物的泥板,但全都是较晚的亚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