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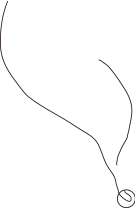
卫生学已经将自由纳入婴儿的生理生活中。自由的具体表现有:取消婴儿的包裹带,让儿童享受户外生活,延长儿童的睡眠时间,做到让儿童自然醒来等。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仅仅是让儿童获得自由的手段。让儿童在生命旅程之初就摆脱疾病与死亡的威胁,才是使儿童获得自由的更为重要的措施。一旦将这些障碍清除,不仅儿童的存活率会大大提升,而且他们的成长发育也能快速得到改善。
卫生学在帮助儿童增长身高、体重,使他们的外形变得更为漂亮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卫生学所做的工作充其量也只是排除了某些影响儿童生长的不利因素。也就是说,有些外部条件妨碍了儿童身体的发展和生命的自然进程,卫生学则帮助儿童冲破了这些枷锁的束缚。每个人都应在认识到“儿童应该得到自由”的同时,也认识到“满足儿童生理、生活条件”与“给予儿童自由”是相辅相成的。由于护理领域的发展,婴儿如幼苗一般受到照顾——良好的食物、清新的空气、适宜的温度,再加上对各类易诱发疾病的寄生虫予以攻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照料这些“天之骄子”的精细程度,就如同对待别墅里最美丽、最娇弱的玫瑰一样。
“儿童是花朵”,这是一个流传已久的比喻。我们希望现实也是如此。但是遗憾的是,现在获得这种特权的仅限于某些幸运的儿童。尽管有人呼吁:“孩子也是人。”但现实的情况却是,我们可以满足一株植物所需要的生长条件,却不能满足儿童成长所必需的条件。当我们看到一位深陷痛苦之中且极其虚弱的瘫痪病人时,我们会充满同情地说:“唉,他就像植物人一样地活着,已经失去了人生存的意义。”确实如此,这个人除了一具躯壳,其他什么都不存在了。
既然婴儿也是人,我们就应该用对待人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在这个躁动不安的社会中,当我们密切注视婴儿的行为时会发现,他们是多么的生机勃勃,对生活多么满怀期望啊!
既然婴儿也是人,我们就应该用对待人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儿童拥有什么样的权利?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应将儿童视作一个社会阶层、一个劳动者阶层。事实上,儿童也在进行着一项创造性的劳动——创造人的劳动。他们在创造自己的未来。他们在为自己身体和心理的成长全身心投入地工作着。母亲在为他们进行了几个月的工作之后,就将后面的工作都留给了他们,他们要自己去完成。也就是说,儿童的任务将会更为艰辛、更为复杂、更为困难。
孩子在出生时,他除了具有内在潜力之外,可以说一无所有。我们成人也必须承认,儿童将不得不在一个充满荆棘的环境中完成每一个任务!
在出生时,人类比动物更加脆弱、无助。经过几年的磨炼,他们就会长大成人。他们所处的社会是经过无数代人艰辛地努力而形成的,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组织的社会,他们要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这些既无力量又无思想的婴儿降生和融入我们这个所谓的文明社会中时,他们应当拥有什么权利呢?让我们看一看婴儿降生到世上后,我们所谓的社会公义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吧!
虽然我们的生活已经进入了20世纪
 ,但实际上在许多所谓的文明国家中,孤儿院和奶妈仍然是社会所承认的照顾某些孩子的形式。孤儿院是什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关押所、一个黑暗恐怖的监牢。它就像中世纪的土牢,在那里,犯人们频繁死亡而不留下任何痕迹,他们从未体验过他人给予的爱。他们连姓名也会被删掉,财产也会被剥夺,或许只有那些年长的犯人才能在记忆中珍藏着母亲的印象,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姓名。一个后天的盲人还能通过追忆美丽的色彩、灿烂的阳光得到某些安慰。然而,一个生活在孤儿院的弃儿连后天的盲人都不如,更像一个天生的盲人。弃儿甚至连犯人都不如,犯人拥有的权利都比他们要多!纵然是在那最让人憎恶的暴政时代,无辜的被压迫者也会燃起正义之火。这种不断累积的不满终有一天会引发一场革命,激发人民去争取平等的权利。但又有谁愿意站出来为这些弃儿的命运大声呐喊呢?
,但实际上在许多所谓的文明国家中,孤儿院和奶妈仍然是社会所承认的照顾某些孩子的形式。孤儿院是什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关押所、一个黑暗恐怖的监牢。它就像中世纪的土牢,在那里,犯人们频繁死亡而不留下任何痕迹,他们从未体验过他人给予的爱。他们连姓名也会被删掉,财产也会被剥夺,或许只有那些年长的犯人才能在记忆中珍藏着母亲的印象,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姓名。一个后天的盲人还能通过追忆美丽的色彩、灿烂的阳光得到某些安慰。然而,一个生活在孤儿院的弃儿连后天的盲人都不如,更像一个天生的盲人。弃儿甚至连犯人都不如,犯人拥有的权利都比他们要多!纵然是在那最让人憎恶的暴政时代,无辜的被压迫者也会燃起正义之火。这种不断累积的不满终有一天会引发一场革命,激发人民去争取平等的权利。但又有谁愿意站出来为这些弃儿的命运大声呐喊呢?
事实上,儿童也在进行着创造性的劳动——造人的劳动。他们在创造自己的未来。他们在为身体和心理的成长全身心投入地工作着。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这个社会还没有意识到儿童也是实实在在的人。某些母亲的职责成为一种社会习俗和一种奢侈表现。在一段时期里,一个出身于中产家庭的将要出嫁的女孩,会以未婚夫承诺的未来家庭的舒适条件为荣——“我的家庭将拥有一个厨娘、一个佣人和一个奶妈”。
由于存在这样的需求,在农村,一个刚生下孩子、身体强健的母亲会为自己拥有一对沉甸甸的乳房而非常得意:“我可以谋到一个好的工作,我可以当奶妈。”直到最近,卫生学家与营养学家才开始责备那些因懒惰而拒绝给孩子哺乳的母亲。为了提倡给孩子哺乳,他们甚至将那些亲自为孩子哺乳的女王和皇后奉为榜样,让其他母亲学习。
卫生学家与营养学家之所以建议将哺乳孩子作为母亲的一项责任,是基于以下这条生理原则的:母乳喂养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能满足婴儿的营养需求。尽管专家的建议很明确,但母亲对这项职责的履行还远未普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位身体十分强健的母亲却任由身旁的奶妈抱着孩子。
母乳喂养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能满足婴儿的营养需求。但母亲对这项职责的履行还远未普及。
这种由奶妈哺乳孩子的方式还会导致另一个后果。如果一个婴儿享有两位母亲的乳汁,那么必将有另一个婴儿连一位母亲的乳汁也得不到。因为母乳不是一种工业品,它源于大自然的精心调配,大自然配给每个新生命的母乳都是定量的。母乳是随着生命的孕育过程而产生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产生母乳。
养奶牛的人对此十分清楚,他们一般会精心地喂养产奶的奶牛,而将小牛送给屠户。他们知道,每当小牛被迫与母亲分离时,它们是多么痛苦!小狗崽与小猫崽也是如此,当一只充满爱心的母狗产下许多小狗崽,而又因为无法全部喂养只得清除一些时,这位狗妈妈是多么伤心!与这些动物相比,奶妈的表现则截然不同,她们是在自愿地出售自己的母乳,由此导致另一个婴儿——她们自己的孩子喝不到母乳。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只有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地规定一个人应享有的权利,才能保护这些婴儿。社会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之上的,一个人即使是因为饥饿而偷了一块面包,他也是一个贼,也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他的行为也会被视为非法行为。如果有人确实犯下了某种罪行,那他就应该获罪。成人每天都在对幼小的婴儿犯罪,但是在社会上,竟然没有人把他们的行为当作一种犯罪,而只是将其视为一种奢侈的表现。对一个孩子而言,有什么比能拥有母乳更为神圣呢?如果婴儿能够表达,他们完全可以用拿破仑的这句话来抗议:“这是上帝赐予我的。”他们的要求毫无疑问是合法的。这是他们降生到世上后所拥有的唯一资本。母乳也是因为他们的出生才产生的,是随他们一起来到这个世上的,是他们的全部财富:他们的生活、成长与生命的希望都蕴含在母乳之中。
出生后即被剥夺吸吮乳汁的权利,对一个婴儿的影响是终生的。一旦他长大成人后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去从事某种艰苦的工作,他一定会觉得身体虚弱,甚至还易患佝偻病。现代医学证明,在工作中大量因伤痛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永久性伤残,往往都源于那些人小时候未能享受到哺乳的权利。一定有那么一天,这些婴儿一旦成年,就站在社会道德的法庭上对自己的母亲提起控诉!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母亲是因为生病而无法给自己的孩子喂奶,那该怎么办?我们面对这种情况只能说,这位母亲和她的孩子是不幸的。但是,我们要进一步问,为什么另一个孩子要因为这对母子的不幸而遭受痛苦呢?无论一个人是多么的富有,我们都不应该允许他去剥夺别人的财富,因为那个人也是亟待这笔财富生存的。即使在野蛮的年代,如果一个皇帝必须靠沐浴人血才能治愈自己可怕的疾病,他也不能让健康的人为自己流血。这是我们建构文明的基本条件,也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有别于“海盗窝”与“食人族”的原因。
我们的社会已认可了成人的权利,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也认识到了儿童应拥有的权利!我们已认识到了正义的力量,但现在它只为那些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所有。直到现在,在卫生学和营养学的观念上,人们也许或多或少有所进步,但在审视文明——一种基于权利平等的文明时,却还存在很大的问题。
当我们认真审视儿童的道德教育时,我们的目光应更宽广一些,应仔细观察一下我们为他们准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难道我们愿意他们也像我们那样毫无顾忌地、粗暴地对待弱者吗?难道我们愿意他们也像我们那样,在与他人交往时,只做个半文明人,但当遇到无知、受压迫的人时,就变成了个半野蛮人吗?
如果我们想从根本上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就要在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之前,效仿那些马上要走上圣坛的牧师:面对全体教徒,先低头忏悔自己的罪行。
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孩子,就像一只脱了臼的手臂一样。在这只脱臼的手臂复位之前,人类是无法使自己的道德得到进化的。
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儿童,就像一只脱了臼的手臂一样。在这只脱臼的手臂复位之前,人类是无法使自己的道德得到进化的。只有当这只脱臼的手臂复位以后,这个人才不用再忍受受伤的肌肉组织所带来的疼痛与麻痹。与之相比,有关儿童的社会问题要更为繁复、深奥,它既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将来会面对的问题。